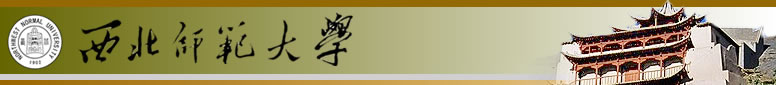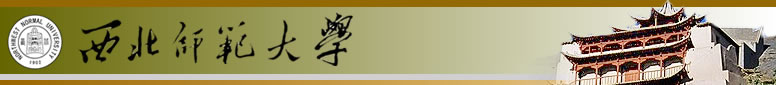第七章
敦煌学与语言文学研究
敦煌文献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语言和文学资料,它们对于研究中国文字、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古典文学、中国文学史意义重大。
第一节
敦煌文学作品概览
一、什么是敦煌文学
敦煌文学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敦煌学中兴起、发展得较早、较快的一个研究领域。然而什么是“敦煌文学”?它应当包含哪些方面内容?它的体系结构及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并不尽一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逐渐深化,许多方面取得共识。
现不少学者认为(如颜廷亮等),所谓敦煌文学,指的是以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创作于以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的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这个界定有以下要点:
第一,主要指保存于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就是说不限于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如敦煌简牍中的、石窟供养人题记中的文学作品等,但主要是敦煌遗书所保存的作品。
第二,是以唐、五代、宋初为主要创作时代的文学作品。就是说其主体部分是唐、五代、宋初创作的文学作品,但并不限于此,还应包括先唐时期和宋初以后的文学作品。
第三,是以敦煌地区为主要创作地区的作品。就是说其主体部分是在敦煌本地创作的,但并不限于此,而还应包括产生于敦煌地区之外而又在敦煌地区流传的文学作品。
二、敦煌文学的分类
敦煌文学作品的数量很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分类。如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俗文学(民间文学)和雅文学(传统文学)、乡土文学和中原文学、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等。而按照通常的以形式特点为基准的分类方法很多学者将其归为六个大类:
1、说唱类
为唐宋时期说唱艺术的文学底本。中国讲唱文学源远流长,唐宋时期十分兴盛。可归入此类的敦煌文学作品有讲经文(附押座文、解座文)、变文、因缘、话本、词文、诗话和俗赋(故事赋)等。此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适合说唱,或重在讲说,或重于唱吟,或说唱并重,表现在书面上则是或以散文为主,或多用韵文,或散韵结合,有的还保留有所用唱调的痕迹。其语言通俗易懂,甚或纯用口语,适合普通民众视听。
2、曲辞类
为配合音乐、合乐歌唱的一类作品,属于所谓音乐文学范畴,包括词(曲子词)、俚曲小调、佛曲等。有的还可配合舞蹈演出,故又可称之为乐舞文学。此类作品的主要特点是以声定文、由乐定辞,多为长短句形式,有一定的格式和调名。它们多为民间作品,基本上产生和兴起于唐五代时期,在研究中国歌辞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
3、诗赋类
是以诗和文赋为体创作出来的一类作品,包括骚体、古体、近体、歌行体诗和文赋。文赋不同于主要用于讲故事的俗赋,而是重在述志、抒情、状物,与诗歌有共同之处,故可将它们归为一个大类。此类作品历史久远,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辑佚、校勘和研究价值。
4、小说类
不完全类同于今天的小说,是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唐人传奇小说相类的作品,包括佛教感应记、灵验记、入冥记、非感应故事小说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篇幅较短小,以散文叙述为主,大量使用民间口语,通俗易懂,在中国白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5、散体文类
泛指所有具有文学色彩的叙事、抒情、状物、表意、说理的、主要以散体表达的文字,其内容庞杂,体式多样,包括表、疏、状、牒、书、启、碑、铭、传、记、文、录、帖、说、邈真赞、祭文、序跋等等。
6、杂著类
除上述五类外,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包括书仪、童蒙作品、寺庙杂著、偈、赞、歌诀等,可归入此类。
三、敦煌文学的基本特点
据颜廷亮、周绍良等学者的研究,敦煌文学在思想内容上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它反映了千余年间,特别是唐五代宋初时期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了全国乃至国外某些民族和地区社会生活的一些断面。具体地说有如下几方面内容:热爱乡土,怀宗念祖;反抗外来侵略,主张民族友好;积极进取,追求美好生活;普遍渗透的宗教思想;注重实际,关切人生;市民生活和市民观念的表现。敦煌文学从思想情调上来说是健康的、积极的、进步的,尤其是其中所体现的乡土之情和中原情结,实际上是敦煌文学的灵魂之所在,构成了敦煌文学思想内容方面最基本的特点。
敦煌文学由于跨度时间长,作品数量多,作者队伍杂,表现在艺术风貌上也就多种多样、绚丽多姿,而其突出的特点,特别是体现在敦煌本土所出作品和一些由外面传入却又在敦煌广泛流传或经过敦煌地区人士加工过的作品上,则是以俗为主,以朴见长,具备平实质朴的大众文学本色。其关切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通俗质俚的语言,活泼多样的大众化体式,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加上很多作品本来就是治实之作,重在实用,因而为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
四、研究敦煌文学的意义
敦煌文学是祖国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中的重要一笔。从事敦煌文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可以使人们全景式地认识唐、五代、宋初文学的整体面貌。唐宋时代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作品,是那样的脍炙人口,美不胜收,传诵不衰。然而这些并非是唐宋文学的全貌,能够流传至今日的作品都是经过历史筛选的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东西,它们体现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主要潮流和主要贡献,但尚难以使人们全景式地认识当时文学发展的总体面貌。而敦煌文学作品中既不乏高雅优秀的文人之作,更有着为广大民众所喜好的平实质朴的俗文学创作;既有纯文学性的作品,又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作品;既有不少中原等地传入的作品,更有大量本籍本土人士之作,还有来自敦煌周边民族地区甚或印度、波斯、叙利亚、朝鲜等地的作品。从其作者队伍构成上来看,既有文士、官员,更有普通民众、僧道人士。敦煌文学可作为一个窗口,透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探到整个唐宋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比如,敦煌文学中的变文、话本、小说、世俗社会和宗教社会所使用的诸多文体的应用杂著类等作品,在敦煌文书未发现以前,人们对之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从而也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唐五代宋初整个中国文学的全貌。而有了敦煌文学,这种状况无疑就会得到相当程度或部分程度的改观。
第二,有助于解决中国文学史上长期难以解决的一些重要学术问题。如词的起源、话本小说的起源、宝卷的起源、戏曲文学的产生、白话诗的来龙去脉、唐宋西北边地的文学状况、通过丝绸之路而发生的中外文学交流的实际情景等问题,只有通过对保存在敦煌文学中的这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或部分解决。
第三,可以给今天的读者提供一批新的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丰富人们的文学生活。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文学生活总是越丰富越好,总是盼望能有更多的好作品欣赏。敦煌文学中许多好的作品正可满足这种需求。诸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白话诗等一批优美的诗作,变文、诗话中的不少作品、脍炙人口的《茶酒论》、《韩朋赋》,流传广泛的俚曲小调等,读起来都能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艺术上的享受,使读者获得一大批新的精神食粮。
第四,可以为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比如在如何解决文艺与群众关系问题上,敦煌文学对我们就很有启示。从总体上看,敦煌文学是与当时敦煌地区的广大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文学,在敦煌文学作品中既可以听到广大群众的心声,又可以看到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其中的俗文学作品,把大众的思想和感情熔铸于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之中,更是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又如在应当如何对待民族文学传统和外国文学营养问题上,敦煌文学本身就可以说是中外文学交流的产物,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对外来文学持胸襟开阔的态度,吸收了印度文学等外来文学的有意养份,才使得其如此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很好地挖掘敦煌文学的宝贵经验,无疑对于我们今天文学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第五,敦煌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限于文学方面,它对于唐宋时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亦很有意义。从中我们可以获悉当时敦煌乃至西北地区的自然景物、生态环境、政治斗争、民族关系、民俗风情、生产生活、宗教活动等方面一幕幕的真情实景。
第二节
敦煌说唱类文学作品和小说
一、讲经文(附押座文、解座文)
讲经文是唐宋时期寺院中俗讲僧进行俗讲时使用的底本。佛教传入我国后,为了宣传教义、争取信众,采用了不少办法,其中面向世俗大众通俗讲解佛经经文的说唱形式俗讲便是其一。
俗讲一般在寺舍中进行,其处所或可称作“讲院”。当时一些较大的寺院中皆有专门负责俗讲的俗讲僧。俗讲的听众多为普通百姓,士子名流甚至皇帝也乐闻其说。《资治通鉴》“宝应二年六月”条记载,唐敬宗就曾前往兴福寺“观沙门俗讲”。俗讲开讲时须有多人配合,由“都讲”吟唱经文,“法师”解释经义,寺中三纲之一的维那也要到场,鸣钟集众,另有梵呗、香火,各司其职。所谓吟唱,不仅仅是一般性地谈说,还要讲求声调。当时要求俗讲僧既要精通佛典教义,又要具备“声、辩、才、博”之学,还要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随机应变。俗讲的主要内容为佛教经文,同时大量增加故事性、世俗性成分,形式上注重通俗化,以达到吸引听众、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因而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
目前所能见到的讲经文仅存于敦煌遗书中。保存完好而又明确标为讲经文的为P.3808《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此为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应圣节(皇帝降诞日)在洛阳皇宫中兴殿内祝寿讲经的作品,所讲为《仁王护国经》。此外敦煌讲经文还有《妙法莲花经讲经文》(P.2305、P.2133等)、《维摩诘经讲经文》(S.4571)、《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P.2133)、《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P.2931、P.2955等)、《父母恩重经讲经文》(P.2418等)等。
由敦煌遗书见,讲经文的一般结构为:开篇多为“说押座”,“押”可通“压”,所谓押座,乃是一种开场前安定听众,使其专心听讲的方式,此段文字称之为押座文。接着唱出所讲佛经的题目,并对经名逐字逐句加以诠释。然后都讲诵出一段经文,法师对其阐释解说,如此递相往复,将经文一段一段讲完。解经时允许都讲或其它听众就疑难之处发问,法师据其诘问给以解答。俗讲结束时,一般有一段“解座文”,以敦劝和吸引听众下次继续前来听讲。
为适应听众水平,阐释经文非常注重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和趣味性,运用讲故事、寓言、比喻、对话等手法,把抽象的教义蕴含在故事情节或具体事物的描绘中,使其易解易明,亲切生动,引人入胜。在表现形式上有说有唱,散韵结合,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说说唱唱,注重文辞的音乐美。有些唱词上还注有“平”、“断”、“侧”、“吟”、“韵”、“吟断”、“平侧”、“侧吟”等大约是表示声腔的说明性文字,可见讲经时应有多种咏唱调子,唱腔富于变化。
俗讲不仅盛行于唐宋,而且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有学者认为后世的乐曲系、诗赞系说唱伎艺均受其影响,今天仍在河西流传的宝卷,作为说唱伎艺“宣卷”的底本,更是敦煌讲经文的嫡传。
二、变文
变文,又可称作“变”,为唐五代民间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转变,即说唱变文。转变一名屡见于唐五代人的记载。如郭湜《高力士外传》记,高力士陪太上皇李隆基“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韦縠辑《才调集》卷八收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四川女艺人说唱《昭君变》的情形。当时还有专门演唱变文的娱乐场所“变场”,有时转变也在街头闹市演出。
唐五代转变虽十分盛行,但作为其底本的变文今天仅能在敦煌遗书中看到,弥足珍贵。敦煌变文主要有:《舜子变一卷》(S.4654)、《八相成道变》(北8437、北8438、北8671)、《降魔变》(S.5511、S.4398背)、《破魔变》(P.2187)、《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S.2614、P.3107)、《目连变文》(P.3485、P.4988背)、《目连救母变文》(北8443、北8444、北8445、北8719、北7707)、《频婆娑罗王后宫采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S.3491、P.3051)、《伍子胥变文》(S.0328等)、《孟姜女变文》(P.3319、P.5019、P.5039)、《前汉刘家太子变一卷》(P.3645)、《王昭君变文》(P.2553)《张议朝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等。
变文是如何得名的,“变”是什么意思?许多学者对之做过不少有益的探讨。向达《唐代俗讲考》认为,变文源自南朝清商旧乐,该乐中自有所谓变歌。程毅中《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认为,变文是在中国固有的赋体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认为,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变字似非中华固有,或许是译自梵语Citra。关德栋《略说“变”字的来源》认为,“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变”字就是“曼”字一音之转。施蛰存《“变文”的“变”》认为,“变”是一个外来语的音译,义为“图画”或“图像”。周绍良《谈唐代民间文学》认为,“变”之一字,只不过是“变易”、“改变”的意思,其中并无若何深文奥义,变文意即把一种体裁的东西改变成另一种体裁的记载,如依佛经改变成说唱文,或依史籍记载改变成说唱文。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看法与之相近,认为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我们倾向于周绍良先生的观点。
与讲经文不同,变文中不再引用佛经原文,而是直接演述故事。其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佛教、道教和其它一些神话题材,另一类是历史和现实生活题材。前者的艺术特色是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极尽夸张渲染,作者的思想驰骋于虚无缥缈、瑰奇谲丽的玄怪世界中。如根据《佛说盂兰盆经》演绎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目连变文》、《目连救母变文》,描写佛弟子目连历经千难万险将其母救出地狱的故事,把地狱的凄惨、刑法的残酷、狱卒的冷酷无情、佛法的万能、目连的勇敢无畏、母子之情的伟大,都描绘得淋漓尽致,人物形象刻画得有血有肉。
历史题材的作品大多以某一历史人物为主线,以历史事实为框架和依托,广泛吸收有关民间传说,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渲染和再创造,从而形象地再现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并通过对不同时期人物的评论,大胆地表达人民群众对贤愚忠奸的爱憎情感。如《伍子胥变文》,以《左传》、《国语》、《史记》中的有关记载为素材,大量摄取关于他的各种传说,演绎出伍子胥复仇灭楚、死于忠谏的动人故事,成功塑造了这个坚毅不屈、大义凛然的悲剧形象,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受害者的深切同情,激励起人们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勇气。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有《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两篇,热情讴歌了张氏叔侄领导人民收复河西、保境安民的英雄业绩,表达了人们重归大唐后的喜悦自豪和爱国情感。
变文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情节曲折动人,演出时还往往配以图画,人们可边听边看,因而为大众所喜爱。变文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宋元及其以后的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弹词、鼓词、话本、宝卷等各类说唱文学以及戏剧文学,都与变文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三、因缘
因缘,或称作缘起、缘,是一种演绎佛教因缘故事而又不解读经文的说唱艺术,即说因缘的底本。因缘本是佛家观念里“因”和“缘”的合称,是佛教用事物间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它们生起变化现象的用语,所谓“因缘和合,诸法即生”。佛家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处于因果联系、依一定条件生起变化之中;众生皆在善恶因果的严密关系中,只有皈依佛法,虔诚修持,才能脱离苦海,获得解脱。敦煌说唱文学中的因缘,就是讲述佛弟子或善男信女前世、今生因果报应的故事。
敦煌因缘作品主要有:《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日本龙谷大学藏)、《难陀出家缘起》(P.2324)、《欢喜国王缘》(P.3375背等)、《丑女缘起》(P.3048等)、《四兽因缘》(P.2187)、《目连缘起》(P.2193)、《十吉祥》(Ф.223)、《佛图澄和尚因缘》(S.1625、P.2680等)、《刘萨诃和尚因缘记》(P.2680、P.3570等)、《远公和尚缘起》(P.2680)、《清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P.2680、P.3570、P.3727)等。
因缘因不需要解读经文,故演讲者有较大的渲染铺叙的自由,便于充分发挥,增强感染效果。如《欢喜国王因缘》讲述欢喜王与夫人有相生死悲欢的遭遇,就颇具故事情节和传奇色彩。
因缘在表现手法上亦是边讲边唱,散韵并行。
四、诗话
诗话,也是唐宋时期一种说唱伎艺的底本。与其它说唱底本相比它的基本特点是,虽然仍为说唱结合、散韵相间,但以唱为主,而散说部分既有押韵自由的四、六骈语(一般隔句押韵,或一韵到底,或换一、二此韵),又有句法灵活的散体叙说;有些文中或文末还证以诗咏。由于其特点与后来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比较接近,故可将其称作为“诗话”,虽然这些写本原件并没有一个是题作“诗话”的。
敦煌诗话类作品有:《季布诗咏》(P.3645)、《百鸟名(君臣仪仗)》(S.3835、S.5752)、《孟姜女故事》(P.5019)、《苏武李陵执别词》(P.3595)、《齖磕书》(S.4129、P.2564、P.2633)等。虽数量不多,但题材各异,风格独特,文辞优美。作者善于运用人物性格刻画展现主题。如《齖磕书》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一个“斗唇磕牙,务在喧争,欺儿踏婿,骂詈高声”、下橱时“翻粥扑羹,轰盆打甑,雹釜打铛”、性格直爽泼辣的新妇形象,尤其是写阿婆、新妇、夫婿间的对话与动作十分简洁传神,人物个性突出。《孟姜女故事》通过送寒衣、哭倒长城、指血延骨、髑髅对话和痛祭亡灵等一系列悲惨景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王朝沉重的赋役带给人民的灾难。《苏武李陵执别词》以虚构的手法描写苏武、李陵、韩曾三人相会于胡地的故事,把李陵投敌的经过与复杂心理、身陷异邦而又时时思念家国的心情表现得丝丝入扣。《百鸟名(君臣仪仗)》以拟人化的笔法描写了以“凤凰为尊”的鸟王国,设想奇特,寓意深刻。百鸟“排备仪仗,一仿人君”,深刻影射了现实社会的君臣关系、封建等级和秩序的森严。文中还描绘了40余种鸟禽的习性、毛色、命名及其传说,准确传神,生动有趣。
五、词文
词文,是唐代一种以通俗韵文叙事的说唱伎艺的底本。一般认为它是从乐府民歌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古代民间叙事诗孕育发展而来的。词文在体式上的主要特征为:个别的在篇首有简略的散说提示语,其余通篇皆为白话韵文,用以唱故事,而非说故事;唱词多为七言体,偶有五言或六言句,偶句必韵,韵律较宽,平上去入不论。
敦煌词文作品主要有:《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P.3386)、《董永词文》(S.2204)、《悉达太子修道因缘词》(S.2440)、《下女夫词》(P.3350、S.3877等)等。
《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一卷》共646句、4522字,计有323韵,且一韵到底,实为唐代一篇宏大的民间叙事诗。作品主要取材于《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但词人“演义史事,藻绘剧情”,将死历史作成活话剧,在情节上多有创造和发展。通过楚将季布骂阵、当众羞辱刘邦、楚灭汉兴后刘邦张榜悬赏捉拿季布、季布东藏西避、躲过层层搜捕、而最后在萧何和夏侯婴的请求下解冤释仇、赦免了季布、并以君臣相待的故事,塑造了巧智慧辩、勇敢无畏、敢于和命运抗争的季布形象,也表现了刘邦不记前嫌的政治家风度。通篇构想奇特,情节一波三折,悬念丛生,人物形象饱满,语言驾驭娴熟自如。
《董永词文》,以民间广泛流传的董永的传说为题材,经过作者的丰富想象和艺术加工,唱述了贫苦的劳动人民因为大孝而争得了男耕女织的爱情和生活的故事。写得情真意切,颇为感人。
《悉达太子修道因缘词》,演唱悉达太子(即释迦佛祖)由乘象入胎、肋下降生、游观四相、逾城出家直到修道成佛的佛传故事。有人认为,该篇词文出现的多人对唱的新形式,透露出由词文向戏剧转变的趋向。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下女夫词》有10余篇,为唐宋时期敦煌婚礼场合中的“下女夫”仪式所用的唱词。“女夫”即“女之夫”,通称女婿。“下”有“戏耍”之意。“下女夫”即当迎亲新郎一行抵达女家门口时,女方姑嫂故意闭门相拦,刁难、戏弄新女婿的习俗。其主要内容为盘诘戏谑、刁难下马、故上药酒、吟诗入门、请婿下床等,从而给婚礼场面增添喜悦热闹的气氛。《下女夫词》多为男女双方有关人员一问一答对唱,内容涉及初见通问、探问身世、传递情思等,妙趣横生。
六、故事赋
敦煌赋体作品共有写卷47件、赋作28篇,其中故事赋5篇。故事赋又称俗赋,是一种以通俗韵文形式演唱故事的赋体作品,是我国古代辞赋通俗化发展的产物。
敦煌的5篇故事赋作品为:《晏子赋一首》(P.2564、P.2647、北4773等)、《韩朋赋》(P.2653、S.2922)、《燕子赋》(甲)(S.0214等)、《燕子赋》(乙)(P.2653)和《丑女赋》(P.5752、P.3716)。
与一般追求雕镂夸饰、铺采摛文的赋体不同,敦煌故事赋以口语叙事为主,行文畅顺,自由押韵,具有说唱的特点,因而可将其归入说唱文学类。同时这些作品情节曲折,跌宕起伏,并多以拟人、比喻等手法表达深刻的社会主题,具有寓言故事的某些特点。
《韩朋赋》取材于干宝《搜神记》中的“韩凭故事”,对其进一步创作,使情节结构愈见波折起伏,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作品从韩朋娶妻贞夫、夫妻恩爱、相誓永不变心起笔,接着写韩朋出游,仕于宋国,六秋不归;宋王欲夺朋妻,贞夫被骗入宫,面对宋王的威逼利诱,贞夫矢志不改;最后韩朋殉情,贞夫投圹而绝,化为青白二石,变生双树,幻化鸳鸯,以羽毛拂去宋王之头,实现复仇愿望。通篇叙事简洁紧凑,语言通俗明快,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为了忠贞的爱情誓死反抗暴虐的崇高品质。
《燕子赋》有甲、乙两种,基本内容近似,但风格有所不同,前者为四、六言赋体,后者为五言诗体。它们都以燕雀争巢、凤凰判决的寓言故事为主线,以幽默诙谐、嬉笑怒骂的艺术手法,深刻揭露了以强凌弱、巧取豪夺、无辜蒙冤的社会现象,以及封建官场里徇私枉法的种种弊端。
七、话本
话本,是唐宋时期民间说唱伎艺“说话”的文学底本。所谓“说话”就是讲故事,类似于今天曲艺中的说书。这一伎艺因适应大众娱乐、审美的需要,曾颇为盛行,就连唐明皇晚年也喜听“说话”。
敦煌话本作品主要有4篇,即《庐山远公话》(S.2073)、《叶净能诗》(S.6836)、《韩擒虎话本》(S.2144)和《师师谩语话》(S.4327)。虽数量不多,但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唐五代话本作品的全部,弥足珍贵。
敦煌话本取材多样,运用文白兼杂、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笔法,塑造出一些既有历史依据、又具理想色彩的特征鲜明的艺术形象。作品追求故事情节的完整曲折和细节描写的细腻入微,增强了故事性和感染力。敦煌话本在我国小说的历史发展中开了白话小说兴盛的先河。
《庐山远公话》与《叶净能诗》,是在唐五代佛教和道教盛行的背景下,佛、道教徒为宣称教义而分别编写的话本。前者描写东晋名僧惠远的故事。惠远早年在庐山宣讲《涅槃经》,声名远播,以至感动潭龙听讲、山神造寺;后被贼人掳掠,为偿还前世之债卖身为奴;后被晋文公召见,供养数年后重返庐山,造一法船,归依上界。其中充满了轮回报应、因缘宿债的佛教思想。《叶净能诗》描写“上应天门、下通地理”、“呼神唤鬼,化穷无极”的道士叶净能符箓救妇、屠妖救女、遥采仙药、化蛇噤鼓、化瓮助酒、斩龙取肉、祈天降雨、陪同玄宗皇帝神游剑南观灯和神游月宫等10余个神奇故事,极尽夸耀、渲染之能事。
《韩擒虎话本》取材于《隋史·韩擒虎传》和有关民间传说,描写了隋朝大将韩擒虎辅佐隋文帝渡江灭陈、奉使和蕃、箭射双雕、镇摄蕃王、最后被点为“阴司之主”的故事。作品运用夸张、虚构、幻想的手法,塑造了韩擒虎英武绝伦的形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晚唐五代孤悬西陲的敦煌人民向往中原王朝力量强大、国家统一的愿望。
八、小说
敦煌小说,指的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唐人传奇小说体式相同的作品,不完全类同于今天的小说。它不属于说唱文学类,而是一般民间口耳相传、街头巷语的故事的记录或创作。其篇幅一般较为短小,甚或缺乏完整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
敦煌小说内容多样,既有中原传入的作品,又有当地人的创作;既有小说集,又有单篇或多篇的连抄;既有佛教感应记,又有非感应故事小说等。
敦煌存三部小说集:《启颜录》(S.0610)为一部笑话集,约结集于初唐,原本在中原久佚。敦煌本抄录笑话40则,其中多半不见于《太平广记》所收该书佚文中。主要内容有辩捷、论难、昏忘、嘲谯等,读后令人忍俊不禁。《搜神记》(S.0525、P.2656、P.5545),作者句道兴,该书与晋代干宝《搜神记》多有相同之处,应为干宝原书最早的辑抄本。但敦煌本更具文学特色,叙事更为细致,情节愈见曲折,应是经过民间流传中的增饰和辑抄者的加工后的本子。唐颜之推《还冤记》(P.3126等),又称《冤魂志》、《冥报记》,含15个宣传佛教因果报应、冤鬼索报的短篇故事。
敦煌佛教感应记小说数量较多,有的称作“灵验记”或“传验记”,皆选取人们行善积德而致福报的故事为题材,宣扬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其内容或写鸣钟以得好报,如《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S.0381);或写置设斋供以得好报,如《落蕃贫女忏悔感应记》(S.6036);或写念佛诵咒以得好报,如《白龙庙灵异记》(P.3142);或记抄写诵持佛经以得好报,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P.3898),汇录14则感应故事。
敦煌非感应故事小说数量不多,但篇幅较长,情节也较曲折。主要有《秋胡》(S.0133背)、《唐太宗入冥记》(S.2630)、《道明还魂记》(S.3092)等。《秋胡》故事原出《列女传》,记秋胡新婚不久辞母别妻,求学老仙,三年后学成往投魏国,拜为左相;胡妻在家孝养公婆,含辛茹苦;数年后胡忆老母,遂返乡探亲,行至桑林遇妻,因相隔年久互已不识,胡见其貌美出言调戏,遭胡妻痛斥;胡回至家中方识其妻,羞愧难当。小说谴责嘲讽了那些庸俗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仕宦人物一旦功成名就便舍弃家室、喜新厌旧的卑劣行为。
第三节
敦煌诗赋辞文
一、诗歌
敦煌文书中保存的诗歌作品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诗歌写本约400卷,所存诗歌超过3000首。敦煌文书以外的其他有关史籍中,也保存一些属于敦煌文学的诗歌作品,如敦煌简牍中的作品、《晋书》所记“五凉”时期的敦煌诗作等。
敦煌诗歌范围广泛,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既有先唐时期作品,更有唐五代宋初的作品;既有中原等地传入的诗集及佚诗,更有大量本土人士之作;既有世俗社会作品,亦有宗教寺观之作。它们汇成了一幅幅具有浓郁特色的史诗般的画卷,是我国诗歌宝库中一笔非常珍贵的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文学和史学价值。
敦煌诗歌中传自中原的作品主要有唐人诗集、唐宋诗篇名作及佚诗。如《王梵志诗集》(S.0778等30多件,有诗300余首)、《唐人选唐诗》(P.2567、P.3619等多件)、《高适诗集》(P.3862等)、刘邺《甘棠集》(P.4093)、李峤《杂咏》(S.0555等)、《白香山诗集》(P.2492等)、《珠英学士集》(P.3771等)、韦庄《秦妇吟》(P.2700等10余件)、《读史编年诗》(S.0619)、垂幌诗图《离合诗》(S.3835)、《方角书》(S.5644)等等。其中不少诗作为《全唐诗》所佚。
敦煌本土创作的诗歌,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作品:一是当地诗人文士之作,如“三楚渔人”张永的《白雀歌》(P.2594背、P.2864背)、西汉金山国宰相张文彻的《龙泉神剑歌》(P.3633)、P.2555所抄59首落蕃诗人诗作、马云奇诗等;二是敦煌僧尼道士所作,如河西都僧统悟真的《百岁诗》(S.0930背)、龙兴寺和尚香岩《嗟世三伤吟》(S.5558)、佚名氏《九相观诗》(S.6631)等;三是民间诗歌,作者大多佚名,如《卢相公咏廿节气诗》(P.2624)、《少年老翁问答诗》(P.2129)、P.3500《童谣》、P.3644《招徕叫卖诗》、P.2498《学郎李幸思诗》等。
敦煌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以高度凝练、概括的笔触,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社会时事的风云变幻,展现了敦煌和祖国西北地区雄浑壮丽的山川景物和厚重的文化积淀,描绘了多彩浓郁的民俗风情,抒发了人民大众的疾苦和愿望。
敦煌诗歌中初唐诗人王梵志的作品甚为引人注目。王梵志为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作品多为五言白话诗,“不受经典,皆陈俗语”,在我国白话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作者十分注重诗歌的社会功用,深刻揭露了赋税徭役苛重、贪官污吏横行、劳苦大众痛苦的社会现实。如写贫穷田舍汉“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劝诫官员“官职莫贪财,贪财向死亲。……一朝囹圄里,方始忆清贫”。
《秦妇吟》为晚唐诗人韦庄(836~810)的名篇,原件早遗,幸有敦煌文书所存。这首叙事七言诗长达328句,为古典诗歌中少见的巨制。诗人亲身经历唐末黄巢农民起义的动荡年代,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通过一位秦妇之口,以高度概括的现实主义手法,形象地描绘出风云变幻的社会现实。如云:“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荞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路旁时见游弈军,坡下寂无迎送客。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明朝晓至三峰路,百万人家无一户……”。
二、文赋
敦煌28篇赋作中,有23篇属于文赋。文赋为我国传统赋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与诗歌有共同之处。
敦煌文赋作品有:佚名《秦将赋》(P.5037)、何蠲《渔夫歌沧浪赋》(P.2621)、张衡《西京赋》(P.2528)、左思《吴都赋》(L.1457)、刘长卿《酒赋》(P.2488、S.2049等)、刘瑕《驾幸温泉赋》(P.2976等)、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P.2539)、张侠《贰师泉赋》(P.2488等)、佚名《去三害赋》(S.3393)、王绩《游北山赋》、《元正赋》、《三月三日赋》(P.2819)、成公绥《啸赋》(S.3663)、王粲《登楼赋》(P.3480)、杨炯《浑天赋》(S.5777)、刘希移《死马赋》(P.3619)、高适《双六头赋送李参军》(P.3862)、卢竧《龙门赋》(P.2544)、佚名《月赋》(P.2555)、佚名《子灵赋》(P.2621)等。
敦煌文赋见于《文选》、《全唐文》等古代诗文集的有7篇、独存敦煌的16篇,其中18篇为唐人作品。见于古诗文集赋作(张衡《西京赋》、王粲《登楼赋》、成公绥《啸赋》、杨炯《浑天赋》王绩的3篇赋)的主要价值在于校订今本讹误。
就敦煌文赋的思想内容来看,或吟诵自然景物、叙写民情风俗,或描写战争的残酷、谴责枉杀无辜荼毒生灵的残暴罪行,或赞扬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英雄事迹和高尚行为,或冷嘲热讽、鞭挞人世间的种种罪恶和丑行,或鼓励勤学成才、倡导道德的自我完善,或抒写生不逢时、壮志难酬的怨愤,或表现隐居不仕、孤傲自许的思想情怀,或以宣泄性爱、追求酒乐为内容。
《秦将赋》取材于《史记·白起列传》中有关白起坑杀40万赵卒的记载。作者以“满谷只闻刀剑鸣,众山遥遥觉血气”的血淋淋的描写,强烈谴责了白起“血流涧下如江湖”、“旋斩旋填深坑底”的暴行,率直表达了对无辜者“朝朝怨气上冲天,夜夜难闻鬼啼哭”的深切同情。
《渔夫歌沧浪赋》,以渔夫与逐臣的对话,道出了一些知识分子
“殊不知世以昏兮道不行,我独醒兮人皆醉”、 坚持信念、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人生态度。
《贰师泉赋》,描写了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征伐大宛回师敦煌途中,剑刺枯山,精诚感天而得到神奇泉水,解除将士渴乏的传说,讴歌了李广利远征西鄙、不畏艰险的精神。
《去三害赋》取材于《晋书·周处传》,叙写了周处浪子回头,勇除南山猛虎、水下蛟怪以及自身弃恶从善的故事,读来令人感慨。
三、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或称敦煌词,指的是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五代时期的燕乐曲词。燕乐系始于隋代而盛于盛唐的乐曲,主要是隋唐新声。燕乐都伴有曲词,这就是词。词与音乐密不可分,因而它应属于音乐文学作品。有时词与乐、舞同时表演,亦可视其为乐舞文学。
今存敦煌词有60余调,绝大多数见于唐人教坊曲和传统的唐宋词,只有极少数词调仅存敦煌,如《郑郎子》、《别仙子》等。敦煌词基本上是民间词,出于文人之手的不多。与当时及后世文人词相比,敦煌词具有作者面广、取材多样、词体不甚定型等特点。它保存了词的早期形态,其字数、句式、韵律上显得较为自由灵活,甚至同调词内也有一些差异。
从总体上看,敦煌词具有丰富、健康、清新、进步的思想内容,在艺术表现方面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构成一幅幅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图景,特别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社会中下层人物的心声和愿望。其思想感情真挚,抒情表意直率坦诚,风格质朴,主旋律是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且语言淳朴自然,活泼生动。
依题材和内容的不同,敦煌词可分为如下几类:
1、边塞词
唐人有边塞诗,也有边塞词。就敦煌边塞词来看,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在唐代边塞词中占有重要地位。保家卫国是敦煌边塞词中最突出的重大主题。如周绍良《补敦煌曲子词》第八首上片:“大丈夫汉,为国莫思身。单枪匹马盘阵。尘飞草动便须去,无复进家门。”不仅男儿如此,巾帼英豪亦不示弱。第九首下片:“女儿束装有何妨?装束出来似神王。宁可刀头剑下死,夜夜不便守空房。”有些词还真实地描写了戍边士卒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境况,有的则反映了边地的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如S.5637《何满子》之三:“城旁猎骑各翩翩,侧坐金鞍调马鞭。胡言汉语真难会,听取胡歌甚可怜。”呈现出边地胡汉杂居而又和平相处的特有生活图景。
2、闺情词
主要反映妇女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情态,与唐宋文人词中多以贵妇、歌伎为描写对象不同,敦煌词所写多为中下层良家妇女,而且许多作品也正是出自她们之手,因而读来情真意笃,倍感亲切。其内容主要为闺妇思念征人,或妇女想念丈夫或情人,或描写民间女子歌舞和游赏等。如《云谣集·凤归云》之二上片:“绿窗独坐,修得为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得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碛里,只凭三尺,勇战奸愚。”
3、咏时事词
咏写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有名人事,或歌颂盛世太平,或赞美敦煌守将,或叙写重大事件发生的实况。如P.3128《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邦,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4、咏社会民情风俗词
涉及面广泛,或反映民间风尚习俗,或写儒生士子生活,或表现旅子情思,或表达男女间的爱慕等。如S.6537《剑器词》之三描写当时人们喜好的剑器舞:“排遍白旗舞,先自有由来。合如花焰秀,散若电光开。喊声天地裂,腾踏山岳摧。剑器呈多少,浑脱向前开。”写男女爱情的P.3251《菩萨蛮》:“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罗衫香袖薄,佯醉抛鞭落。何用更回头,谩添春夜愁?”
5、咏物词
咏诵月、马、燕、雁、剑等,不重于描其形貌,而重在写其情意和精神,类似写意画。如S.6537《乐世词》写孤雁的孤独飘零:“失群孤雁独连翩,半夜高飞在月边。霜多雨湿飞难进,暂借荒田一片眠。”
6、咏佛道词
或咏佛地的形胜灵异,或咏佛子礼佛的虔诚,或写道士生活环境之美及闲适之情等。
四、佛曲
佛曲,属佛教音乐,本指唱经或赞叹歌咏佛经的声调,即所谓梵呗,其发声形成一定曲调,如同歌曲。佛曲也就是专为佛赞而设的曲调,与之配合的歌辞便是作为文学文体的佛曲曲词,其体式接近敦煌词。
敦煌佛曲,或在音乐上仍基本保留由印度传来的调子,曲词也译自梵语,连其中的和声也为译音,用以唱经劝世,如《流俗悉昙章》8章和《佛说楞伽经禅门悉昙章》8章;或在音乐上仍用原有曲调,而曲词内容则系新作,与佛教无关,如《婆罗门》;或不再采用原有曲词,而借用燕乐或民歌曲调以唱经劝世,如《百岁篇》、《五更传》、《十二月》等调,就被用来唱诵佛教内容。
若严格地说,真正典型的敦煌佛曲,即曲调专为佛赞而设而内容也纯为咏叹佛门之事者,约有《悉昙颂》(16首,P.2204等)、《好住娘》(14首,P.2713等)、《散华乐》(7首,S.0668等)和《归去来》(15首,P.2066等)等。
佛曲为敦煌歌辞增添了新形式,表明敦煌文学敢于和善于大胆引入异域文学而为己用的开放态度。
五、俚曲小调
敦煌俚曲小调,是以《五更传》、《十二时》、《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
等音乐形式吟唱的。它不同于佛曲,其中有的是唱诵佛教内容的,有的则是歌咏世俗生活的。即使歌唱佛教内容的,也非典型的佛曲作品。
俚曲小调为真正的民间文学作品,历史悠久,群众基础广泛,易于在民间流行。它一般按时序歌唱,以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和思想。如《五更传》以五更更迭为时序,《十二时》以一天中十二个时辰为序,《十二月》按一年中的月次歌唱,《百岁篇》以年岁为序,《十恩德》则把母亲养育子女的过程分为十段而依次歌唱。
俚曲小调语言通俗易懂,抒情率直真诚,情感质朴深切。在表现形式上以“套”出现,以时序组织篇章,虽篇幅一般较长,容量较大,但易于记诵传唱,乐于为民众接受。如《发愤十二时》(P.2564、P.2633等):“平旦寅,少年劝学莫辞贫,君不见朱买未得贵,犹自行歌背负薪。日出卯,人生在世须臾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食时辰,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是珍。……夜半子,莫言屈滞长如此,鸿鸟只思羽翼齐,点翅飞腾千万里。鸡鸣丑,莫惜黄金结朋友,蓬蒿岂得久荣华,飘飘万里随风走。”
此外,敦煌文学中还有一种民间唱词,或在标题中,或在某几个小段开头或结尾,标有“儿郎伟”字样。它们多为六言通俗韵文,有时是四、六言韵文,偶有间以五、七言者。这类作品主要出现在民间岁末驱傩仪式、建房上梁仪式和婚礼过程中障车仪式的唱诵中。迄今尚不知此类作品所依之曲调的原有调名或者原来是否有调名,因而一般便据“儿郎伟”三字而称其曲调及歌词为《儿郎伟》,并将其作为俚曲小调之附体。那么“儿郎伟”三字究竟是什么意思,长期以来并不清楚。近有学者认为,“儿郎伟”实际上是象声词,即“哎哟喂”,是在上述这些仪式所唱歌词中发出的感叹声。
六、散体文
敦煌散体文类作品,或称敦煌文,是指具有文学色彩的散见于敦煌遗书中的表、疏、状、牒、书、启、帖、碑、铭、传、论、录、说、邈真赞、祭文、杂记等等。这些作品虽大多为治实之作,有的属于各种官私文书,但抒情、状物、论理、表意,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富有文采,生动地反映了敦煌及西北地区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因而亦应归入文学作品之列。
表、疏均为臣下进奏帝王之文,所谓“陈情为表,陈事为疏”。重要的表有《张议潮进表及朝廷批答》(S.6342)、《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S.4276)、《灵武节度使表状集》(P.3931)、《沙州百姓等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P.3633)、《王锡上吐蕃赞普表》(S.3201背)等。语言大多工美华丽。敦煌的疏多半是供神佛道场之用,如各种镇宅疏、布施疏、回向疏、礼佛疏、转经疏、追念疏、请宾头庐疏等,一般写得比较严肃、虔诚,行文亦很讲究四六文采。
状、牒在敦煌文书中有数百件,多为官文书。写得较有文采的如《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P.2992)、《肃州防戍都给归义军状》(S.0389)、《凉州节院押衙刘少晏状》(S.5139)、《长安三年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大谷2853)、《军资库司牒》(S.6249)等。此外还有不少寺院用状、牒亦很讲究行文炼句,如《吐蕃寅年正月沙州尼惠性状》(P.3730)、《释门法律庆深牒》(S.3876)、《大宋国沙州灵图寺授菩萨戒牒》(S.4482)等。
书、启主要指信札函牍一类交往通讯性文字。敦煌书、启类作品很多,与一般公文相比其体式较为自由活泼,或议论指事,或抒情表意,或状物绘景,生活气息浓郁,性格特点鲜明。有些书、启构思精心,文采飞扬,足可称道。如窦昊《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P.2555),约写于唐肃、代宗间,为吐蕃大军威逼压境的危机情势下刘臣璧写给吐蕃上赞摩的一封私信,目的在于劝说吐蕃休战言和。信中言辞不卑不亢,叙事陈情张弛有度、严婉并用,既语势咄咄,不失王朝威仪;又娓娓道来,寓兵势于人情常理的游说之中,展示了一种淋漓尽致的雄辩风格。
帖,也是一种应用性文书,有些相当于往来函件,有些名为转帖,为相互通问事项所用,如行人转帖、渠人转帖、社司转帖等。行文大多简洁明了,流畅质朴。
碑、铭、传、祭文,均以记人为中心,皆系作者精心撰写,刻意点染,以图传之后世,因而颇具文采,且史料价值甚高。敦煌碑文有14篇,铭文多为墓志铭,有10篇。所纪均为敦煌达官显贵、名僧大德,如张淮深、索勋、李明振、洪辩、罗盈达等。传记类作品有别传和家传,如《鸠摩罗什别传》(S.0381)、《南阳张延绶别传》(P.2568)、《敦煌氾氏人物传》(S.1889)等,遣词炼句讲究。敦煌祭文有行香文、亡考文、亡孩文、追福文、忌日文、临圹文等,还有祭畜文(祭马、祭驴等)。哀思悲情,溢于言表,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民俗风情。
论、说二体性质相近,又有区别。论,系论断事理的文字;说,早期为游说之辞,后偏重于说明性、解说性文字。《茶酒论》(P.2718等),以茶和酒二者谁个重要、谁有功勋展开辩论,妙语连珠,隽词迭见,诙谐成趣,令人叫绝。
录,为记载言行和事物的册籍。最有名的为《敦煌录》(S.5448),记载敦煌地区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和神话传说,堪称一篇优美的游记。
敦煌文中的杂记作品,包括写经题跋、学郎题记、功德记等,内容庞杂,数量众多。功德记主要记述、颂扬功德主修寺造窟或做佛事的事迹,文笔雅致。如《莫高窟功德记》(P.3564)、《莫高窟再修功德记》(P.2641)、《河西节度司空造佛窟功德记》(S.4245)、《敦煌社人平诎子一十人创于宕泉建窟一所功德记》(P.2991)等。其中《河西节度司空造佛窟功德记》记载了曹议金及其回鹘夫人天公主等“割舍珍材,敬造大龛一所”的事迹,言辞华丽,叙事清晰。
邈真赞,或曰写真赞、邈影赞、图真赞等,即人物像赞。邈,即描绘、画像;真即生平事迹;赞即称赞。唐宋时期敦煌社会上层人物多在晚年或病危时请人画像、撰写生平并作赞,为的是留下容貌德绩,供亲友后人瞻仰祭奠。敦煌邈真赞约存近百件,其赞主(重复者不计)约90人,绝大多数图像无存,仅留人物事迹与赞。它们记载了一大批敦煌著名人物的生平,如悟真、罗通达、张良真、李绍宗、康通信、浑子盈、吴法成、张安信、薛善通、张保山、梁幸德等,对于敦煌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在意识形态方面,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社会评价人物德行风范的标准和社会向往。从文学角度看它们是以当时当地具体人物为对象,通过美化的语言文字加以表达的治实文学,体式上多采用齐言辞赞体或序赞合成体,叙事简洁,感情饱满,有颂有悼,情绪迭宕,读来音节顿挫,朗朗上口。
第四节
敦煌文学杂著
敦煌文学杂著,包括书仪作品、童蒙读物、寺庙杂著等。其中童蒙读物已在本书第五章中言及,这里不再赘述。
一、书仪
书仪,即书牍文范,主要用来为书信一类实用性文书的写作提供一套文体规范和用语模式。书仪约起源于魏晋,据云流传至今的最早传世作品为西晋索靖的《月仪帖》。唐代传世书仪极少,可能仅有台北故宫研究院藏唐人《月仪帖》。敦煌文书中则保存了近百件唐五代时期书仪,经周一良、赵和平等的整理研究,已摸清了其基本面貌和许多重要问题。
敦煌书仪依其内容约可分为以下四类:一类是朋友书仪,类似唐人《月仪帖》,又称“十二月相辩文”,计有S.6180、P.3375、S.5660、P.2505、P.2679、S.6246、P.4989等10余件。它们均为唐代前期作品。其基本结构为,开头为年叙凡例、节候用语,然后按一年十二个月编排,每月给远地的朋友一通书札,朋友亦回信答书一封,互叙思念渴仰之情。多数信札是边塞的游子写给中原朋友的。
第二类为综合性书仪,或曰吉凶书仪。主要写卷有:武则天时期书仪(P.3900)、杜友晋《吉凶书仪》(P.3442)、杜友晋《书仪镜》(S.0329+S.0361)、杜友晋《新定书仪镜》(P.3637等)、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一部并序》(S.6537)、张敖《新集吉凶书仪》(卷上P.2646等、卷下P.2622等)、张敖《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P.3502背)、唐前期书仪两种(S.1725、P.4024)、吐蕃占领敦煌时期书仪(S.1438)、晚唐书仪(P.4050+S.5613)、五代《新集书仪》(P.3691等)。吉凶书仪是唐代书仪中内容最丰富、史料价值最高的一种,几乎涉及到当时士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直可以说是士大夫们的生活指南,或曰行动准则。主要内容包括节候赏物、公移平阙式、祠部新式、诸色笺表、僚属起居、吉凶凡例、四海吉书、内外族吉书、妇人吉书、僧道吉凶书、门风礼教、国哀奉慰、四海吊答书、口吊礼仪、诸色祭文、丧服制度等等。
第三类是专门用以公务往来的表状笺启类书仪。多数内容为应酬官场中的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书、启、状之类范文。如刘邺《甘棠集》(P.4093)、郁知言《记室备要》(P.3723)、《新集杂别纸》(P.4092、S.5623)、《刺史书仪》(P.3449+P.3864)等。
第四类是专门用于一些特定场合的文范。如放良文、放妻书、祭文、结社文等,以及一批释门文范,如《礼佛文式》(P.3819等)、《释门应用文范》(S.5957)、《祭文范例》(S.4364)、《愿文范例》(S.4364)等。其中《释门应用文范》包括二月八日文、启请文、开经文、散经文、转经文、四门转经文、灯文、临圹文、三僧尼舍身文、亡妣文、脱服文、难月文等。
如以书仪的文学性为标准来衡量,有的学者则将敦煌书仪分为如下三类:仪注型,主要指作品彰示的文书格式,着重体现封建礼式规范,如杜友晋、郑余庆、张敖等人的一些书仪;专题型,指那些承袭魏晋《月仪》之类而又有某种变异、思想内容相对专一的书仪,主要有朋友书仪、释门文范、官牍样式等;实例型,指为书信等写作提供实际例子的书仪类型,其用意不在明示格式,而在于使人从中体会写法,如放妻书、分家书、结社文等。
敦煌书仪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史料,反映了尊卑森严的社会等级关系,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民间岁时文化和浓郁的民情习俗,体现了唐五代士庶阶层的行为、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显现了敦煌社会生活中一些相当重要的历史影迹。如节日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敦煌书仪对于唐五代各种节日的来源、节庆内容、赏物名称、休假天数等的记载甚为翔实,这在传世史籍中是较少见到的,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人们的思想和信仰方面某些深层次的东西。
敦煌书仪在文学性上亦颇具特色。作为实用性文字的写作,书仪自然要受到文体程式本身的制约,但它们并不因此而拘泥,不仅把相关文体的格式要求标注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表达方式上殚精竭虑,不少作品显示出相当高的文学水准。许多书仪注重从生活源流中汲取题材,不仅少有呆滞刻板之感,而且不少题旨显得新颖别致,使我们窥察到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历史遗闻和富有时代、地域气息的人情世态。如《刺史书仪》围绕封建时代官员候补得替前后的种种情事发态命题,把官员罢任后赴京候缺途中的那种惶惧心理、官员除授新职后四处叩拜的情景描绘得具体入微,活灵活现。
书仪作品语言结构基本上采用骈体,注重文章的辞藻华丽和音乐和谐,一些作品在抒情状物方面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水乳交融的境界。如《朋友书仪》中写仲春二月边地友人之思:“分颜两地,独凄怆于边城;二处悬心,每咨嗟于外邑。月流光于蓬径,万里相思;星散彩于蒿蓬,千山起恨。且兰山四月,由结冷而霜飞;灵武三春,地乏桃花之色。蒲关柳媚,鱼跃莲晖,蜂歌绕翠叶之欢,蝶舞戏红芳之乐。愁人对此,倍更相思,远念朋友,何时可忘?”写景清丽,抒情真挚。
敦煌书仪还富有口语辞色,如“口吊辞”、“妇人吊辞”、“贺正语”、“贺天公主语”、“贺本使语”、“赐物谢语”、“贺破贼语”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口头用语都是在各种场合下的正规用语,由此可揆当时书面语言通俗化的进展,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寺庙文学作品
敦煌自古为佛教胜地,唐五代时期又是道教、祆教、摩尼教、景教流行之域,因而敦煌文学中宗教方面的作品数量可观。除以上所介绍的讲经文、变文、诗、词、佛曲等中宗教题材的大量作品外,还有诸多常见体式的寺庙文学品类,如偈、赞和各种佛事应用文等。
偈是梵语“偈陀”(Gatna)的简称,本为佛经以及礼佛仪式中的唱颂词,有时也译作偈颂。佛家偈文于《大藏经》中比比可见,但大多偈文出现在经中或经后,单独成篇者甚少,且语言散化、抽象,又不押韵。而敦煌偈文则多数独立成篇,语言形象、押韵,文学色彩颇浓。
敦煌遗书中的偈颂约有80多件写本,它们反映了释门生活的诸多方面,或诵咏佛祖、净土,或赞扬功德修行,或唱颂出家修道和佛事活动。如《先洞山和尚辞亲偈》(S.2165):“不好浮荣不好儒,愿乐空门舍俗徒。烦恼尽时愁火灭,恩情断时爱河枯。六通(根?)戒定香风引,一念无生慧力扶。为报北堂休怅望,譬如身死譬如无。”此偈为晚唐禅宗高僧筠州洞山悟本大师良价所作,倾诉了作者对佛理执着信仰和追求的信念。
赞,在我国源远流长,秦汉之后历代有之,如东汉班固《离骚赞序》、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各篇篇末的《赞曰》等。敦煌赞体与此不同,它是由赞佛兴起的,是佛教传入后随着高僧译经的盛行和礼佛的普遍化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起初赞只限于礼佛范围,后来释门佛子也自撰了不少赞文。赞的内容也不完全限于佛门,出现了孝道赞、父母恩重赞、景物赞、景教赞等,不过大量的仍是佛赞。
敦煌赞文内容丰富,或赞佛祖,赞净土和佛典,赞释门三宝,或赞佛子出家修行,赞佛教道场,赞佛教名胜等。如《太子入山修道赞》(P.3065)、《悉达太子赞》(S.5487、北8441)、《五台山赞》(S.5573、S.5487、L.0278、北8325等10余件)、《游五台山赞文》(S.6631背)、《送师赞》(P.3120)、《净土乐赞》(P.2130)、《金刚经赞》(P.2039)、《法华经廿八品赞》(P.3120)、《开元皇帝赞金刚经》(P.2049)等。佛祖赞大多始于佛祖出家,终于佛祖涅槃,类似长篇佛传叙事诗,以生动曲折、波澜起伏的情节和参差多变的句式,给人以感染和震撼。如《悉达太子赞》中描写释迦救度罗睺母子出火坑情景:“若是世尊亲子恩,火坑速为化清凉。清净如来金色身,多劫曾经患苦辛。今日出离三界内,救度众生无等人。”淋漓酣畅地颂扬了释迦的慈心和神力。
佛事应用文,应用于具体的佛事活动中,数量繁多,宗教实用性很强。从内容上看主要有发愿文、还愿文、祈愿文、启请文、礼佛文、礼忏文、礼赞文、戒忏文、庆幡文、庆像文、庆经文、庆钟文、散经文、燃灯文、施舍文、施斋文、散食文、愿斋文、禳灾文、安伞文、道场文、患文、追福文、叹圹文、脱服文、祭僧文、行香文、唱道文、平安文、布施文、转经文、行城文、印沙佛文、回向文、回施文、皈依启请文、布萨文、劝善文、受戒文、十念文、请四方佛文、赛天王文、无遮大会文等等。
这些应用文既有散体,也有韵体,大多语言洗炼,文笔庄重,带有神秘色彩,并注意运用多种修辞方式和表现手法,极尽论说表意之能事,以宣扬释教。如《十愿文》(S.4504背):“一愿三宝恒存立,二愿风雨顺时行。三愿国王十万岁,四愿边地无刀兵。五愿三塗离苦难,六愿百病尽消形。七愿众生行慈孝,八愿屠儿莫杀生。九愿劳行得解脱,十愿法界普安宁。眼愿不见刀光刃,耳愿不闻怨(冤)枉声。口愿不用随(违)心义(意),手愿不杀一众生。总愿将来持弥勒,愿备将当入化式(城)。”通篇紧扣一个“愿”字,并由心而推及眼、耳、口、手,最后以“总愿”作结,通俗明快,朗朗上口。
第五节
敦煌学与语言学研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语言学方面的资料也不少,不仅有关于汉语音韵、训诂、文字的写卷,也有大量可供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的语料,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它们对于研究中国文字、语言的发展演变颇具重要意义。
一、敦煌韵书
敦煌韵书是指敦煌文书中按照字音分韵编排汉字的写卷。我国初期的韵书最主要的是成书于隋仁寿元年(601年)陆法言的《切韵》,但可惜该书早佚。
据禇良才的统计、研究,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韵书目前所知有26种,多为唐五代《切韵》系统的写本,少数为刻本。其中陆法言《切韵》的传写本有6种(S.2055等),使我们得以一窥《切韵》之原貌。该书所存主要是平声、上声韵,分为193韵,收字较少,训释简约,常用字大多不释。另有一种韵书以《切韵》为底本,在收字和训释方面有所增加,原注之外多半还加上按语,除平、上声外还有入声。又有一种增训加字本《切韵》,其分韵和韵次虽与《切韵》相同,但在收字和训释方面增加内容较多,取材较广。
除上而外,敦煌韵书还有:王仁煦作于神龙二年(706年)的《刊谬补缺切韵》(P.2014、P.2015);孙愐作于开元二十年(732)的《唐韵》,为迄今唯一所存《唐韵》平声韵写本,收字和训释较前均有大量增加;五代刻本《切韵》,其特点是分韵多,收字广,注释详。
上述这些《切韵》系列的韵书,不仅对于我们考究《切韵》的原貌和中古音系,探讨从《切韵》到《广韵》的发展演变十分重要,而且由于它们在不断增修中还收录了大量口语,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文字、语音和词汇的发展甚有意义。
二、敦煌字书
敦煌遗书中的字书抄本约有百余件,种类多样,既有童蒙诵习的识字教科书,又有解释音义的字典;既有要用杂字的字书,又有刊正字体的字样书,还有解说俗语的字书。
《字宝》,又称《碎金》(S.6204、P.3906等),为唐五代民间流行的通俗字书,以平、上、去、入四声编排入字,每声收字词百余条,所录多为民间口语、俗语以及僻字、俗字语汇,其下注以反切或直音,而少有义释。另有《白家碎金》(S.0619),应为《字宝》的节略本。
《俗物要名林》(S.0617、P.2609等),为依据事物名称分类编纂的一种通俗字书,也是敦煌遗书中收录民间口语词汇最多的专著。所谓“俗务”指世俗间的诸种事物,“要名”即指重要常用事物的名称、文字。本卷对于研究唐五代社会生活、习俗和考察当时西北地区方音十分宝贵。
《杂集时用要字》(S.0610、S.3227等),体制与《俗务要名林》类似,收录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语,分为衣服部、音乐部、农器部、车部、舍屋部、饮食部、屏障部、彩色部等,编汇而成。
《一切经音义》(S.3469、P.2271等),唐初释玄应撰,为佛经音义书,分经解释词语音义,详注反切。
《正名要录》(S.0388),初唐时期的一种字样书,专门用以辨别形体相近字、别体俗书字,指明正字。
敦煌字书复现了唐代字书多产的原貌,提供了一批地区性字书和通俗字典,保存了数以千计的唐五代口语词、大量俗字和西北方音,大大丰富了文字学和词书史的研究。
三、少数民族语言文献
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吐蕃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突厥文、梵文、佉卢文、窣利文、吐火罗文(A焉耆文、B龟兹文)、叙利亚文、希腊文等民族语言文字的文献很多,对于中古时期民族学、语音学、文字学以及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贡献重大。
敦煌少数民族语言文献中,以吐蕃文即古藏文文献为最多,仅英藏、法藏吐蕃文写卷就超过3000件,我国国内藏吐蕃文箧页约万页。这些文书大多写于吐蕃统治时期(786~848年),也有一些此前此后的文卷。其内容除大量与佛教有关的经典、疏释、愿文祷词外,还有相当多的世俗文献,涉及到吐蕃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同时敦煌还有一批用吐蕃文拼写的汉文文献,以及《汉蕃对译字书》(P.2762背)、《汉蕃对译佛学字书》(P.2046)等,真实反映了汉藏语的历史语音情况,是研究汉藏语历史和汉藏语比较的可靠史料。
回鹘文是公元9世纪回鹘民族西迁后至公元14世纪左右使用的主要文字,借自中亚粟特文,其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书现已刊布的有42件,内容包括各种经文、笔记、文学作品以及从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带到敦煌的公私文书、信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于阗语是新疆和田地区古代民族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公元11世纪以后逐渐消失,成为“死文字”。敦煌于阗语文献大部分已获解读,内容主要有佛教经典、文学作品、医药文书、使河西记、双语词表(汉语—于阗语词汇、梵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等,对于于阗历史、语言文化以及于阗与敦煌的交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意义重大。
粟特语为古代中亚粟特地区民族使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的古伊朗语东部方言之一。敦煌粟特语文献大多为粟特人来到敦煌后留下的文字材料,内容有佛经、信札、帐单、诗歌、占卜书和医药文书等。
除藏经洞中庋存的少数民族文献外,莫高窟等石窟中还留下了吐蕃文、西夏文、回鹘文、蒙古文等不少民族文字的题记,近年莫高窟北区又新发现了一批民族文字写本,实可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