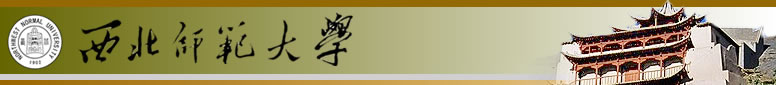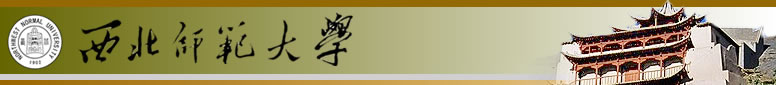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
第四章
敦煌学与民族史和古代民俗研究
敦煌文献对于吐蕃、回鹘、于阗、粟特等民族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对于我国古代婚嫁、丧葬、饮食、服饰、结社、礼仪、岁时、郊游、性爱、禁忌等方面民俗的研究亦很有意义。
第一节
吐蕃史、回鹘史
一、吐蕃史
敦煌文书有关吐蕃的文书,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另外,在我国甘肃省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兰州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有劫余的古藏文文献万余卷。国家图书馆还收藏有四百余件。这批古藏文文献大部分是佛经,但也有不少吐蕃历史、社会文书以及法制文书、文学作品、医学、星占等方面的文献,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其他民族情况的文献。
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
1950, 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藏文写本编号在5000件以上。英、法收藏的残页、碎片及流散国内外的其他藏文写卷,尚未有编目公布。这批古藏文写卷流散国外不久,即引起国际藏学界的极大兴趣,他们在登录编目的同时,也影印刊布了一些文书原件,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数法国的巴考、杜散和英国的托玛斯三人通力合作、拼接整理的《吐蕃历史文书》。.其学术价值已为国际藏学界公认。吐蕃在河西的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政府和一些地方政权仍把藏文作为官方文书,匈牙利藏学家乌瑞在1981年的《亚细亚学报》上以《吐蕃统治结束后甘肃和于阗官府使用藏文的情况》为题,曾披露过归义军时期使用的18件藏文文书,日本藏学家山口瑞凤在1985年出版的《敦煌胡语文献》第一节《吐蕃统治期以后的诸文书》,在乌瑞所举之外,又多列出2篇,其中6篇是沙州曹氏和于阗之间相互交往的文书。这些都证明了,吐蕃统治后的归义军时期(公元8--9世纪)部分地方政权使用藏文文书的事实。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汉文文献,总量上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估计。部分资料密集,如法国所藏P4696号汉文写本,即《顿悟大乘正理决》,是“中印僧侣于八世纪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有关禅的大辩论会”的记录,法国汉学家戴密微据此考释,写成《吐蕃僧诤记》这部名著。但大量的史料,是散见于各类文书的。学者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在浩博的文书堆中去爬梳这些零星的、片断的、不相连贯的资料,披沙简金,钩沉索隐,考究有关问题。日本学者滕枝晃的《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我国学者姜伯勤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等一批论著,尤其是对吐蕃陷落瓜沙、吐蕃统治河西的政治经济与民族关系、归义军收复敦煌等问题的研究,都大量使用了敦煌汉文吐蕃史料,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在敦煌文献中的这批弥足珍贵的古藏文文献以及有关吐蕃的汉文文献,为我们研究吐蕃的历史与文化,以及中古时期吐蕃的社会风貌、伦理道德、政治制度,乃至唐蕃关系、北方民族史、佛教史等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吐蕃史可分为吐蕃占领史、吐蕃王朝史二个专题,即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历史和吐蕃自身的历史。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情况,正史中除了记载吐蕃攻占敦煌的史事之外没有更多的记载。而就吐蕃王朝史而言,可供研究的吐蕃时期的历史文献也非常少。可喜的是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我们研究这两个专题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
安史之乱,唐军东撤,河西、陇右逐次为吐蕃陷落,至清水会盟(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唐与吐蕃以贺兰山、陇山、六盘山为界,承认了吐蕃对河西、陇右的事实领属权。关于吐蕃在这一统治区的施政及社会状况,两《唐书》及其它文献,对此记载很少。间有记录,或语焉不详,或传闻失误,盲从信之。而这一时期的敦煌文书,以其直接、多层面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填补或印证了这一特殊时期纷杂的社会状况。应该说,其内容是比较真实的,可信度是比较强的。
吐蕃于贞元二年(786)占领了沙州(敦煌),随后在敦煌设置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对其进行了长达60余年的统治。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王尧、陈践的《吐蕃职官考信录》、日本学者山口瑞凤的《吐蕃统治的敦煌》、藤枝晃的《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等一批力作,基本上已经勾勒出吐蕃时期政治、军事体制的轮廓。吐蕃占领敦煌后,按其本身的制度在敦煌设立官制和行政建制。敦煌写本P•1089是一份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职官及其职司一览表,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吐蕃设置的各种行政机构和官员的情况。在这一职官体系中有机密大书记,在机密大书记下又有机密信使、机密收集官、机密传布官、机密书吏等。另外吐蕃在敦煌还设有“节儿”一职,王尧认为“节儿”是吐蕃统治沙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吐蕃官制中一城一地的守官。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节儿”执掌沙州的军事、财政和司法大权,其上司是节度使,属官有都督、部落使和判官等。
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吐蕃统治敦煌的军政职官序列已经基本清楚,大体是:瓜州节度使(留后使)——瓜州大监军——沙州节儿论——乞利本——大都督——监军使——副节儿——小都督——(汉人)观察使——(吐蕃人)部落使——(汉人)副部落使——(汉人)小节儿——岸武库令——(吐蕃人)沙州料敌防御都使——(吐蕃人)小千户长——(汉人)副小千户长——(汉人)大税务官——乞利本长书论等。
吐蕃占领敦煌(沙州)后,按其自身的军政建制,结合敦煌唐朝旧制,还建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社会基层组织。唐朝地方行政区划是道、州、县三级,县以下设乡、里。沙州在吐蕃占领前设13个乡,即敦煌、莫高、神沙、龙勒、平康、玉关、效谷、洪池、悬泉、兹惠、洪润、寿昌、从化等。吐蕃占领以后将其本部军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的乡里制度相结合,在敦煌地区实施了废乡设部落的政策,基本上以唐朝的乡为单位设置了军部落、民部落和通颊部落3种类型的部落,以部落制代替了原有的13个乡的建制。
杨铭、刘忠等结合敦煌文书记载,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推行的部落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认为在吐蕃统治期间曾设置过僧尼、道门亲表、上行人、下行人、丝棉、曷骨萨、悉董萨、中元、宁宗、撩笼、通颊等十二个部落。部落之内,吐蕃又将其本部的将、十户制与唐代的乡、里、邻、保制相结合,实行了将、团头下制。从而使该社会基层组织在蕃占敦煌时期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职能。
王尧、陈践《敦煌藏文写卷P.T.1083、1085号研究》中认为,部落是吐蕃当时在军事部落联盟制下的基本军政组织,它是区域性与血缘性结合的组织,也是军事与行政结合的组织。部落长官称为部落使或千户长。敦煌文书中,以stong-sde(东岱即千户)来对译部落,以千户长(东本)对译部落使。
日本学者山口瑞凤、我国学者荣新江的研究表明,790年设置有“行人部落”、“道门亲表部落”、“丝绵部落”、“僧尼部落”等。820年前后,增置军事系统的阿骨萨(曷骨萨或纥骨萨),悉董萨(思董萨或丝董萨)部落,上、下部落。820年又增置通颊军部落。部落有部落使,下设将,将有将头等。姜伯勤对“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及该部落设置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证明该部落是由道士、女官及有关内亲、外戚组成的。荣新江在其《通颊考》一文中还对敦煌通颊部落的来历、在吐蕃军政系统中的位置,以及通颊部落的消亡情况作了考察,认为敦煌的通颊部落是吐蕃占领者镇抚百姓的重要军事力量。
金滢坤通过总结诸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各个部落出现的时间列表进行了说明:

敦煌文书中还有吐蕃王朝颁到沙州的诏令文书,也有敦煌等地的官府或民众的上状,如P·T·1089,《戌年(830)敦煌官吏呈请状》叙述了凉州、沙州各级军镇的职官体系,要求改善待遇,是今天研究吐蕃王朝蕃汉官制和机构设置的重要资料。此外还有不少反映告身、土地、税收、驿传、军制等方面的文书,这些文书不仅仅反映的是敦煌一地的情况,而是看作反映吐蕃王朝整体的面貌。
敦煌文献中的古藏文文书以及有关吐蕃的汉文文书不仅仅是有关吐蕃统治敦煌的资料,也包括吐蕃王朝本身的一些史籍和文献,基本上反映了吐蕃王朝早期的历史进程。
上面已经提到,早在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巴黎大学任藏文教授的巴考和杜散与牛津大学的教授托马斯合作出版了《吐蕃历史文书》一书。当时我国藏学学者于道泉在英法等国游学、任教和旅居,为巴考的入门弟子,回国时曾携此书而归。王尧、陈践将该书译为汉文,译名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980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近期黄布凡、马德又对这一文献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译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吐蕃王朝编年史》,共三件写本(P.t.1288+S.t.750、Or.8212.187),按年代顺序记载每一年内吐蕃王朝的大事,包括会盟、征战、狩猎、税收等,实际上是吐蕃王朝的编年历史。开头部分是几年合在一起的总结性记录,涉及到吐蕃尚未掌握文字的年代,显然是以后的追述。一件缀合写本的内容是从狗年(650)至猪年(747),一本是羊年(743)至龙年(764),共115年,可以互相印证和补充。这部编年史是研究吐蕃历史的最重要史料,其中有关与唐朝征战的历史记载,与唐朝史籍不完全相同,而且其中还有许多吐蕃与周边民族和政权交往的历史,为唐朝文献所无,更为珍贵。
《吐蕃王朝大事记》(P.t.1286+P.t.1287),以赞普为单元记述一代赞普在位期间的大事,从传说的聂赤赞普时代,到吐蕃王朝最辉煌的赤松德赞时期,为我们研究早期西藏历史和吐蕃王朝内部的情况,提供了详细的内容。
涉及吐蕃王朝历史的还有,《小邦邦伯与家臣名表》(P.t.1286/1),记录了吐蕃王朝兴起前,青藏高原上各个部落或邦国的情况,有十七个君长和二十三个辅佐大臣的名单。《吐蕃赞普世系表》(P.t.1286/2),记录了从吐蕃王朝远祖聂赤赞普以后三十九代、四十一位赞普的名字和世系,也包括十六位赞普妃子的名字。《崇佛赞普名录》(P.t.849),记载印度和吐蕃崇佛的国王、赞普和大德的名字,所记吐蕃赞普的名称可以补上述《吐蕃赞普世系表》之缺。
敦煌文书中还有一些反映吐蕃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文献,《吐谷浑大事纪年》(VoL·69,fol.84)就是附属吐蕃的吐谷浑王在706——715(一说634——643)九年间的活动,包括婚姻、会盟、朝觐、征伐、税收等。这正好可以弥补汉文史料只记归附唐朝的吐谷浑王事迹的缺陷。《敦煌古藏文本(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
是五位回鹘使臣撰写的出使吐蕃等地的报告,记述了吐蕃北方突厥、墨缀、契丹、乌护、回鹘等30余大小部落的名称、地理位置以及生活习俗等,是研究8——9世纪中国北方诸民族的重要历史文献。
二、回鹘史
回鹘史文献主要包括回鹘文文献和汉文文献二类。回鹘文文献均出自莫高窟,具体地点有三处:一是藏经洞,约50余件;二是北区464窟(伯希和编181窟),约363件残片(含蒙古语13件残片);三是其他洞窟,仅数件(多为册子装)。藏经洞出品均为唐末宋初文献,哈密屯整理公布了其中《善恶二王子本生经》(即《报恩经讲经文》),后又整理公布了另38件(缀合为36种)其他各类文书。464窟及其他洞窟出品均为元代文献。汉文文献十分零散,主要属归义军时期。
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在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受到北部的黠戛斯的打击,以及天灾内乱的交逼之下,以庞特勤为首的十五部开始大举西迁,一部分进入河西走廊的甘州及其临近地区,一部分到达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天山地区,公元九世纪后半叶,逐渐形成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两个政权。敦煌位于东西两个回鹘势力之间,甘州回鹘就是在归义军的地盘上建立的政权而西州回鹘在壮大的过程中叶从归义军手中夺取了伊州(今新疆哈密)。敦煌归义军政权与东西回鹘王国既有争夺,也有交往,因此,敦煌文书有许多关于回鹘的史料,这些史料极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对我们研究归义军政权与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课题。
甘州回鹘和西州回鹘与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是东西两个回鹘政权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通过敦煌文书,我们才能全面了解其内涵。
进入河西走廊的甘州回鹘起初依附于吐蕃,吐蕃政权瓦解以后,曾暂附于归义军政权;但是,为了自身生存,甘州回鹘又多次与归义军政权及其他部族进行军事争夺。这在敦煌文书中是有记载的。如P·4011《儿郎伟》云:
甘州数年作贼
直拟欺负侵凌
去载阿郎发愤
点集兵钾军人
亲领精兵十万
围绕张掖狼烟
未及张弓拔剑
他自放火烧然
一齐披发归伏
献纳金钱城川
······
另一首P·3270(5)《儿郎伟》也有记载说:
河西是汉家旧地,
中隘玁狁安居。
数年闭塞东路,
恰似小水之鱼。
今遇明王利化,
再开河陇道衢。
太保神威发愤,
遂便点辑兵衣。
略点精兵十万,
个个尽擐铁衣。
直至甘州城下,
回鹘藏□无□。
走入楼上乞命,
逆者入火愤(焚)尸。
······
文书中的“玁狁”系指回鹘,“阿朗”、“太保”应为张淮深。从这两段纪实性很强的韵文可知,曾一度据有甘州,并且阻隔丝路东端。为了再开河陇旧道,张淮深调兵遣将,一举将回鹘击败。
距这次战争不到一年,回鹘势力又起,并且占领了甘州。张淮深遂又点兵征讨,“河西一道清泰”(P·4011)甘州又重新属归义军统辖。
虽然几经易手,回鹘仍然是甘州的主人。S·5139背《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云:“甘州回鹘兵强马壮,不放凉州使人拜奉沙州”,P·3633《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称“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可以看出,到了归义军张氏后期,回鹘不仅雄踞甘州,而且已称霸河西。邓文宽根据敦煌文学作品对张淮深的这两次平定甘州回鹘进行了考证,但由于这些有关回鹘与归义军的资料没有具体年代,所记回鹘居住何地亦不明确,引起学界对甘州回鹘及其与归义军关系的讨论。如荣新江认为亲征甘州回鹘的是曹义金。
五代宋初,回鹘势力进一步强大,不断侵扰归义军政权,敦煌文书P·《太平兴国六年都头安再胜等牒》有此方面的记载。
归义军曹氏时期,曹义金修好周边民族关系,主动与甘州回鹘可汗仁美结为姻亲。一方面嫁其女给甘州回鹘可汗,莫高窟中的题记“甘州圣天可汗公主”即是其女;另一方面,又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莫高窟中也有题记“北方回鹘国圣天可汗的子敕受秦国天公主陇西李氏”。敦煌文书P·2704《曹义金疏》记载:
天公主抱喜日陈忠之谋,夫人陈(承)欢永阐高风之训······东朝奉使,早拜天颜;于阗使人,往来无滞。
这些都证明曹义金与甘州回鹘政权以及于阗政权建立了友善的姻亲关系。
回鹘史研究原来多利用汉文文献,主要讨论甘州回鹘专
题;后来才利用回鹘文文献,提出沙州回鹘等概念。钱伯泉较早提出敦煌在归义军后应有一个沙州回鹘时期,并试图考定这一时期的时限。李正宇则认为沙州回鹘统治沙、瓜地区的时问约从1036年驱逐西夏开始,到1067年又被西夏灭亡为止。杨富学、牛汝极则将藏经洞出品的回鹘文文献均定为沙州回鹘文献,并对所谓沙州回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但由于涉及藏经洞封闭时间这一重大问题,而主张有沙州回鹘时期者多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在北宋皇祜(1054年)以后,与传统见解存在较大出入,归义军之后是否有沙州回鹘时期尚未得到广泛赞同。
另外,敦煌汉文文书中也有关于回鹘内部情况的珍贵资料,如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一说为《说三归五戒文》,是一位汉族和尚在西州开讲的,当中提到不少官名的当地的情况,是研究回鹘的官制、僧官制度、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不可或缺的资料。
敦煌藏经洞还出土了一些回鹘文和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其中有一些是西州回鹘或甘州回鹘寄到敦煌的信件,或回鹘商人在沙州写的帐单,或回鹘人携带来的宗教文书,有的是佛教的,也有的是摩尼教的内容,应当是回鹘信仰摩尼教的反映。有一份突厥化的粟特语文书提到沙州的景教徒,十分珍贵。
第二节
其他民族史
敦煌文献对于研究于阗、粟特、仲云、龙家、等民族、部族的历史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于阗
敦煌遗书中所藏于阗语文献,据目前所知,约在120份以上.现在主要分藏在巴黎和伦敦两地。其中最多的也是佛教文献.如《金光明经》(P·3513)、《菩萨行愿赞》(P·3513)、《出生无边门陀罗尼》(P·2855)、《观自在陀罗尼》、《观自在赞颂》(P·3510)、《妙法莲华经》(P·2782、2029)、《劫王经》(P·1311)、《礼忏文》(P·3510、3513)、《阿育王传说》(P·2798、2958)、《善欢喜譬喻》(P·2834)、《须达孥譬喻经》(P·2784、2896、2957、2025等)、《般若波罗蜜多经》(P·3515)、《文殊师利化生经》(P·4099)等。这些丰富的佛教经典证实了中古时期中国一些西行求法的僧人,如法显、玄奘等对于阗佛教盛况的记载。通过这些佛教经典,我们还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于阗的佛教发展史,譬如早期的于阗佛经都是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因此有不少可以与梵文原经一一对勘。但到唐代.情况却有改变,如P·3513号的《金光明经》和梵文原典的差距已经较大。但却和公元703年汉僧义净在中原地区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极其相似,说明此时的于阗佛教已受到中原的影响。又如晚期的一些于阗文佛经还经过了于阗僧人的缩写、加工或解说,已带有鲜明而独特的于阗风格。这一类佛经和一些由于阗人所写的赞文,对我们了解于阗佛教情况都大有帮助。同时,在十世纪初期于阗文佛经的前后.还常常有一些史料价值很高的序或跋,对了解于阗王国的情况,以及于阗和敦煌地区统治者的交往都很有用。
此外,在于阗文卷子中还有一些历史文书,如《使臣奏于阗王奏报》(P·2790)、《于阗王致曹元忠书》(P·5538)、《致金汗书信和奏报》(P·2958)、《致于阗王奏甘州突厥情势》(P·2741)、《沙州纪行》(钢和泰所藏残卷)等。根据这些材料并参照一些其他文书,人们才得以对中古时期.特别是从吐蕃占领到被穆斯林灭亡为止的于阗尉迟氏政权有了一个基本认识,不仅弄清了它的世系、国号、年号以及沙州于阗间的交通路程和民族分布情况,还了解到当时西域的一场十分重要的宗教战争,即于阗佛教王国和占据疏勒的大食伊斯兰教徒的对抗情况。
敦煌的于阗文文献中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如著名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阿育王的神话、迦腻色伽的传说,以及一些抒情诗等等。对于研究于阗文学和音韵学都是宝贵资料。此外还有一些双语词汇表.如汉语——于阗语词汇、梵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也都是十分重要的语言文献资料。
上文已经提到从曹氏归义军政权开始,与西面的西州回鹘和于阗王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特别是与于阗结成婚姻关系,于阗王李圣天娶曹义金女,曹延禄又娶于阗金玉国皇帝第三女,双方保持十分紧密的交往,使者来往不断。于阗王李圣天的儿子太子从德,就长期住在敦煌。这些于阗人还在敦煌开窟造像,为敦煌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敦煌石窟(莫高窟和榆林窟)中,保存有关于阗的绘画资料,有于阗的“瑞像图”,有于阗的供养人像等。
于阗、敦煌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也是丰富多彩的。如P·2826记载了于阗王送给归义军节度使“白玉壹团”,但要换取沙州工匠杨君子到于阗来。于阗盛产美玉,玉一直是于阗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输出品,送往沙州的玉持续不断,其中不少玉石或成品经由沙州运往甘州、凉州、灵州乃至中原地区。同时从上述地区换回的丝绸、佛典、工匠,又补充了于阗王国之所缺。
二、粟特
粟特民族即所谓昭武九姓。隋唐时期,大批粟特人进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成为中国与中亚等地区进行物质和精神文化交流的沟通者。
伯希和根据敦煌发现的唐抄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认为,蒲昌海(罗布泊)南有一粟特人聚落。他还认为这里的粟特人对佛教的流传和景教的东渐都起过作用。池田温最早根据P.3559(C)号《差科簿》考证敦煌城东安城及从化乡为8世纪中叶粟特人聚落,并对这一聚落的形成及消亡进行了探讨。安城位于敦煌城东五百米处,是沙州敦煌县从化乡所在地。该乡有三个里,750年时有三百户,一千四百口人,其中大部分居民来自康、安、石、曹、罗、何、米、贺、史等姓的中亚昭武九姓王国,聚落大约形成于七世纪初。八世纪中叶由于唐朝与大食的斗争激化,加上安史之乱的吐蕃入侵,聚落突然离散。到八世纪末,除了留下祆祠外,聚落完全消失。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到归义军时期,仍有粟特人后裔在敦煌活动。郑炳林对敦煌粟特人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及其在敦煌佛教、农业、畜牧业、商业、手工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陆庆夫也对敦煌粟特人后裔的职业分布、婚姻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及汉化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敦煌藏经洞中还发现了一批粟特语文献,主要是佛经,有译自汉文的佛典,还有正统的经书,也有疑伪经,表明原本信仰波斯祆教的粟特人,到了敦煌以后,受到当地强烈的佛教文化的影响,逐渐皈依了佛教。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在藏文文献中发现的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的汉语数词一至十。
三、仲云
仲云又作众云、众熨、种榅,一般认为仲云源出自汉代的月氏,归义军时期在以大屯城为中心的罗布泊地区建立政权。史籍中有高居诲《使于阗记》记载:
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地无水而尝寒多雪,每天暖雪销,乃得水。匡邺等西行入仲云界,至大屯城,仲云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晋使者,匡邺等以诏书慰谕之,皆东向拜。
这里一方面讲仲云是小月氏遗种;另一方面说仲云国胡卢碛(今新疆哈密一带)为牙帐,其境在沙州以西,大屯城是其活动中心。
敦煌文献中关于仲云的汉文及其他文字的资料多达十几种。P·2760《使臣奏稿》中记载:“仲云一名南山人”。仲云还有另外一个称谓是“南山”。在归义军时期,瓜沙甘等州南部祁连山区,活跃着许多仲云人,是仲云的另一活动范围。敦煌藏NO·1《酒帐》记载:“迎南山酒壹角”;“供向东来南山逐日酒二斗”;“城南园看南山酒一角”等,可以看出南山部族在沙州的活动相当频繁。P·4525《瓜州义郎牒状》也有南山人活动的记载。
四、龙家
龙家又称龙部族,源出焉耆,吐蕃占领安西四镇后开始内迁。
有关龙家源出焉耆的问题,写于唐光启元年(885)的敦煌文书S.367号《沙州伊州地志》“伊州”条下有明确记载:
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斗战,皆禀皇化。
这是认识龙家归属及其迁徙、流布的一条重要史料。由此可知,那些自西而东流散于伊州、肃州、甘州等丝绸之路上的龙家人,当来自焉耆国。
根据写于中和四年(884)的S.389号《肃州防戍都状》载,原住甘州城中的龙家诸部族与甘州城外的回鹘人争战,由于城中粮尽,无法拒守,龙王只得率领龙家人及退浑等族人退出甘州,并入肃州逐粮。从此,肃州便成了龙家的主要居处。也是从此以后,龙家归伏了归义军政权,并时时向归义军“送纳金钱”,以示顺化。写于曹议金执政时期的P.4011号《儿郎伟》讲到甘州回鹘向西发兵,“准拟再觅寸境,便共龙家相煎”,所指正是肃州城的龙家。还有因为这支龙家人来自焉耆,所以P.3552号《儿郎伟》唱辞里将这支龙家人称作“焉祁(耆)”。但无论“龙家”,还是“焉祁(耆)”,所指的对象都是一个,就是进入肃州的龙部落。
第三节
宏富的敦煌民俗史料
敦煌文献中包罗了大量的古代婚俗、丧葬、服饰、饮食、礼仪、岁时、郊游、性爱、禁忌等方面的民俗资料,这些民俗资料为我们展现了唐宋时期在敦煌一带流行的风土习俗。
敦煌民俗所反映出的民俗的传承性,再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某些史籍记载不详、不具体、不确切的民俗,敦煌民俗可以对之有所补充。如周秦以来的婚嫁六礼,往往以南宋《朱子家教》为简化的转折点,而敦煌晚唐张敖的《新集吉凶书仪》已提出“礼经繁综”、“所以综其旧仪,较量轻重……采其的要,编其吉凶”。将六礼简化为通婚、成礼两大阶段,五礼用雁改作一次性奠雁。关于中国古代桃符题辞,一般以孟昶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两句题辞为最早,而在敦煌遗书中则保存了唐代流传于民间的题辞达十三联之多。如S·610《启颜录》背面:“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福庆初新,寿禄延长;”等。从汉代以来的驱傩,史书中只记载了宫廷的活动,而敦煌遗书中则保存了约十四件唐至五代的“驱傩词”,描绘了民间驱傩的实际情况。敦煌民俗有其独特的地方色彩:首先是在民族杂居的影响下,其民俗也包容了多民族成分,如源自胡人的赛袄,少数民族婚嫁的男就女家,祈赛驼马神,胡饼作主食等。其次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为佛教东渐的必由之地,所以敦煌民俗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如二月八行像,一月两次的赛天王,丧俗中地藏十王信仰,预修生七斋等。中古的民俗对当代人来说,只有文字的概念,而敦煌藉助于壁画、白描画等,使人们得以目睹其形象,如婚礼的青庐、新婚夫妇的服饰妆扮、行礼的姿势直至礼雁的形态等,在画面上都有所反映。敦煌民俗内容丰富,是中国民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因为其包含多民族民俗及中外交流的因素,所以也为比较民俗学提供了参考。
一、婚俗
在敦煌文献中有关婚俗的资料异常丰富,其中敦煌“书仪”对婚俗的记录最多。书议就是写信的范本,因为要给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男男女女准备书信范本,所以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包括婚俗在内。在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唐五代时期的多种书议写本,主要是吉凶书议,有唐前期的,也有晚唐五代时期的。如中原士族杜友晋撰P·3442《吉凶书议》、宰相郑余庆所撰S·6537《大唐新定吉凶书议》、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张敖撰《新集吉凶书议》、安西四镇地区行用的《书议镜》、以及五代敦煌十分流行的《新集书议》等。
还有P·3350《下女父词》和P·3284《通婚书》对婚俗的记载尤为详细,为我们提供了我国古代婚礼程序最完整的资料。高国藩通过对敦煌文书的研究,总结出敦煌的婚礼程序有二十三道程序。大概是女父(即女婿)先到女家大门,女方请新郎下马,在男方向女方奉献了绫罗之后,女方向新郎敬上“上门酒”,并诵《上酒诗》,男方要作答诗。进入女家大门、中门、院内土堆和堂屋外的堂基时,都要应物赋诗。如果遇到故意上琐的堂门,要作诗叫门,并诵《至堂门诗》。女家铺设帐仪,延新郎如帐,撒帐以祝吉庆,并咏《撒帐词》。撒去帐幔,新娘才走出堂门,由侍娘用扇遮住,送入帐幕,坐在床上。然后去扇,傧相请女下床,与新郎同吃一盘牲牢(牢为祭祀用的畜牲,即牛羊猪。三牲全备称太牢或大牢,只有猪羊称少牢,结婚的同牢只吃一种羊肉或猪肉)。食后,用无色绵系住二人的足趾,新郎脱掉礼服,新娘去掉头上花饰、帽帼。二人结发为夫妻。然后众人退出,垂帘安寝。婚礼结束。
在敦煌石窟壁画中还有很多婚俗的形象资料,如奠雁礼,中国古代婚礼中,有六个礼仪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日、迎亲。六礼之中,除纳征不用雁外,其他五礼皆用雁。敦煌文献P·3284、P·2646卷中记载有详细的奠雁仪式。这种婚礼仪式,现已不从在了,而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中都有形象的绘制,所用之雁,有的置于新郎新娘前面的地毯上,有的由侍女抱着,有的已抛出帐外放生了。古人婚嫁用雁,有两个吉祥象征,一、雁是侯鸟,南来北往,四时有序,象征一对男女阴阳和顺;二、雁是贞鸟,雌雄成双,一雁失伴,再不成偶,象征爱情忠贞,白头偕老。
二、丧葬
有关丧葬的习俗,同样,敦煌写本《吉凶书议》记载最为详细。从入棺、吊丧、卜宅、大小殓、启柩、送葬、临圹、掩埋、都有相应的礼仪文字。如吊词,就有吊父母亡、吊人翁婆亡、吊人伯叔姑兄姊亡、吊人弟妹亡、吊人妻亡、吊人姨舅亡、吊人小孩亡、姑亡吊姑夫、姊妹亡吊姊妹夫、吊人妻父母亡、吊人女婿亡、吊人子在外亡等各种吊答词,这些都是《开元礼》中所没有的。还有在P·2622《吉凶书议》记载了敦煌葬俗中临圹设祭的内容,“柩车到墓,亦设墓屋,铺毡席上,安柩北首。孝子居东北首而哭,临圹设祭”。P·3765为晚唐的“临圹文”:“卜善地以安坟,选吉祥而置墓,于是降延清众,就此荒郊,奉为亡灵临圹追福,惟愿以斯舍施功德,焚香念诵胜因,资用亡灵所生魂路”。在敦煌丧俗中,当灵车到达墓地后,要举行一次隆重的斋会,临圹设祭。临圹设祭的目的是为亡灵追福。
敦煌丧俗中还有预修生七斋的习俗,七七斋本来是亡人的斋忌,而敦煌人提倡在世之人预修生七斋。P·2003、P·2870、S·2489、S·3147等《佛说阎罗王受记四众逆修生七斋往生净土经》(亦名《十王经》),提出预修七斋的好处:⑴“必出三途,不入地狱”;⑵(死后)“判放其人生富贵家,免其罪过”;⑶“若是生在之日作此斋者,······七分功德尽皆得之,若亡殁已后,男女六亲眷属为作斋者,七分功德,亡人惟得一分”。预修生七斋得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每日二时,供养三宝,祈设十王,唱名纳状”。另外一种是每七作一斋,“如至斋日到,无财物及有事忙,不得作斋请佛、延僧建福,应其斋日,下食两盘,纸钱喂饲”。莫高窟壁画弥勒经变有“老人入墓”得情节,画面上一座座坟墓形制的建筑,有的老人坐在里面,有的老人正被搀扶着走向此处,这是预修生七的形象表现。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一些经变画以及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画等也有丧俗的内容。如灵柩立鸡,避邪鸣阳的丧俗,在第332窟、第148窟《涅槃经变》送殡图和第61窟佛传故事画送殡图中,佛弟子抬的释迦牟尼彩棺上都站立着一只雄鸡。民间认为:“鸡鸣阳出,四时有序。”用雄鸡有以阳引阴,在冥间为死者报晓的象征。
三、服饰
服饰包括⑴衣着,包括用不同质料如棉、麻、丝绸、皮革等制作的衣、袍、裤、裙、帽、袜、鞋等;⑵各种附加的装饰物如头发的夹、簪、钗、梳等,耳部的装饰物如耳环、耳坠,颈部的装饰物如项链,腰部的装饰物如腰带、腰佩等;⑶人体自身的装饰发式、画眉、文身等三类。在敦煌文献中这三类服饰种类都有记载。尤其以《分家书》、《遗嘱》以及寺院的《唱衣历》(叫卖衣物的帐目)中记载详细。如P·3410《吐蕃某年沙州僧崇恩析产遗嘱》列举的服饰有:汗衫、紫绫夹裙衫、绫袄子、白练衫、紫绫履、京皮鞋、腰带等。在北图藏殷字41,S·4577《处分遗物凭》(分配遗物的字据)中还有紫罗裙、白叠袄子、玉带、银钗子、碧绫裙、十二综细褐、十综昌褐、番褐等。
在自身的装饰中,敦煌女子的束发梳髻,表现的最为突出。如高髻,就是头发束的很高,近一尺,若在高髻上饰以金银等物,则被称为宝髻。P·2748《敦煌廿咏》就有“为珠悬宝髻,作璞间金钿”。还有云髻,“云髻,美发如云也”,头发被绕成环形,也称云鬟。《敦煌曲子词集》有“珠含碎玉,云髻婆娑。”的唱词。
在敦煌石窟壁画、塑像的故事画、人物形象、供养人画像以及佛神、僧侣塑像中反映的服饰资料更是应有尽有。从时代上讲,有十六国末及北魏时期胡服,隋唐时期的宽袍大袖、小袖裙襦、窄衫小袖、襕袍裙履,吐蕃统治时期的吐蕃服,五代宋时期的回鹘装,西夏的党项服,蒙元时期的蒙古装等等。从阶级、等级上讲,有汉族帝王的衮冕、笼冠、通天冠、有文臣的进贤冠服,有宰相的貂尾冠服,有节度使的幞头靴袍,也有普通劳动者如屠夫、泥匠、农民的缺骻长衫、半臂、犊鼻裤、幞头、笠帽等。还有妇女的面部妆饰,如朱红染额、眼睑的“晓霞妆”、“黑眉白妆”、细长的娥眉、宽脸的短眉、以及朱红点唇的“露珠儿妆”,另外还有额面染、贴花钿、花子等等。
四、岁时
敦煌是佛教圣地,其岁时民俗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敦煌岁时民俗大体可分三类:
一类是从事佛事活动的纯佛俗,来源于佛教。如从P·3765《四门转经文》、P·3149《新岁年旬上首于四城角结坛文》可知有四门结坛,从S·2146《置伞文》、P·2854《竖幢伞文》可知有安伞旋城,另外还有上元燃灯、赛天王、印沙脱佛脱塔、二月八日设道场讲经说法行像、释迦忌辰、四月八佛诞、盂兰盆节等。这些佛俗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有的还一直流传到今天,如四月八、盂兰盆节已发展成为我国民间的节日。这些佛俗有如下的特点:一是和佛教信仰有关。二是具有镶灾、植福之功能,如白伞法事的神通、天王的护佑、印沙佛的积德等,和每个人的切身利害紧密相连。三是与中国传统的孝道观念吻合,延寿荐亡,深得民心。四是方法易行,便于普及,如印佛只需在近水之处,用泥团打印脱模即可。
第二类是中国传统民俗,如上元燃灯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下元令节、冬至节等。就拿正月燃灯节来说,敦煌的燃灯是由刳身燃灯供养佛以表至诚演变而来,是群众性的建福功德之举,常有敦煌社邑组织进行。S·5828社条中规定:“本社条件:每年正月十四各令纳油半升于普光寺上灯”。S·527后周显德六年(959)社条:“社内正月建福一日,人各税粟一斗、灯油一盏”。P·4525宋太平兴国七年(982)社条:“新年建福一日,人各炉饼壹双,粟一斗,燃灯一盏”。社司转贴:“右缘年支正月燃灯,人各油半升,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廿一日卯时,于官楼兰若门前取齐”。可见敦煌百姓对燃灯的重视程度。另外三月寒食清明有设乐踏歌、上坟祭拜活动。每个季度末都举行罢四季道场,祈福禳灾仪式。四月八日佛诞辰日有造幡、写经、四月大会、寺院礼佛、求儿女等活动。五月端午节僧官向节度使献物送礼,佛家以受气法供养十方诸佛。七月盂兰盆节要整修粉刷佛堂、设盂兰盆道场、造盆破盆、户内祭拜、造花树、图像写经活动。
第三类是佛俗与我国传统民俗的融合,如元正斋会本是庆祝新春佳节,可又是斋会的形式。罢四季道场、岁末诸巷道场,正是在我国传统祭祀、驱傩的基础上,冠以道场佛事之名。藏钩之戏本是我国一种群众性的游戏活动,经佛教吸收,又添加清斋之会。这也是佛教加速汉化、深人传播的方式之一,使群众在喜闻乐见的活动中,自然地接受佛教的影响,从而在民间生根发芽。例如,驱傩是唐宋时期在敦煌岁末举行的驱祟逐疫活动。届时州、县及节度府各有官办的驱傩队,坊巷有民办的驱傩队,佛、道、祆寺有寺观驱傩队。各队皆有领队、部众及器乐班子组成。不同的傩队,有名色不同的领队者,敦煌文书中所见的有太常、钟馗、五道将军、安城大祆等;部众则分别化妆成佛、道、祆的神将神兵,随队歌唱呼叫是由公私学校的学郎扮演,称为“儿郎”;乐器班子击鼓敲锣,兼充伴奏。敦煌驱傩歌《儿郎伟》的基本句式为四言或六言,偶句押韵,每节之后有音乐间奏。歌词内容主要为祝愿来年国泰民安,家兴人和,五谷丰登、牛羊繁盛,侧重队社会人事的美好祝福,而渲染驱祟逐疫的性质已经淡化。敦煌傩的这种特点成为中国古代傩文化系统中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品种。
五、饮食
在敦煌文献中,记载饮食的社会经济文书也很多,有些学者统计约有700多件,这些文书详细记录了当时敦煌人日常的饮食原料、食物品种名称、饮食器具、饮食礼仪等。还有在敦煌文学作品、敦煌佛教文献中,也有不少饮食方面的资料。45000多平方米的敦煌壁画中,一些形象直观的图画,同样也记录了当时人的饮食场面、食物品种、饮食礼仪以及与饮食有关的内容。
饼是敦煌人的主要食物和种类最多的食品,也是敦煌文献记载最多的食品。在敦煌文献中各种交纳谷物时的记帐,支出面和油的《破除历》、《入破历》,以及P·2641《宴设司呈报帐目》、S·1366《归义军衙府帐目》等都有对饼的记载。其种类有胡饼、蒸饼、煎饼、索饼、饼泚、饸饼、环饼、白饼、烧饼、油胡饼、梧桐饼、菜饼、菜模子、馒头、菇鼓、水饼、乳饼、捻头、粘米饼、龙虎蛇饼、糕饼、侠饼、薄饼、笼饼、饼饮等二十余种。除了饼以外,还有其他不少的非饼类食物,有馎饦、炒面、冷淘、水面、饭、油面、粥(浆水粥、白粥、米浆水)、羹、灌肠面、煎胶面、傲饭、粽子、糌粑、煮菜面、须面等,它们和各种饼一起,构成了敦煌人主要的加工食物品种,是敦煌人膳食结构中最主要的部分。从用酒的帐目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敦煌还有各种各样的酒,如以葡萄、粟、小麦、青棵等为原料酿造的麦酒、粟酒、青棵酒、葡萄酒、白酒、清酒等,还有以呵梨勒为原料酿造或炮制的胡酒等。
六、郊游
在春天寒食节,敦煌人聚在一起“踏歌”,举行春游活动。寒食节一般在清明节前一天或两天,但敦煌的春游活动从三月初开始一直延续到四月下旬。春游最主要的特征是跳“踏歌”舞。“踏歌”是我国古代流行于民间的一种群众性歌舞的形式,人们多在节日集会时,成群结队,手拉手,以脚踏地,在村落间、在郊外、在街头,边歌边舞。如刘禹锡《踏歌词》云:“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S·4705《粮食支出帐》记载:“寒食踏歌羊,便麦玖斗,麻四斗”。说明寒食节春游不仅要跳“踏歌”舞,还要吃羊肉,吃小麦面做的饼。P·3333《菩萨蛮》云:“路逢寒食节,处处樱花发,携酒步金瓶,望乡关双泪垂”。可见寒食节郊游还要饮酒。敦煌研究院藏《酒帐》中有:“十九日,寒食坐设酒三瓮,支十乡里正纳球场酒半瓮”,前苏联藏2905号写本也有“戊午年四月廿五日寒食设坐付酒历”的记载,寒食饮酒有多方面的作用,可以是祭祀、扫墓、会亲、访友、聚餐、招待官员等等。
七、禁忌
敦煌民间有所谓的七种禁忌,在P·2661背“杜康以丁酉日死,不得聚会饮酒,扁鹊辛未日死,不得此日服药。田公丁亥日死,勿此日种五谷,凶。仓颉以丙寅日死,勿此日入学。师旷以辛卯日死,勿以此日作乐。河伯庚申日死,勿此日乘船远行。皋陶以壬辰日死,不得此日劾罪人”。以历史上的传说和真实人物的忌日,来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P·2661背“诸杂略得要抄子”还记载了古代敦煌人出门远行得禁忌:“凡欲远行初发家:东行避日出,南行避日午,西行避日入,北行避夜半,慎之大吉。”“凡欲远行避四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此是四纥。”“凡欲远行千里外,勿三长三短日:正月岁长,每月一日,甲子日长;每月卅日短,癸亥日日短,十二月卅日岁短。”
第四节
敦煌社邑文书
敦煌社邑文书数量众多,有社条、社文、社历、社司转帖等。敦煌遗书中有关社邑的文书有三百余件,莫高窟和榆林窟中的十八个窟有社邑及社人题记,绝大部分属唐后期到宋初之间。这些社邑文书展现了我国古代民间结社方面多彩的内容。
在敦煌历史上,曾普遍流行一种以“社”命名的基层社会组织,它是民众自愿结合进行宗教与生活互助活动的组织。其特点就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和集体的活动来维护集体成员的各种利益,使这些成员能在敦煌这块土地上得以生存和发展。
敦煌的结社活动,据一些学者考证,从西汉昭帝元风年间(前80-前75年),一直到宋、元时期,敦煌地区都有“社”的活动。唐初,朝廷下令从中央到州县乡里恢复春秋二次社祭,以此组成里社和村社。唐及宋初,敦煌除官社外,也盛行私社,被称为“社邑”、“社”、“邑”、“义社”、“义邑”、“邑义”、“邑义社”等。其结社的组织形式,一般为十几人到四十几人不等。有些私社还有专名,如“亲情社”、“兄弟社”、“女人社”、“官品社”、“巷社”、“都官社”、“车社”、“修佛堂社”、“渠人社”、“龙沙社’等。
亲情社主要从事社人间营办丧事的互助活动。敦煌文书中有十件通知社人助葬的亲情社转贴。如S·6981,P3164,S5139背(4),P·3707,S·6532、2894背(3)、2894背(4),
x·1439A,S.2242、3714等。
兄弟社主要有同族人组成,以从事社人间营办丧事的互助活动为主。社司转贴中有五件题为兄弟社的转贴。如S·6981、4660,P·4987、4716,S·6199等,其中三件是通知社人营办丧事的。
女人社是由妇女组成的。如P·3489“戊辰年正月廿四日袿坊巷女人社社条”以及S·527“显德六年(959)正月三日女人社社条”都是。女人社的领导有社官、社长、录事、虞候等均由女尼担任。
官品社由地方官吏结成。如P·2991背《莫高窟素画功德赞文》有“敦煌官品社某公等某人彩集崇逮”等字样。
修佛堂社是为修佛堂而结成的社。其修建的物料工食全靠募化得来,也设有社长、社官、录事等职。如P·4960,
x1410等。
可以看出这些社有的以性别为特征,也有以职业为特征的,还有以同姓宗族为特征的,以及以相邻关系为特征的等等。其结社的成员也很广,有世家毫族与高级僧侣等上层社会人物,也有一般地主、一般寺院僧侣和军队、官衙里的中级官员等中层社会的人们,但更多的是依附于寺院的常住百姓以及各类手艺人等社会下层民众。然而不论其成员来自什么阶层,他们的结社宗旨都大致相同,也非常明确。如P·2041《大中年间儒风坊西巷村邻等共议赈济凶丧章程》云:“所置义聚,备凝凶祸,相共助诚,盖期赈济急难”。S·0527《显德六年女人社章程》云:“遇厄则相扶,难则相救”。S·6537《十五人结社社条》云:“籍朋线而共佐,。······济苦就贫,······割己从他,······”。结社的目的主要为赈济互助即为自己利益,也为他人利益。
上述这类私社,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主要从事佛教活动,如营窟、修寺、斋会、写经、燃灯、印沙佛、行像等。其中有的佛事完成即行解散。另一类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最主要的是营办丧葬,有的还兼营社人婚嫁、立庄造舍的操办襄助,以及困难的周济、疾病的慰问、宴集娱乐、远行和回归的慰劳等。这类社多要求“坚要长久”,社人身死,由子孙继承,有的社存在时间达五六十年以上。许多社则兼具上述两类职能,而传统的社祭,往往仍是这些私社的重要活动内容。
此外,还有在官府组织或管理下的士兵集资买马的马社、管理灌溉渠道的渠社。
这些遍及敦煌城乡的私社,入社者称为社人,亦称“社户”、“社家”,推举社长、社官、录事,合称三官,主持社务,社有集会,一般由录事发转帖通知社人参加。社邑还有若干公共积累,称为义聚。社有社条,规定社的宗旨、活动内容、社人的权利义务、不遵社条的罚则、入社出社的办法等。不少私社在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上受到官府、寺院、贵族、官僚、军将、富户的控制,为之提供变相的赋敛和力役,以及维持社会秩序。有些社的三官就是由官僚、富户、僧人、军将担任,甚至以这些人的名字为社名。
社条又称社案、条、条件、条流、约、凭等。是社邑组织和活动的规约。敦煌文书中有二十余件(其中有复本二件),其中文样六件,抄一件,学郎模仿成人结社习俗写的结会记一件.实用件十余件。社条文样各本详略不同,文字各异。其程式一般先叙述结社宗旨是在儒家礼法或佛教教义指导下,从事朋友问的互助教育、集体祭祀和生活互助,主要是营办丧葬以及春秋二次社祭和三长月斋会。其次叙述组织、活动、罚则的具体条款。如S.6537第一件计有:三官的条件与职权;三长月斋会办法;春秋二次祭社的规定;营葬纳物祭奠及出车办法;济苦救贫;立庄造舍、任职、婚嫁、行役、回归的互助慰问;局席秩序的维持及罚则;社人身份死后由子孙继承及营葬的三驮请赠办法等。其他社条文样无此详尽。也有将七月十五盂兰盆节或正月燃灯或印沙佛列入的,但均有营办丧葬的条款。实用社条除S.3540系为修窟、P·4960系为修佛堂外,多半依据各社活动内容的需要参照社条文样拟成,并按具体情况作一些变动,内容较为简略,主要是营葬办法和罚则,可知丧葬互助是一般结社的主要目的。条后(有些在正文前)列有社人名单,有的名下还有本人签押。从社司转帖及社邑牒状等内容及其中多有“准条”字样,可知社的活动是严格按社条进行的。社邑成立日久或情况变化,往往集议重立社条或对原条修改补充,原条即称为“祖条”或“大条”。修改补充的条款或附原条之后,也有因原条封存、开视不便而另纸书写的。如S.2041即为儒风坊巷社自吐蕃统治期到归义军初期二三十年间四件社条及补充条款的粘合(P.3544,S.2041,P.
3989,S.8160,P.4960,S.6005、527,P.3489,S.3540、2894背(3),P.3691背、4525(11),S.5629及同号复本、6537背(6—7),P.3730背为前引件复本,S.5520、6537背(3-5)、6537背(7-8),P.3536背).
社斋文也称社邑文、邑文、社文。社斋时由斋主延僧念诵的祈愿文。主要祈愿佛佑合社及斋主平安,消灾免罪、求福来世,也有兼及国家升平,节度使及地方官员安泰的。敦
煌文书中的社斋文共四十余件,其中有的是保存在斋仪中的文样,有的则是据斋仪文样添加内容持以念诵的文本。如s.6417(1)社斋文二首后一有“贞明陆年(920)庚辰岁二月十、廿日金光明寺僧戒荣裹自转念”。有“戒荣文本”字样的,即属僧人自备文本,在敦煌文书中有P.3545、3128背,S.4976背、543背(6),P.2226背、2331背、3770、3241背,S.5573,P·3765、3276背,S.5957,P.4608,S.6417二件,P.3122、2058背、2588、3566,S.6923背(3),北新832背,S.5953背、5561,P.3521背,s.6114,P.4966,北地62,S.1173背(1-2)二件,P.2820二件,S.5875,P.3980,Io.Ch.77,S.10563、8178,P.2767背、2547、3806、3722背、2497、4536背、3362背、3678背、4062、2820、4062等。
社历就是社邑收支记录。敦煌文书中共有四十三件,绝大多数是实用文书。其中最多的是社人身故纳赠历,此外有社司便物历、社人纳色物历、社司罚物历、社司破历及一件不能确定事主的麦粟算会。
社司转贴是社司通知社人知会的文书。类似后世的通知单。敦煌社邑文书中,社司转帖数量最多,在二百件以上。其中多数为抄件,有相当数量原未抄完,实用者有六十多件。社司转帖一般要写明集会事由,如助葬,春秋座、座社局席,建福、设斋、设供,有事商量,纳物、软脚、筵设等;各人应携带物品,如面、麦、饼、粟、油、柴、布、绢等,品种和数量视社条规定及聚会事各异,也有帖中不列此项者;接着是聚会时间和地点(一般在寺院门首取齐或在社人家中);后到和不到者的罚则,一般是最后到的二人罚酒一角、不来者罚酒半瓮;然后写明接帖者要速相转递,滞帖者准条有罚,转帖传遍后还给社司,作为通知到和处罚的凭证;然后列发帖时间及发帖者。发帖者一般为录事,也有由社长或社官单发或会同录事发出的。帖文后列社人名单(也有列在帖文前的),接帖者在自己名下书一“知”字或在一侧点一墨点或画指印、签名、画押,有的社条规定,帖到时如本人不在,由家属代接,不得拒绝。有的实用转帖在社人姓名旁还有社司的勘验符号,表示到场及纳物与否。
从敦煌文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诸如“籍朋贤而共佐”、“相共助诚”、“相扶”、“相救”等结社宗旨,不仅明确要求每一位成员必须具有“利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还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具有“集体”的观念;不仅要随时“佐”、“助”、“扶”、“救”他人,更要想到大家一起“共”、“相”而佐、而助、而扶、而救。显然这是以共同利益,以集体利益为上。每一个入社人的个人利益,也显然包含在这个“社”的共同利益当中。尽管单个人的入社目的本来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是为了防自己之“凶祸”,“救”自己之“急难”,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救防不了可能要来的凶祸、急难,因而想通过入社利用他人,利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和争取自己利益;想利用他人,利用集体,救必须考虑他人,考虑集体,这就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基本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