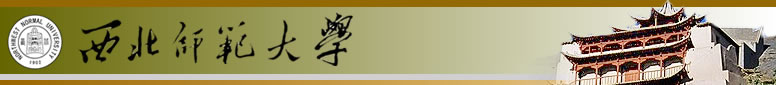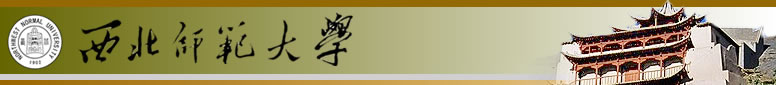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
第五章
敦煌教育、科技文献
第一节 敦煌教育文献
敦煌文献中没有专门记载教育方面的卷子,但是,在各类文献中,有很多涉及到教育和科举。这些史料,不但使我们可以了解敦煌地区的教育及科举方面的历史,对了解封建国家的教育和科举也很有帮助。藏经洞出土文献中的教育史料跨度的时代范围很大,上自两汉下止宋,但以唐至宋初为多,也有部分关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教育材料。材料的内容几乎涉及教育的各个方面,大致可分为学校类、学官类、教材类、学生类等。
一、学校类文献
比较而言,这类文献不是很多,也没有单独存在的卷子,大都需要从其他类文书中选拣。但这类文献的内容比较明确,一眼便知其教育类性质。其中绝大多数是作为其他文献的尾部题记出现的。出土文献反映,敦煌有各类学校,有官学系列、私学系列和寺学系列。官学是指被列入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的州县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并不完全指私家的学校。寺学则是寺院所开办学校。每个学校系列都有多少不等的相关材料存世。
1、官学系列文献
州郡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州学
右在城内,在州西三百步,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该文书作于开元年间,是敦煌文献中关于州学(包括县学、医学)的最详细的记载。此外的材料都是题记类,主要有:
P.3274《孝经疏》卷末题:“天宝元年(742)十一月十八日于郡学写了”。
P.3369《孝经白文》末题:“咸通十五年(874)沙州学生索什德”。
p.3783《论语白文》末题:“文德元年(888)正月十三日敦煌郡学士张园通书”。
P.2859d《占十二时来法》末题:“州学阴阳子弟吕弁本。”时在天复四载(904年)。
P.2578《开蒙要训》末题:“天成四年(929)九月十八日敦煌郡学仕郎张显顺书”。
这里的郡学与州学是同一所学校。敦煌在武德年间初建敦煌郡,后改名沙州,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复名为郡。州郡学名称的变化与唐在敦煌行政机构名称的变更完全相符,可见郡学就是州学。
县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县学。右在州学西,连院,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除敦煌县学外,还有关于沙州所属寿昌县学的记载。P.5034《沙州地志》记:“一所县学。右在县城内,在西南五十步,其(院中,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堂内有素(塑)先圣及先师(颜子之像,春秋二时奠祭)”。寿昌县在今敦煌西南。P.2832《天宝初年敦煌县学状》记:“县学。囗学生匚
,四人柚匚 ,一人守匚 ,人患匚 ,一人祖匚 ,人不匚 ,一十匚
,张元嵩,张承光,吴庭元,王茂囗,件状如”。“县学”、“学生”等字样表明文书是有关县学学生情况的记载。题记所见县学有:
S.4057《佛经》后题:“唯大唐乾符六年(879)正月十三日,沙州敦煌县学士张”。“敦煌县学士”即敦煌县学学生。“学士”一词是晚唐时期敦煌特有的一种学生称谓,最早出现在乾符三年,流行使用于乾符至景福间,后来被“学士郎”逐渐代替。
S.1893《大般涅槃经卷第卅七》末题:“校了。经生敦煌县学生苏文颃书”。经生即写经生或抄经生,是苏文颃的社会职业,其本人身份是县学学生。
医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沙州的医学校与州学同在一个院内。P.2657《天宝年间沙州敦煌县差科簿》记:“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令狐姓是沙州名族,翊卫是要服差役的,但思珍后标明其身份是医学博士,职责在于教授学生,应免除徭役。整簿记录中仅令狐一人戴医学博士衔,与唐朝规定下州设医学博士一人的编制是相符的。
道学。P.3768《文子》末题记:“天宝十载(751)七月十七日道学博士索□林记子校定。”索□林任职道学博士就是教授道家经典的教师。
2、私学系列文献
镇学。北菜十九号《妙法莲花经》背题:“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官武保瑞自手书”。悬泉在初唐时为敦煌县一乡名,晚唐至宋初改名为赤心,另外在悬泉堡(今安西县踏实破城子)设立了悬泉镇。题记中武保会、武保瑞都是悬泉镇人,在镇学读书,故称为悬泉学士郎。
坊学。S.4307《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两条题记,一署名时间为雍熙三年(986),另一记:“丁亥年(雍熙四年,987)三月九日定难坊巷学郎李□□自手书记之耳”。定难坊是敦煌城内一个坊名。
社学。P.2904《论语集解第二》末题:“未年正月十九日社学写记了”。从书写特征看属晚唐时期。
义学。P.2643《古文尚书》末题:“乾元二年(759)正月廿六日,义学生王老子写了,故记之也”。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与甘肃相邻的新疆同样开办有义学:“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
”。“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同时可见私学生即义学生。《唐会要·学校》记唐制:“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
家学。有关家学记载比较多。目前共见九所,分别是:某家学(867年。该年代为大约办学时期,仅限记载。下同)、郎义君学(885年)、李家学(890年)、张球学(889—907年)、就(龙)家学(957年)、白侍郎学(976年至977年)、范孔目学(978年)、孔目官学(978年)、安参谋学(986年)。这些家学大都存在于归义军时期,所属家姓都是地方望族,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如张球,在咸通年间任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后加朝议郎,光启三年(887)权掌归义军书记兼御史中丞,乾宁年间迁节度判官、宣德郎兼侍御史,而且博学多识,后任教于寺学。
3、寺学系列文献
绝大多数寺学的名称在其他文书末题中出现,个别出现在壁画题记或者书仪中,至少有40多号。存在的时代在唐末至宋初间(见下表)。
|
寺学名称 |
文献显示年代 |
出
处 |
|
莲台寺学 |
893年—936年 |
P.3569、P.3833、P.2618 |
|
净土寺学 |
870年—973年 |
S.2614、S.395、S.2894(5)、S.3691、P.2808、P.2504、
P.2621、P.3649、P.2633、P.2570、P.2484、北位六十八背 |
|
金光明寺学 |
905年—922年 |
P.3381、P.3692、S.692、S.1586 |
|
乾明寺学 |
975年 |
P.4065 |
|
龙兴寺学 |
917年—920年 |
P.2721、俄1293、俄1484、莫高窟第199窟壁题 |
|
永安寺学 |
923年—979年 |
S.214、S.1163、S.1386、P.2483 |
|
三界寺学 |
925年—975年 |
S.173、S.707、P.3528、P.3386、P.3189、P.3393 |
|
灵图寺学 |
927年—936年 |
S.728、P.5011、P.3698 |
|
大云寺学 |
958年—962年 |
S.5463、S.778、P.3886 |
|
显德寺学 |
977年 |
P.3170、北盈七十六背 |
二、学官类文献
唐代的州县学教师属于品官,名博士或者助教,有秩。同时,出土资料中还有一些关于归义军时期“国子祭酒”的记载。这里将记载博士和祭酒的材料统称为学官类资料。
国子祭酒。记载国子祭酒的文献主要有碑铭赞和题记两类。见于碑铭赞者:阴善雄(P.2482)、李绍宗(P.3718)、氾府君(P.2482、P.3268)、索公(P.4986、P.4660)、张兴星(P.4660)、张议广(P.4660)、失名(P.2913)、浑子盈(P.5448)、张良真(P.3718)、阎子阅(P.3718)、曹盈达(P.3718)、张明德(P.3718)、阎胜全(P.3718)、薛善通(P.3718)等。见于壁画题记者:其中仅莫高窟第98窟就有35条。两类总共近百条。任职“国子祭酒”者,基本上都带“检校”衔,属兼官。时间上集中在归义军时期。国子祭酒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即负责国家教育行政,属京官。但敦煌曾经有不少担任国子祭酒者,其中最早者是李明振。莫高窟第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记: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其任职始于大中五年(851),这是敦煌文献中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国子祭酒的记载。李明振任“国子祭酒”当属朝廷授予。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和P.4615《李端公讳明振墓志铭》记载,李明振是陇西成纪人,与皇室同宗。大中五年随张议潮兄张议谭等人入长安告捷,倍受关宠,“宣宗临轩问其所以,公具家牒,面奏玉阶。上亦冲融破颜,群公愕然。乃从别敕授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赐金银宝贝。诏命陪臣,乃归戎幕”。在李明振之后,整个归义军时期加戴“国子祭酒”之衔者可知有数十人次,其中包括张承奉、翟奉达(莫高窟第220窟题记)等显赫人物。张承奉是金山国皇帝,翟奉达是归义军时期最著名的学者、历学家,他们出任教育长官,显示出教育对归义军政权之重要。而张承奉等人戴“国子祭酒”头衔是归义军政权保持独立性的结果。
博士。P.2937va《太公家教》末题:“沙州敦煌郡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太学博士宋□达”。这是敦煌教育文献中所见的最早关于太学博士的记载,时间在中和四年(884)二月廿五日。P.4660《都法律氾和尚写真赞》记:“宰相判官兼太学博士陇西李颛撰”。“太学”属于中央官学,这里的“太学”应指州学。莫高窟《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妹夫乡贡明经摄敦煌州学博士阴庭诫”。时间在大历十一年(776)。S.2263《葬录卷上》题记:“归义军节度使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士、将士郎张思贤。”张思贤任职在乾宁三年(896年)前后。宋□达、李颛和阴庭诫、张思贤身份是学校的教师,不过都是兼职。
值得一提的是僧慧菀曾经也是州学博士。P.4660记:“鄯州龙支县圣明福德寺前令公门徒释慧菀”。根据杜牧《樊川文集·敦煌郡僧正慧菀除临坛大德制》记载,慧菀“领生徒坐于学校,贵服色举于临坛,若非出群之才,岂获兼荣之授。勉弘两教,用化新邦”。其中慧菀的职衔是“敦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正兼州学博士”。这封制书颁赐于大中五年(851年)左右。可见,归义军政权初期曾经聘请高僧担任州学博士,释慧菀确实也登台讲学。
P.2623题记:“朝议郎检校工部尚书员外郎行沙州经学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翟奉达撰”。时间在显德六年(959)。翟奉达在任国子祭酒后出任州学博士,他是盛唐时期敦煌州学博士翟通的九世孙,可谓教师世家。这是其与众不同之处。除经学外,他还精通历法,有多种历法著作出手,自天福十年(945年)至显德六年以后一直在州学任教。
S.3768《文子》卷末题记显示,道学的教师为道学博士。道学博士或称道德博士,曾经名玄学博士。
三、教材类文献
1、州县学经学教材
敦煌遗书中,儒家经典总数达百卷以上,有《周易》、《周易经典释文》、《古文尚书》、《今字尚书》、《尚书释文》、《毛诗故训传》、《毛诗音》、《毛诗定本》、《毛诗正义》、《礼记音》、《春秋经传集解》、《春秋左氏抄》、《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解释》、《御注孝经疏》、《论语郑氏注》、《论语集解》、《论语疏》、《尔雅白文》、《尔雅注》等。
根据众多学郎题记看,这十多类典籍都具有教材性质。据此,姜亮夫曾言:“当时(中原)学风,早已西被流沙”。
在众多教材类文献中,保留最多的有《诗》、《书》两类。各种《诗经》写本,以郑玄注《毛诗古训传》和《毛诗音》最受重视。《毛诗古训传》有一部分抄写书法拙劣,个别应是书师所写,还有学生习抄作业。《毛诗音》是关于《诗经》音读的著作,唐宋之际已经散佚,现仅存于敦煌。《论语》是敦煌学校教育中的又一重要教材,主要是《论语集解》和《论语皇侃疏》。研究认为,“敦煌所出论语集解,无虑六七十卷,概皆恶札,差讹百出,盖因为童蒙必读之书,尽出学童之手也”。《论语皇侃疏》在唐代各地学校盛行,北宋时仍作为学校课本,后散佚。日本有唐代传入的皇疏旧本,清朝初年传回中国,收入《四库全书》,但已非原貌。敦煌本《论语皇侃疏》“确为皇疏原形,其式乃合于唐人五经正义之单疏”。这一事实表明,敦煌州县学校选用的教材不但在内容上,甚至在版本上都与唐政府的规定“五经正义”保持一致。这既是唐朝重视各地教育的结果,也是甘肃地方学校教育发展的真实反映。敦煌地方州县学校使用的教材是至今见到的最古的版本,也是保存至今最早的教科书。
2、医学教材
《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可见,本草和医方是学校的主要教材。从敦煌所出的唐代文献中,基本可看出当时医学校的教学内容有本草、医典、针灸和医方四类。
本草类有梁陶弘景《本草集注》,唐人李绩、苏敬《新修本草》和孟铣《食疗本草》三种。《本草集注》为南朝梁以前本草之总集,具有“本草正典”之称,医学界奉为圭臬。抄本序言讲到:“有毒无毒易知,惟冷热须明,今以朱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朱墨杂陈,标明其教学之用途。红黑对照,鲜明易辨,使学习者一目了然。《本草集注》所论述的一些药物的分类、采治方法,延至今日仍在教学和治疗过程中使用。《新修本草》计收药844种,是由唐朝国家组织编写的我国第一部医学教学参考书,也是世界上由国家颁布的第一部药典。《食疗本草》中之食疗,专讲动植物之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犹如今之食品疗法和营养疗法。为便于教学,敦煌本《食疗本草》以朱笔书写药名,药性冷热,用小字旁注。
敦煌文献中发现的针灸教材名为《灸经》,附图十多幅,直观性很强,图文并茂,图示详明,能使学生很快“明白经脉孔穴之道,辨识浮沉涩滑之候”。
医典类书籍包括以脏腑学说为中心的五脏类著作,或医经、诊法著作。敦煌医学校使用的有《五脏论》、《明堂五脏论》、《医书》和《玄感脉经》等。《医书》为《三部九候论》、《伤寒论》、《佚名代脉经》的抄录。医学关系到人的性命,所以唐代在医学专业教育中严格要求学生精通医学理论基础,重视理论与临床相结合。如学习《本草》须认识药形、深明药性;学习《明堂》须检图就能认识孔穴;学习《脉经》须能互相诊候,了解四时浮、沉、涩、滑的脉候;医典类则必须精读,做到融会贯通,得心应手。
医方也有相当数量的保留。医学类教材其实也是重要的科技文献。
3、道学教材
S.3768《文子》卷末题记表明,《文子》是敦煌道学中的教材。《通鉴》云:开元二十五年(737)“春,正月,初置玄学博士,每岁依明经举”。胡三省注云:“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亦曰道举”。规模为“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习老、庄、文、列,谓之四子。荫第与国子监同。”《老子》、《庄子》、《文子》、《列子》各书在敦煌文献中均有发现。其中现存《道经》总计约300余件,有相当一部分是道学师生的用书。这些教学用书与道教徒用书的区别在于,学校用书避唐讳,而教徒用书不存在避讳现象。这些课本用纸精良、墨色鲜亮,反映了道学在开元时的重要地位。敦煌道学的存在时间较为短暂,随着唐朝罢崇玄馆大学士而废,前后不过数十年而已。
4、童蒙教材
州县学以下的各类学校中,学童们所讽诵、书写的教材大都是识字、习书类,属于启蒙教材。目前能见到的敦煌出土的童蒙教育文献至少有上百个卷号。
《太公家教》。《太公家教》约成书于安史之乱后,是现存最早的格言谚语类蒙书,唐宋之际颇为流行。敦煌出土有九个卷号,最早者P.2825抄于唐大中四年(850),最晚者是P.3797抄于北宋开宝九年(976)。编纂目的是“辄以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幼童儿,用传于后,幸愿思之”。内容涉及有《孝经》、《礼记》、《论语》、《列女传》、《颜氏家训》、《千字文》及诸子学说。除少数外,均辑成四言韵语,便于记诵,且通俗易懂,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和认识需求。如“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知恩报恩,凡流儒雅。有恩不报,岂成人也。事君尽忠,事父尽孝”。
《开蒙要训》,马仁寿撰,此书性质接近《千字文》,属于小学字书之类。体裁为积字成篇,篇无重字,供初学者诵其文词,摹其点画,重在教学童识字。敦煌大约存有三十五个卷号。
《李氏蒙求》,唐李翰著,中唐至北宋颇为流行,内容为历史故事,形式为四言韵语,属童蒙知识类课本。此书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时期的《龙文鞭影》等书即导源于此。敦煌出土三件。
《新集文词九经钞》。此书抄缀经史,以类相从,既采择嘉言粹语,以供写作取资,又灌输伦理道德观念,以期陶冶品德,尤偏重进德修业,是一格言训诫类通俗读物。正如其卷首序文所言:“包括九经,罗含内外,通阐三史,是要无遗,今古参详,礼仪咸备。忠臣孝子,从此而生,节妇义夫,亦因此起,……恶词而众草不植而自生,善言而百谷非力无自媚。”史家评曰此书“杂辑九经诸子中佳言粹语,颇有助于修身,盖在《开蒙要训》之上,为入德之门也。……则并当时社会上通行之童蒙书也。敦煌至少有十五个卷号。
《字宝碎金》。此书不见隋唐、宋志著录,仅发现于甘肃。书中内容属杂字俗书类,全书不按内容分类,不连贯,不押韵,而以四声分类。俗书伪字和自创的新字特多。形、动、口语词多,名物词少,反映了通俗蒙求书的特点。其注文重在注音,其音往往与《切韵》不和,而与唐五代西北方音一致。有六个卷号。
此外,属于童蒙读物还有《兔园册府》、《俗务要名林》、《新集吉凶书仪》、《新集严父教》、《王梵志诗》和《杂抄》(一名《珠玉钞》,二名《益智文》,三名《随身宝》)等。童蒙读物注重识字与修身密切结合,且多为韵文,读来朗朗上口,容易记诵。
四、学生类文献
学生类文献有学生习作和学郎题记类,是各级学生留下的习字及杂写,内容颇为丰富。
1、学生习作
习字课本有《千字文》、《百家姓》等。这些书所收字体笔画少,简单易学。一些著名书法家所写的千字文书法作品,往往成为学生习字的范书。史书记载,智永禅师书写《真草千字文》八百本,每次写完,就被人争抢一空。敦煌出土文献证明,当地的学生也在使用这种范本。敦煌所出的完本、残卷及书写于卷背、卷末等处的杂写类千字文数量很大,类别很多。如:智永真草千字文(P.3561)、篆书千字文(P.3658、P.4702)等。甚至还有汉藏对音千字文(P.3419)。在一份旧的官府文书的背面,有学生习写的千字文真迹,有光、果、珍、奈、李、菜、重、芥、姜、海、碱、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出、丽、水、玉、出、昆、岗等字。最后是教师批语:“渐有少能,亦合甄赏”,意为“逐渐有了进步,应当给予奖励”。这件文书是我们了解古代童蒙教学活动非常难得的资料。
P.3145《敦煌百家姓》。《伯希和劫经录》认为是“习书杂字”。除写有“上大夫”外,另录写姓氏六行,二十五句,句四字。以“张王李赵”开头,下文与通行《百家姓》不同,可能是敦煌当地的百家姓。
《“上大夫”习字本》有六个卷号。是学童习字用的范本和照描本。以“上大夫孔乙己”开头。S.1313记:“且如世小儿上学,初学‘上大夫’等”。与近本“上大人孔乙己”略有不同。敦煌本是今天能见到的最古的实物。S.4870《小儿习字》有“水、本、子、乙”等。
2、学郎题记
学郎题记是学生在各种文书的卷背、末尾留下的片言只语。目前可以检索到的题记多达144条。按照纪年,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有朝代年号和确切题年者有72条。最早者是唐天宝元年(742年),最晚者是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前后245年。二是无年号而有干支纪年者47条。跨度大概从晚唐大中十四年(岁次庚辰,860年)到北宋雍熙四年(岁次丁亥,987年)。首尾128年。三是仅仅书有地支者6条。可以考订者仅仅有张议潮题记之“未年”为815年。其余大都难以定论,大致为吐蕃占领时期及晚唐时期之题记。四是全无纪年题记者,大致可以断定为晚唐、五代至宋初。
学郎题记的内容往往比较简单。一般内有时间、地点、身份等,再还有“写了”、“诵读、书记”等学习方式的记载。但这些时间、地点、身份及被抄写或者诵记的内容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对我们认识敦煌学校的性质及设置、教材的选用、著名人物的经历及其志向以及文书的性质、创作时代等问题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研究中国教育史的珍贵材料。
学郎诗。学郎诗是学童诗作,属于学郎题记的一部分,但体例略有不同。内容不多,大多以题记或者杂写形式出现,个性鲜明,语言质朴,真实反映了学童们的生活、学习、兴趣及爱好。天真自然,亲切感人。可见者如下:
S.3287:“今日书他智(字),他来定是嗔,我今归舍去,将作是何人。”
S.728:“学郎大哥张富千,一下趁到《孝经》边,《太公家教》多不残,喽猡□儿实相偏。”P.3486:“谁人读自书,奉上百匹罗。来人读不得,回头便唱歌。”
P.4787:“今朝好光景,骑马上夫堂。谁家好女子,嫁娶何□家。”
P.2746:《孝经》末题记:“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辞杖捶体,愿赐荣躯路。”
北图藏玉字91号(8317)背:“高门出贵子,好木出良才,丈夫不学闻,官从何处来。”
北图藏伍字68号(8442):“学使郎身性,长大要人求,唯亏急学得,成人作都头。”
也有比较规矩的诗作。P.2498《学士郎李幸思诗》为五代时七言诗,诗前有序:“天成三年(928)戊子岁正月七日学郎李幸思。”诗云:“幸思比是老生儿,投师习业弃无知。父母偏怜昔爱子,日讽万幸不滞迟。”相比之下,此诗当为学郎诗中的佳作。还有记实诗。如P.3386三界寺学士张富盈写《学士郎写文书诗》:“许写两卷文书,心里些些不疑。自要身心恳切,更要师父闍黎。”学郎诗是研究敦煌文书抄写情况的重要资料。
第二节
敦煌科举文献
科举制在隋唐以后的社会史中是一个影响到身份体制、文学生活、士子时尚、都市风俗的重要制度。陈寅恪先生把进士科举之注重看成“唐代统治阶级转移升降”的一大关键,从现已发现的敦煌史料来看,直接记载科举制的文书很少,其数目大大少于氏族志、姓氏录、家传等反映“氏族”体制的文书。因此,在既有的敦煌文献研究中,也就较少提及科举制问题。其实,经过详细的分类和仔细的挖掘,同样能发现一些相关文献。一些儒学经书实际上是科举教育用书,一些诗赋杂文是启发士子准备科举考试的进士文学,有的文书是举子“求知己”的书状。简单地说,敦煌文书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记载了科举制度及其风俗的史料,另一类是科举教育史料或进士文学史料。
一、科举制制度史料
1、贡举文献
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南壁题记:“翟通,乡贡明经授朝议郎行敦煌郡博士”。
莫高窟《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妹夫乡贡明经摄敦煌州学博士阴庭诫”。
P.4638《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阴庭诫“前沙州乡贡明经”。
P.2488a《贰师泉赋》:“乡贡进士”张侠。
S.0076vf:《乡贡进士刘书状》。
P.2718《茶酒论一卷并序》:“乡贡进士王溥撰”。
S.3723《记室备要一部并序》:“乡贡进士郁知言撰”。
S.4473vc《乡贡进士谭象启》。
所谓乡贡,《新唐书·选举志》云:每岁仲冬,“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即各地通过地方一级考试的州县学生员,他们“岁随方物入贡”进京师,参加国家组织的科举考试。
P.2488《渔父歌沧浪赋》:“前进士何蠲”。唐人习惯,举进士而未第者曰进士、曰举进士,得者曰进士第、曰前进士。
2、制举文献
莫高窟332窟所出《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大□□□□□□校尉上柱国李君修慈悲佛龛碑并序
首望宿卫上柱国敦煌张大忠书 弟应制举□□□□”。该碑造于圣历元年(698),是关于沙州“制举”的史料。《新唐书·选举志》记:“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制举即天子以制诏举士,有贤良方正科、博学宏词科等数十科。应试制举者不同于学馆之生徒和由州县之乡贡。题衔“应制举□”当为“应制举人”。
这些文献都是反映唐朝科举制的规定、运作及在敦煌等地实施和科举制社会影响的绝好资料。
二、科举制风俗文献
唐朝的科场考试中有很多成文或者不成文的习俗,其具体情况不见于正史,在唐人笔记小说中仅有个别反映。S.4473《乡贡进士谭象启》和P.2617《周易经典释文》末题记中则有很多具体和难得的资料。
科场中的称谓。《谭象启》中作者自称“从表侄孙”,是科场中门生对知己、座主、庇荫者的谦称。其时门生对座主常谦称“旧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孙”。《谭象启》为此种“叙中表从”的风俗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谭象自称是“久在科场,不遇梯媒,漫劳进取”的多次落弟者。“不遇梯媒”,即尚未找到“显人”作为“知己”。文中“秋赋”指乡试、州试。“春官”采听则指正月礼部试及二月放榜,即所谓“省试”。而“谏议老丈,中朝公辅”则是谭象对所求知己的赞词。《周易经典释文》末题记云:“开元廿六年(738)九月九日于蒲州赵全岳本写。此年八月七日□敕简过放冬集。敕头卢济、甲头张□(又奉十二月)敕放春选,差御史王佶就军试,敕头陈令祀,己卯开元廿七年正月十七日在新泉勘音并易一遍。五月廿五日于晋州卫杲本写指例略。”所谓“放”即敕准,所谓甲头是被批准人中在呈奏文时同甲呈奏的一甲之首名。其时进士、明经诸科应试者人数众多,根据敕令,有的考生是必须“冬集”的。所谓“冬集”亦即“孟冬之月,集于京师”。不须冬集的,称为“授散”。
“行卷”风习。行卷即应试举子将自己的诗文写成卷子,试前送呈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请求其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谭象启》中:“逐英翘而观上国,携文赋以谒雄藩”,即提出行卷的要求。而“果遇至公,获颁文解,巨人维挈,必赴搜扬,永承门馆之恩,长在荫庥之下。谨修启事,捧竭门馆”,即以启事请见于未来门主的风习。
《谭象启》是某乡贡进士往京师“求知己”的一件书启,《周易经典释文》抄写人显然是正在准备科举考试,故将该年有关贡举的敕令附录于后。
三、进士文学或科举文学史料
唐代举子以诗赋应试,旁及杂文、判等。考进士者又以古文行卷,旁及传奇小说。由此,我们看到,敦煌所出文学作品,尤其是赋、诗,旁及判、传奇等,其中不乏与科举文学有关者。如《贰师泉赋》题名“乡贡进士张侠撰”,此赋写敦煌古迹贰师泉及李广利西伐匈奴的故事。《渔父歌沧浪赋》题名“前进士何蠲撰”。以上两例说明,敦煌所出的这类“赋”当属于进士文学。敦煌写本中发现大量的赋作,独立成篇者有26篇,其中唐人赋22篇。同一件赋有多个写本,说明其在沙州广为流行。人们研习诗赋,与隋唐以诗赋取士分不开。敦煌还发现一些不同“乡贡进士”撰制的杂文。《茶酒论一卷》题名“乡贡进士王敷撰”,《记室备要一部》题名“乡贡进士郁督撰”等,都是珍贵的进士文学史料。
第三节
敦煌科技文献
一、敦煌文书中科技史料概述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中的科技文献资料相当丰富,总数大约在五百号上下。按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单纯性属于某种学科的资料。这类文献是观其名即知其性的专门科技文献。按照我国古代四部图书分类法,这类文献大多归于子部,数量也比较多,包括天文历法(具注历日等)、数学(算经等)、医药典籍(医方、本草等)、地理(地志、图经等)等。其中天文、历算、医药类文献最多。如果将与天文有关的星占类遗书不计,天文历法方面的卷子也达五十五种左右。主要在伦敦博物馆、巴黎图书馆的藏品中,有少部分散见于国内外公私藏品中。有关医学的专门卷子达六十多种,加上在其它内容中与医学有关的文献,总数几达八十种左右。这类卷子大部分也流散于巴黎、伦敦。有一部分散见于日本、俄罗斯及国内私人收中。地理方面的卷子将近二十种,主要部分是关于河西地方山川形势的文献,除二、三种散见于国内之外,其它卷子都藏于伦敦、巴黎等地。
第二类是被称作术数的中国传统方技类文献。作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类文献与当时人们生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是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其中某些材料对科学史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方技类在当时的流传很广,传播范围不比天文历法、医药典籍小。其实这类遗书中的个别材料本身就是天文历法、医药典籍的一部分。中古时代,科学与民间迷信在许多情况下纠缠在一起,甚至不分彼此,这些文献就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其中主要有天文、历法、医学、地理等方面的占星书、占病书、阴阳、堪舆、卜筮、释梦、相书等内容。其中与天文历法有关的星占、占时日气象风云等遗书大约有五、六十号。与医学有关的占病、推得病时日等方面的卷子约二十号,与地理有关的堪舆遗书十多号。其它试图解释生命现象的释梦、相书类卷子约三十号。还有涉及建筑的宅经等多种。
第三类是其他类文书中包含的科技类资料。由于文书的内容比较庞杂,科技内容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多见于类书和字书。类书和字书中往往有各类明确的科技资料。在问对吉凶的书信中,虽不集中,也零星涉及不少天文历法、节气时令等方面的内容。此外,地籍、户籍、什物帐文书之类,也不乏关于地理、人口、水道、物产、服饰等方面的科技资料。
就敦煌科技资料的创作性而言,原创的资料不多,抄录的文书占绝大多数。以医学文献为例。在敦煌科技文献中,医学卷子最多,但大多数是传统医学典籍的择抄。比如S.5614就择抄了《五脏论》、《平脉略例》、《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和《占五脏声色源候》四种已有医书。《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都是抄本,且有时代标志。星占、阴阳、相书之类也多为抄本。综合性卷子成卷途径也不尽相同,如书札、地籍、什物帐等就是当时的记录或抄本,而字书和类书几乎全部是传抄来的。
科技文献中,有些有明确纪年,而大多数只能根据部分题记、内容或其它旁证来确定。但大致属于南北朝至宋初,其中唐、五代时期为多。由于各类文献的性质与残存的内容不同,其确切时代,在使用时需要具体确定。历日残卷中不少有纪年或年号,如北魏写本历日有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和十二年(451年)的记载。已知日历年号最晚的一种是P.3507宋太宗淳化四年(993)癸巳年具注历日。后晋天福十年(945年)翟奉达所撰《寿昌县地境》也有明确的纪年。其余大多数没有纪年的卷子,经过研究,基本上也能断定其创作年代。如《兔园册府》,根据《困学纪闻》的记载,是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所撰,而《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记载蒋王恽于贞观七年至永徽初,在安州十多年,则此抄本必在其后。又如《俗务要名林》就是唐代的字书,而在敦煌地区被广为流传传抄的启蒙读物《开蒙要训》,是五代时的读物。其他医学文献据研究大多数也是六朝至唐末五代时期的读本,而大量药方(估计在一千多种以上)也未能超出六朝隋唐医家的医方范围。地学类遗书和综合性字书、类书、田籍、户籍文书以及星占方术类遗书的抄本也基本上不出唐五代范围。
敦煌遗书中科技类文献的卷子,以卷轴装为主。由于卷轴发现后大多已经残损,完整无缺的卷子比较少见,仅见《寿昌县地境》首尾完整。目前可知比较长的有日本龙谷大学藏《本草集注》,长约17米、高约28厘米,首佚数行,后均完好。《沙州都督府图经》首尾虽残,但还残存10米。S.5614《五脏论》、P.3596《医方》、敦煌县博物馆藏76号《地志》残卷,都残存长约3米左右。这类卷轴的高度,一般在20厘米左右,最高者达30厘米。除卷轴之外,敦煌遗书中的有关科技文献,也有少量为折装和蝴蝶装书册。
敦煌遗书使用的材质主要是蜀纸,质地比较粗糙。但佛经、道家经典则选用规格较高的洛阳纸。洛阳纸张比较讲究,有固定的行数和直行格子。由于敦煌科技文献大多抄写在经卷背后,所以质量要好一些。卷子的书写水平不高,只是比较工整,字体多为自由体行书,即所谓的经书体。也有少量刻印卷子,如伦敦藏木刻010《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
二、敦煌科技文献内容举要
敦煌遗书中散见于宗教典籍、语言文字、社会经济文书及民族文献中的科技资料很多,有待发掘,现将汉文卷子中与科技最有联系之方面加以归类并予以简单介绍。
1、天文历法类
现存40余件。主要为天文和历法两类。天文方面有两幅精美的古代星图:S.3326《全天星图》和敦煌县博物馆076《唐人写地志》背《紫微垣星图》。其中《全天星图》是现存记载星数最多(1359颗)、也是最古老的一幅星图。图为彩绘,囊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看见的大部分恒星。绘制时间当在公元705—710年间。《全天星图》的绘制办法:把北极附近的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附近的星画在横图上。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现代。李约瑟在比较该图与欧洲各国星图后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就没有”。《紫微垣星图》也是彩图。画有两个同心圆,外圆直径约26厘米。图中的星点用红、黑两种不同颜色表示。根据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在北纬35度左右,相当于长安和洛阳等地。
P.2512是一部重要的天文著作,残存内容有四部分:星占,《二十八宿次位图》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玄像诗》,日月旁气占等,内容丰富,是唐以前或者初唐的作品。其中《玄像诗》非常值得关注。全篇五言为句,263句,浅显易懂,是配合三家星经而作。特点是每次从角宿开始分别叙述三家星经,最后三家合在一起总叙紫微垣。这样,人们只要以诗为指南,便可迅速地将全天主要星官铭记在心。
历法分来自于中原类和本地编写类两种。其中来自于外地者仅仅有三件:《北魏历日》为敦煌所见历日最早者,也是现知唯一的北魏历书实物。“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为印本,仅存三行。《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印本历日》来自于唐王朝,是现存敦煌历书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件,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本历日。敦煌地方编写的历日有三十余种,形制有繁本和简本两种,书写格式有通栏和双栏之别。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808)戊子岁具注历日》。历日除记全年各月大小外,还有本年几十种年神方位、各种宜吉日的选择和凶日的避忌、昼夜时刻等,内容复杂,这恐怕也是“具注历”之名的来由。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星期制度在敦煌历日中也出现了。
2、数学文献
数学文献达十几部之多,有《算经》、《九九乘法歌》、《算表》等。有本《算经》的背面杂录有学童识字课本《千字文》的内容,另外一本的背页为学生所习的吾、及、在、也等常用杂字,《算经》与杂字共为一册,表明其为学校教学用书。
算经文献的内容主要有:数字认读、量度换算等。其中筹式记数法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应用算筹记数的记录。P.3349《算经一卷并序》记载的数字进位制有十进位制和万万进位制两种。量度换算方面对面积、容量、重量等单位的规定及进位都有详细明确的说明。如长度单位:“度之所起于忽,从蚕口中吐丝为忽,忽者如一蚕丝之广。”忽以上单位分别为丝、毫、厘、分、寸、尺、丈,皆10进位。至于对具体物品的一些习惯丈量方法,算经同样给出。如绢布类,“三丈为段,四丈为匹,五丈为常,十丈为引。”虽然段、匹、常、引等名称非为规范的进制换算单位,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使用率非常高,唐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统计中,庸调类的衡量单位就是匹、段等。另外,算经中对体积、面积的计算和换算还附有一定例题,其中有粮草食用和布防编制方面的计算实例。这类题型虽属于应用性计算题,但内容更具实际性,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现实在教材中的某种程度上的反映。
乘法口诀表的第一格是“九九八十一”,这是唐人习惯,到了宋代才倒过来,从一一得一开始,乘法表后还附有“自相乘”(平方)和“分之”(均分)等内容。
P.2490《算表》有15大格1250小格,该表是关于田土面积计算的。根据此表,可迅速查出边长10步到60步的任何矩形田地的面积。该表为历代算书之仅有。
3、医学文献
医学残卷大概有六十多个卷号,加上佛经等卷中散见的医学内容,总计近百个卷号。一般可以分为医经、针灸、本草和医方等。医经残卷有10余卷,主要包括以腑脏学说为中心的五脏论类著作、或医经、诊法著作。有《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段及《玄感脉经》、《明堂五脏论》、《五脏论》和《平脉略例》。经卷大都是初唐五代时期的写本。个别经卷中避“世”、“治”讳,是显示时代的重要标志。
针灸残卷有6卷。包括《新集备急灸经》和针灸图。P.2675卷首题名《新集备急灸经一卷》,书题下记“京中李家于东市印”。表明原来为刻本,初印于长安。此卷为写本,有小序说明编写目的:将流行于当时各家灸经汇集成卷,供原缺医少药的偏远州县救急治病所用。正文中画有正面人形穴位图的上半身,用引线标明穴名、部位、主治和灸法。共存17个穴位。S.6168和S.6262原为一书,是一部绘有人体穴位的灸疗图谱,能辨析者有18图,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实物记录。
本草残卷有7卷。包括《本草集经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等。
医方残卷有30余卷,共录有方近千首。其中有的题有书名,有的为唐人选录著名医家的医方,大多则不知书名撰者。这些医方有个别古医方,大多是六朝隋唐医学家经过验证的经效医方,另有不少单方。
4、农业水利类文献
P.2507残卷,成书于开元年间,首尾具残,无书题。据《白氏六帖》卷二十二引《水部式》文证明,知为《水部式》。该残卷为考察唐代农田水利状况的珍贵资料。P.3560《敦煌水渠》又名《唐代沙州敦煌地区灌溉用水章程》,首尾残缺。该章程制定于唐永徽六年(655年)至开元十六年(728)之间,是沙州地方官府文书原件的副本。《齐民要术》是北朝时期记载农事和手工业技术的重要著作,在敦煌文献中有该书残卷。
三、藏经洞出土科技文献的历史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历日,其中有国家颁布的,有地方制定的,这可以用来印证《魏书·律历志》关于地方制历法现象的记载是确切的。《魏书·律历志》记载:“世祖平凉土,得赵匪欠所修《玄始历》,后谓为密,以代景初。”惟此类地方修订的历法久已失传,无从参证。在敦煌所发现的五代宋初历书中,地方所制的就有多种,已知翟奉达撰订的就约有五种,如《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日》、《天成三年戊子岁具历》、《天福十年具注历》等。可见历法由国家统一颁定的制度,并不是无例外的,即在一定条件下(如这些远离中土,由于战乱等而不能及时使用国家颁布历法的地区),地方政府自己也会制定必需的历法。可见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有地方历与国家历两种历法系统。
敦煌出现的自制历日与国家颁布实行于内地的历法有一定的差异。如《北魏历日》与宋《元嘉历》相较,尽管在宋、齐、梁之世,《元嘉历》使用很普遍,但《北魏历日》与《元嘉历》还是有相异之处。如真君十一年八、九、十三个月之大小建,以及朔日干支,十一、十二两个月的朔日,太平真君十二年(六月已改元正平)十二月的朔日干支都互相有差异。再如敦煌本《同光四年具注历》、《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显德六年己未岁具注历》、《淳化四年癸巳岁具注历日简本》等,与当时相应的五代宋初历相校,在置闰、每月朔日甲子等方面差异很大。
中国古代类书、字词书的分类编写法,使用在动植物的分类上,就有动植物分类学的意义。中古时代的不少字书、类书已经散佚,但在敦煌有所保留。如P.2609号《俗务要名林》一卷是唐代的一种辞典,共有二种。该卷前面残缺,现存从量名“十摄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开始,有市部(?)、果部、菜疏部、酒部、肉食部、饮食部、□部(记载河流)、手部等,共二十一部。S.617《俗务要名林》比P.2609卷子多出□部(记载工具)、农部、养蚕及机杼部、女工部、丝帛绢布部、珍宝部、香部、彩色部、数部、度部、秤部、市部十二部。两者可以互相补正。“俗务”中使用的数及度量衡的完整形式,是珍贵的度量衡制度史料,在数学物理计量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S.1722《兔园册府》存卷第一“辨天地”,本书行于五代,宋时尚存。这卷“辨天地”系统地阐述了当时儒、释、道杂糅过程中传统宇宙观念的发展演变概貌,是研究天文学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S.3835《百鸟名》,记录了时人对鸟类的知识。P.3622、P.3776对天地、阴阳、年载、地理的记述,都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比较庞杂的备问吉凶、瑞应等文献于天象、历法、节气时令有不少记载。如P.2581《孔子备问书一卷》以设问做答的形式,解释“何谓天地”、“何谓日月五星”、“何谓四季”等类问题,颇似一种百科读物。
还有些敦煌科技文献是其他史籍中很难见到的。如:P.3379《显德五年阴保山等牒》是一份官方文书,其中记录着四十五人姓名,特别是画着每个人的或左或右一只手的中指节背部的大小形状和纹路,以供官方存验。这大概是当时法医学使用储存指纹特征断案侦破技术的最早实物记录。此外,还有许多涉及饮食、烹调、牛羊奶酪的制造以及关于性科学等方面的资料,亦很珍贵。
敦煌科技文献,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部分。还有许多零散的材料,需要进一步整理发掘。我们相信,通过对敦煌遗书的记载及敦煌文物、壁画等互相参证,将会为中国科技史研究中所遇到许多难题提供有益的线索。
四、敦煌科技史画
敦煌壁画艺术中包含有中国古代一些十分重要的科技成果,其中包括化学、建筑、服饰、玻璃制品、印刷技术、农业生产技术等领域。
敦煌壁画中约有80多幅农作图,涉及北朝至西夏近一千年间的各个时代。农业画面主要表现在如弥勒经变、法华经变、福田经变、佛传等图画当中。壁画中的农事活动很多:犁耕、牵牛、播种、扬粪土、锄草、收割、捆田、人工挑运、打场、扬场、掠场、粮食装袋、牛车拉运、归仓等第。伴随着这些场面出现了数十种生产工具如:耕犁(单辕直辕犁、双辕直辕犁、曲辕犁、三角耧犁)、铁铧、牛衡、籽种篮子、耱、耙、锄头、铁锹、镰刀、扁担、称、斛、木斗、升子、粮袋、牛车等等。壁画中还有畜牧养殖、花草树木的种植与栽培等场景。这些形象的实物资料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我国古代特别是北方地区农业生产活动的情况,是我们了解古代农业生产活动的客观而珍贵的资料,
敦煌壁画中交通科技形象资料有:道路、桥梁、牛车、马车、羊车、鹿车、骆驼车,还有各种船只。也有在丝绸之路上东来西去的行人商贩正赶着牲口艰辛奔波的图像。莫高窟第61窟西壁大型巨幅五台山图,是至今所见到的最完美、最早的交通图。十分全面而准确记录了五台山及其附近地理位置。
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包括帝王的宫殿、王侯将相的府第、官府衙门、民众的宅院、街头小店酒肆以及佛教寺院、山崖禅穴等。豪华者金碧辉煌、琼楼玉宇,简陋者诸如秋风所破之茅屋。而个别建筑结构和部件,是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资料。另外,许许多多的家具,诸如床、凳子、椅子、桌子等,不但有个人用品,也有婚宴用品、寺院及僧人的用具和供具等。壁画中各种人物服装和款式,则是服装设计和纺织科技资料的汇萃。
敦煌璧画中的医疗卫生资料也有不少。福田经变中布施医药情节、宝雨经变中病人得医服药场面、法华经变中“如病得医”等均为很宝贵的古代人行医用药生病治疗的形象记载。维摩诘经变中的刷牙图、法华经变中打扫马厩图、福田经变中的洗澡图和大便池、弥勒经变中扫城等情节,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的真实记载。
榆林窟第3窟西夏五十一面观音图中锻铁和烧酒蒸馏技术、大量的玻璃器皿、制陶术等均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史中的重要成果。莫高窟第61窟甬道的炽盛光佛图是一幅天文黄道十二宫图。
敦煌是一个文化宝藏,对了解中古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能提供很多有重要价值的资料。综合不同的实物、遗书和璧画,我们几乎可以找到与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相关的各方面参考资料。可以说,敦煌壁画艺术是一部中国古代的科技史画廊。
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