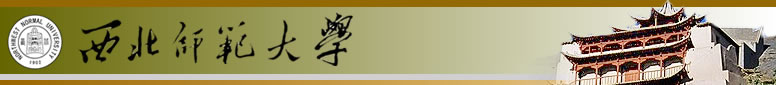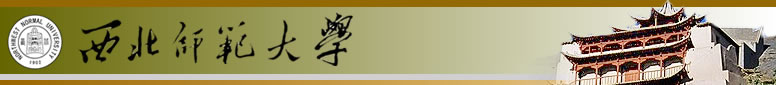第三章
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研究
第一节
敦煌遗书对于古文献校勘、训诂、辑逸方面的贡献
敦煌遗书规模之大,内容之宏,涉及面之广可谓是空前的。姜亮夫先生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说:“它在文化上的整个价值,虽此时尚不能作确切的估定,将来影响于学术文化,甚至于我们民族创进的资鉴,亦正待于国人的兴起研究。但我可以平平实实,不夸张、不收不揜地说,它的深邃之处,容或不如孔壁之于儒家经典,甲骨之于殷商史实,铜器之于两周史迹,而博大之处,关联之处,即综合的比价必不在前几次任何一次之下”。诚如斯言,敦煌遗书为浩博的中国古代文献增添了异样的光彩,弥补了许多以前意想不到的空白,在古文献校勘、训诂、辑逸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校勘
校勘,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基本任务,又叫做“校雠”,是广泛搜集各种相关的本子,取证各种相关资料,对同一古籍进行比较对照,校出篇章文字的异同,审定是非,力求准确地恢复古籍原貌的一项学术性工作。敦煌写本中,有些原本是四部典籍的写本,还有的不少是孤本,可以取作底本或参校本,也可用作参考材料,补充现存古籍校本的不足。
敦煌写本产生年代一般要早于刻本产生年代,往往更接近于原本真实面目,在校勘中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在校勘《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地志文献时,不仅要取两《唐书》、《唐会要》、《通典》、《太平寰宇记》等书相互参证,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采用敦煌文献,才能更好地还原本本来面目。敦煌写本中存3件唐代编纂的地理总志写本,即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十道录》,保存了5道138州府、614县的记录;P.2522《贞元十道录》,保存了剑南道12州残文;P.2511《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保存河东道州府情况。这3种文献都可作为整理《元和郡县图志》等的参考资料,可利用借鉴之处甚多。如《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卷40沙州敦煌县悬泉水条“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一句,校勘记云:“今按:各本作‘出悬泉山’,无‘腹’字”。而据敦煌写本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悬泉水”条载,“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西凉录·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据此,“腹”字不误。又据P.5034《沙州图经》卷五龙勒山条,“右在[寿昌]县南一百八十里”。可知《元和郡县图志》底本“龙勒山”应为“悬泉山”。
又如,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首尾完整的唐代慧能的《六祖坛经》抄本,这个抄本比现存的宋代刻本要少很多内容。根据这个抄本,人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坛经》的扩充经过,以及到宋代时又增加了哪些内容。此外,敦煌市博物馆藏完本、旅顺博物馆藏完本的首尾照片、北京图书馆藏冈48和有79号两件残本的相继问世,为校订新的《六祖坛经》提供了重要资料。周绍良先生《敦煌写本<坛经>原本》一书指出,这些敦煌本年代不一,但内容相同,应当就是慧能的原本,也就是惠昕所据以改动的古本。在此种见解的指导下,周先生对此书的整理方法是,先把各个敦煌写本影印出来,然后校录,以保存本子的真实性。周先生的看法是建立在利用现有所知全部敦煌写本来考订《坛经》写刻本基础上的,是利用敦煌文献来考订古籍的范例。
二、训诂
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古籍写本和一些与之相关的珍贵文书,在训释、考订古籍,或是在利用古籍编纂某一专题的工具书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如古代口头语言,在正统文献中涉及的很少,而利用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变文文书却可以对当时人们的口头语进行深入的探讨。变文是唐五代时期的民间文学,其中保存了不少民间口语,有些材料可以和敦煌的其他文献相印证。如《难陀出家缘起》中有文“道三两声家常”,此言较难理解,而通过敦煌王梵志的诗文,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它含有布施的意思。又如“庠序”,利用敦煌文献可以了解它除“学校”含义外的意思:在敦煌维摩诘讲经文
“威仪庠序,服锦新鲜”
中,可知它有“安详”的意思,同时根据敦煌《贤愚因缘经》可知“徐庠”“祥序”都可表示安详。
又如《资治通鉴》卷239中曾记“(李)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中的“奸人”是指何人?据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前缺)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僕射。”可知奸人应为密探、间谍之人。
可见敦煌文献在训诂字义、考订古籍方面具有其他正统史书所无的价值。
三、辑逸
辑逸是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手段,是对群书保存下来的已经亡佚文献的佚文进行搜集整理,编辑成册,以达到基本恢复原书面貌,或辑录出一个残本的目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都含有一些古佚书的残卷,如《论语郑氏注》、《春秋后语》、《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等,它们是古书的转抄本,和清代学者辑逸作品相比,大多保存字数较多,而且相对完整,价值大大超出一般从类书、地志、古注等书中所辑出的零散片断。因此,敦煌文献在古籍辑逸上具有极高价值。
如唐五代时颇为流行的晋孔衍的《春秋后语》,元以后亡佚,明清时期辑逸之风盛行,现在所能见到的该书辑本共有6家,其中以王谟《汉魏遗书钞》所辑最全,共辑75条,约七八千字。而敦煌所存《春秋后语》写本多达12件,即P.2569、P.2589、P.2702、P.2872、P.3616、P.5010、P.5034、P.5523、S.0713、S.1439、P.t.1291和罗振玉旧藏本等,保存下来的文字既多于前人辑本,而且更为真切,大多为孔书本文,弥足珍贵。
敦煌写本中还保存下来一些佚书片断,这些片断往往留存于类书、书仪、地志当中,它们对于辑逸工作同样是极其珍贵的。台湾成功大学王三庆教授所著《敦煌类书》(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中特别列出“提供遗佚书籍的残文”一项,将敦煌类书所含亡佚古籍的名录加以分类,为今后辑逸工作提供了指南。现转录于下:
经部及小学:《尚书中候》、《易飞候》、《易乾凿度》、《易通卦验》、《易是类谋》、《河图洛书》、《赤伏符》、《运斗枢》、《礼含文嘉》、《春秋说题辞》、《春秋考异邮》、《春秋元命苞》、《孝经援神契》、《韵集》,共14种。
史部:《春秋后语》、《三十国春秋》、《东观汉记》、《三国典略》、《晋中兴书》、《晋阳秋》、《汉官仪》、《良吏传》、《孝子传》、《三秦记》、《梁四公记》、《广州记》、《武昌记》、《英雄记》、《宜都山川记》、《嵩山记》、《蜀王记》、《南越志》、《风土记》、《拾遗》等,共50余种。
子部:《亡名子》、《玄游子》、《华子》、《抱朴子》、《符子》、《典论》、《世语》、《制法论》、《忠臣论》、《物理论》、《古今通论》、《氾胜之书》、《语林》、《女诫》、《博物志》、《太公家书》、《灵异记》、《五行记》、《梦书》、《符瑞图》等,共41种。
集部:诸家《诫子书》、《流别论》、《魏朗书》及各家诗、文、论、引、俗谚等,数十种。
此外敦煌其他文献写本也常常引用佚书。如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引有《西凉异物志》、《十六国春秋》之《西凉录》、《北凉录》、《后凉录》等多种。P.2511《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引用《赵录》、《图经》等。P.3900《书仪》残卷,引有毋至《风土记》、《续晋阳秋》、《晋咸康起居注》等。可见,敦煌文书对于中国古籍的校勘、训诂、辑逸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敦煌遗书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价值
敦煌遗书中历史学资料极为丰富,有些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些则可以纠正正史记载的讹误,有些则可改变某些传统的说法,特别是有关西北史研究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史学材料包括:法制文书、官府文书、田制文书、户籍、手实、差科簿、赋役文书、财政文书、寺院经济文书、仓廪文书、勾检文书、地理文书、军事文书、各种契约以及有关公廨钱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大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的第一手史料,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文献有助于了解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有关土地制度的文献,可以使我们得晓唐代均田制、吐蕃计口受田制、归义军请授田制度等实行的细节;户籍、差科簿、契约与社司转贴等文书,对敦煌古代徭役、兵役等制度的研究很有帮助;唐代法制文书,可与现存唐律相互印证;社会史的史料,有助于帮助了解唐代物价、劳动力价值、僧尼的生活、喜庆宴会及婚丧嫁娶等社会风俗。如敦煌唐代法制文书,保留了正史中大多已散失的唐令、格、式,以及部分唐代律、疏等,计有20件,另外吐鲁番出土法制文书8件,共计28件,计律10件、律疏6件、令2件、格5件、式4件、令式表1件。这些写本共计载律、疏、令、格、式约250余条,涉及名例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诈伪律、捕亡律八律,名例、职制、贼盗、杂律四疏,田、禄、祠、假宁、公式、职员、官品七令;刑部、户部、吏部、职方、兵部五格;吏部、度支、祠部、水部四式,保存了贞观、永徽、仪凤、垂拱、神龙、开元及天宝历朝的法律制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代律典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尤其是令、格、式等法典写本的保存,填补了正史典籍记载的空白。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4件为历代书目所未载,题名为《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的残卷,卷号分别为:S.5505、5785、P.2652、4016。记载了远古传说中的开天辟地、九氏三皇五帝的事迹,一直到晋朝。据考证此书作者是宗略、宗显二人,成书时代不早于西晋,不晚于隋,而作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可能性较大。据《隋书·经籍志》所载,这一类著作当时还有《帝王世纪》、《古史考》等,但大多数都已失传。而敦煌石室中保存的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却首尾完整,较好地保存了这一类书的面貌。
敦煌文献中的社会经济史料,开拓了对唐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的研究领域。如敦煌出土的有关均田制与户籍管理方面的文书,记载了均田制的实施情况及细则,十分珍贵。如有关北朝均田制的情况,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无法清晰地了解其实施的完整过程,而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残卷》,记载了西魏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情况。在田制上记载了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内容
;在丁户上记载了老、丁、女、贱、婢等内容。此外还保存了有关当时的纳税量词: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从而为研究北朝均田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再如敦煌文书中保存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资料,其中尤其以晚唐五代宋初的资料为最,这些资料为我们敞开了古代敦煌佛教社会的大门,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僧官体系、僧尼生活、寺院规模、依附人口、佛教节日等相关问题。其中僧官体系在吐蕃与归义军时期名称不尽相同。吐蕃时期敦煌的僧官体系为:都教授—副教授-都法律-法律-都判官-判官;归义军时期的僧官体系为:都僧统-副僧统-都僧政-僧政-法律-判官。总管各寺的教团机构是都司,设在敦煌城内的龙兴寺。敦煌的寺院规模,最盛时期有17座,寺院有大有小,有的在城内,有的在城外。各寺中一般都有经藏、佛像等供养具、家具、衣物等常住物。对于寺院财产的出入收支都有明晰的帐目,如P.2032背(3)《后晋时代沙州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详细记载了当年寺院各色开销与收入。他如S.4120《壬戌年至甲子年(962-964)沙州某寺布褐等破历》、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等,不一而足。
对于僧尼生活,敦煌文书更是提供了一般正史所不可能提供的绝佳材料。如敦煌文书中有关僧尼不住寺的记载、僧尼修行与参与宗教活动情况的记载、赋役负担与各种收入来源的记载、僧尼丧事的操办以及政府对寺院的控制等方面的记载,多为正史付之阙如。又如P.2642《诸色斛斗破用历》等文书记载敦煌僧人饮酒、P.3410《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疏》等文书记载敦煌僧人拥有私有财产、P.3249《大中、咸通间(848-874)归义军对兵名籍》等文书记载敦煌僧人参军之事等,为其他史料所鲜见。关于寺院的依附人口,敦煌文书中也有着大量记载。敦煌的依附人口主要包括寺户、常住百姓、硙户、梁户、酒户和牧羊人等。其中寺户的具体工作有佃种、刈稻、看园、园收、放驼、放羊、泥瓦、木匠、造纸、看硙、看梁、煮酒、修仓、守囚、车头等。对于佛教节日,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记载。如P.3103《浴佛节佛事斋文》、S.4191《腊八道场斋文》、S.2575《为筹办七月十五庄严道场启》等文书所记:正月十五要举行燃灯、赛天王的法事;二月八日佛诞日,要举行行像会;七月十五日要设盂兰盆会,设乐讲经;腊八要燃灯等。从敦煌文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敦煌寺院及僧人生活状况的真情实景。
敦煌文书尤其对于古代河西、敦煌的社会经济、生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弥补、纠正正史之不足,同时还可以通过它们对古代敦煌乃至古代河西的历史形成一个更为透彻、更为明晰的认识。
第三节
文书制度、职官制度研究
1、文书制度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留下来不少唐朝各级官府的文书原件,透过这些官府文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对唐代文书制度的了解,一方面可以对文书中涉及的其它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唐代对于官文书颇为重视,并且还有严格的专门规定。据《唐六典》和其它文献记载,唐朝政府对于官文书的纸张、字体、签署、用印、避讳、归档、录副、保存、修补、发送、传递、接受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如文书的传递过程为:起草、中书覆奏、进画、宜奉行、过门下、行下。以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为基础而编成的《唐六典》,对唐代最主要的几种上行和下行文书均有记载。下行文书包括:制、敕、册、令、教、符等6类,制、敕、册是天子所下文书,令为皇太子所下文书,教为亲王、公主所下文书,尚书省下达于州、州下达于县、县下达于乡的文书称为符。上行文书包括:表、状、笺、启、辞、牒等6类,表指上于天子之文书,状为上于近臣之文书,笺、启是指上于皇太子之文书,九品以上官员上行文书通称为牒,庶人上行文书曰辞。政府各部门互相间的往来文书依其类别不同可分别称为关、刺、移。
此外,《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条,记“凡王言之制有七”,分别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卷8门下省侍中条记载,“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分别为:奏抄、奏弹、露布、议、表、状。
以上所列这几种文书其内容、形式不尽相同,但在一般正史中大多只存留文书名称与相关规定,而不见原件。而在一些唐代文章总集和官人文集中,虽然保留了一些官文书的内容,但却往往删除了文书的格式或其年代,以致使唐代官文书的原貌很难得见。然而有幸的是,敦煌遗书中不仅保存了一批官文书的原件,而且还保存了一件唐《公式令》残卷(P.2819V),其中包括《移式》、《关式》、《牒式》、《符式》、《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6种官文书的书写格式,十分珍贵。
有关唐代文书制度,日本学者中村裕一曾做过大量研究。据中村裕一检索,敦煌出土下行官文书包括:制书(诏书)S.446《天宝七载(748)册尊号大敕文》、P.2696《中和五年(885)车驾还京师大敕文》;发日敕书有P.4632《金山国皇帝敕》(制授告身的敕词相当于发日敕);敕旨有S.5257《先天元年(712)敕旨》;论事敕书有S.11287A《景云二年(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敕牒有P.2054天宝元年(742)职官表保存的敕牒、P.4632《咸通十年(869)敕沙州刺史张淮深牒》;制授告身有P.3714V《乾封二年(667)氾文开诏授告身》、P.3749V《圣历二年(699)氾承俨制授告身》、S.3392《天宝十四载(755)秦元□制授告身》;奏授告身有敦煌研究院藏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告身;过所有敦煌研究院藏天宝七载(748)过所等。敦煌出土上行文书包括:表有P.3827《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上表》、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状有P.5566《书仪·上中书门下状》、S.4398《天福十四年(949)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进贡状》;牒有P.3952《乾元元年(759)罗法光祠部告牒》等。
这些文书的原本与抄件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唐代各级官府文书的起草、传达与格式有一清晰的了解,而且还可以从中窥见唐代中央、地方的行政运作效率。
2、职官制度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批唐代官府文书,对于研究唐代的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这些文书大多撰于唐代后期,而前期较少。并且大多为记载官府运作的原件,十可宝贵。相比之下,正史中所记唐代职官制度,如《唐六典》、《通典》、《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等的记载,则是详于唐天宝以前,而略于唐代后期。并且正史对于官制的记载往往多记职官的名称、品级、员额、职掌等,却略于官僚体制演变发展及其运作的状况。敦煌所存官府文书在时间上恰可与正史记载相衔接、相弥补,并可对唐代行政制度的运行进行研究。
此外,正史所记大多为中央官制,对地方官制记载较少,如《唐六典》30卷中对地方官制的记载只有一卷。相比之下敦煌官府文书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制的记载,主要包括州(郡)、县、乡、里各级官吏的材料,以及军事系统的折冲府、军、镇、戍、守捉等资料,对于研究唐代地方军政职官制度意义重大。
吐蕃占领敦煌后,有关吐蕃官制正史记载语焉不详,而敦煌文书中保存了有关吐蕃时期官制的大量珍贵史料。如据S.2146《行军转经文》、P.t.1079《比丘邦静根诉状》等文书记载,吐蕃占领敦煌后,设河州、瓜州两个节度使,分别治河州和瓜州。这与敦煌陷蕃前唐朝在凉州、鄯州设节度使有所不同;据P.3770《祈愿文》、S.6101《行城文》等文书可知,乞律本乃蕃占时期的临时性行政官职,又名乞利本,节儿、都督是其在敦煌的两位蕃、汉副贰;据S.2146《释门杂文》、P.2341《燃灯文》等文书记载,节儿一般由吐蕃人担任,上统于乞律本;据P.2631《释门文范》、P.2770《愿文》等文书记载,都督是由汉人担任的最高官职,辅助节儿治理敦煌,而负责乡一级政务的是部落使,其职责等同于乡官;据S.6172《布萨文》、P.3699《祈愿文》等文书,可知监军的地位低于节儿,高于都督,是由吐蕃人担任的行政官员。所以根据上述文书,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吐蕃时期敦煌的职官设置情况:节度使——乞律本(乞利本)——节儿、监军——都督——部落使——判官——乡部等。
第四节
军事制度、政治史研究
一、军事制度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为数较多的一批军事文书,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军事制度及相关问题甚有价值,特别是对唐代兵制的研究贡献更大。唐代兵制前期主要沿袭并发展了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度,后来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日趋解体。唐代后期兵制由府兵为主体的行军转变为以募兵为主体的镇军,而以军镇为据点的节度使体制也就相继建立。
据孙继民梳理研究,敦煌吐鲁番唐代军事制度的文书主要有:
(1)与府兵有关的文书:如吐鲁番阿斯塔那150号墓出土的《唐诸府卫士配官马、驮马残文书》、《武周长安四年(704)牒为请处分抽配十驮马事》、341号墓所出《唐开元五年(717)考课牒草》、108号墓所出《唐开元三年(715)西州营典李道上陇西县牒为通当营请马料姓名事》,
232号墓所出《唐某府卫士王怀智等军器簿》、507号墓所出《唐队正阴某等领甲仗器物抄》、214号墓所出《唐军府领物牒》等,这些文书记载了唐府兵的马匹、器仗、资装等装备情况。吐鲁番出土《唐永隆二年(681)卫士索天柱辞为兄被高昌县点充差行事》、阿斯塔那91号墓所出《唐贞观十九年(645)安西都护府下军府牒为速报应请赐物见行兵姓名事》等文书,记载了唐府兵的番上宿卫和征戍镇防,为研究唐代府兵的征行制度提供了绝佳史料。
(2)、与兵募、健儿有关的文书:如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武周智通拟判为康随风诈病避军役等事》、501号墓出土《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等,记载了唐代的兵募。兵募又称募人、征人、州兵,是唐前期除府兵之外最重要的兵员,这一地位直到唐玄宗后期才被健儿取代。上述文书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困惑。阿斯塔那188号墓《唐神龙二年(706)主帅浑小弟上西州都督府状为处分马料事》、《唐西州蒲昌县牒为申送健儿浑小弟马赴州事》、《唐被问领马牒》、S.964《唐天宝九载十载(750-751)兵士衣服支给簿》等文书保存了唐代健儿制度的珍贵史料。健儿是唐玄宗时期至唐后期的重要兵员,属于募兵制的范畴,是由国家供给衣粮的职业军人。上述出土文书解决了唐代健儿的来源、马匹配备、供料制度以及资装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3)、与行军有关的文书:如阿斯塔那4号墓《唐麟德二年(665)赵丑胡贷练契》、184号墓《唐开元二年(714)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等文书,记载了唐代在西域的几次行军情况。行军一词在北周、隋、唐时期是特指出征的军队。阿斯塔那222号墓《唐垂拱四年(688)队佐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唐中军左虞候贴为处分解射人事》等文书,记载了唐代行军的营制、兵种以及垂拱年间西域的军事形势等问题。
(4)、与军镇有关的文书:如P.3274背《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S.11287残卷、阿斯塔那83号墓《唐先天二年(713)队副王奉琼牒为当队兵见在及不到人事》等文书,记载了唐代军事管理制度、队官设置、军事形势以及兵员枯竭等状况。S.11453号H-L、S.11459号C—H《唐瀚海军典抄牒状文事目历》两组文书记载了唐瀚海军的行营、战斗序列、兵种以及后期设置等问题。P.3348《唐天宝六载(747)十二月河西豆卢军军仓收纳籴粟米麦牒》、阿斯塔那178号墓《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土右营下建忠赵伍那牒为访捉配交河兵张式玄事》等文书,记载了唐军镇判官、典等职官的设置等情况。
(5)其它军事文书:如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残卷、阿斯塔那191号墓《唐军府名籍》等文书,记载了唐代的武官、番兵、兵员等问题。阿斯塔那506号墓《唐天宝十载(715)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官告》、《唐大历四年(769)张无价买阴宅地契》、《唐西州道俗合作梯镫及钟记》等文书,记载了唐代折冲府官号与折冲府官职事的分离现象。唐前期军将的称谓有官号与职号之别,职号又有泛称与专称之分,泛称的职号有主帅、营主、押官等,专称的职号有总管、子总管、对头等。而大谷文书3786号背《开元五年(717)牒文》、阿斯塔那35号墓《唐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等文书就记载了这一史实。
二、政治史研究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西端,其保存的许多文书与当地或西北边疆史事有关,其中对河西特别是敦煌地方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本书第二章《丝绸路上的敦煌》中,分别从史前时期、汉代、魏晋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夏元明清时期对敦煌的政治状况作了论述。最为可贵的是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吐蕃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及西北周边的史料,而这些史料恰恰是正史记载所阙的,通过敦煌文书我们可以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河西的社会政治发展有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可掌握归义军时期敦煌的政治制度发展脉络。而且,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不仅有汉文文书,还有不少藏文文书,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吐蕃王朝大事记》等,既可以对敦煌政治史进行研究,又可探讨吐蕃王朝自身的发展。
由于敦煌文献对唐前期西北政局的记载相对较多,这有助于认识唐朝对西北的经营以及唐朝进入西域的历程等问题。如前述敦煌军事文书记载了唐朝在西域的行军或镇戍等情况,对研究唐代的西域史具有重大意义。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等论著,都是利用敦煌吐鲁番及相关原始文书对唐代西域史进行研究的成果。
此外,利用敦煌文书还可以对唐代中央政治史事进行研究。如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可对玄武门政变作出新的探讨,利用敦煌写本《大云经疏》及一些写经上的武周政治和尚的题名,有助于了解武周在政治运作方面的史实。敦煌诗歌作品《秦妇吟》,则生动地记录了黄巢起义进入长安后的情形,翔实可靠。
第五节
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研究
一、户籍制度研究
户籍是国家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受到历代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户籍制度中,籍帐则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敦煌所出籍帐文书有早至十六国西凉建初十二年(416)的户籍、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计帐文书,而更多的是唐代的籍帐。唐代籍帐大致分为手实、计帐、户籍三类。手实是在里正监督下,居民自报户内人口、田亩及赋役情况的登记表册,是制定计帐和户籍的主要依据。计帐是以乡为单位,根据各里所造手实,总汇各户人口、田亩、赋役等情况的“乡帐”,每年制定一次,作为制定户籍和县、州、尚书省户部制定各级计帐及国家“量入制出”的主要依据。户籍也是政府按行政区划登记居民户口、土地、赋役等情况的簿籍,一般三年制定一次,在逢丑、辰、未、戌之年,从正月上旬开始,到3月30日结束。其间,由各县主管户籍的户曹携本县前两年所定手实、计帐前往州府,共同制定一州之籍。籍依乡、里次序逐户登记,最后一式抄写3份,以乡为单位粘接成卷,骑缝处注明某州某县某乡(有的还注有某里)籍,并加盖州、县官印,分存尚书省户部及州、县籍库。此外,为了确保户籍的真实,各地乡里政府还需对各户进行“貌阅”,即勘验各户人口的相貌、年龄、废疾等情况,作为制定手实的依据,从而以之保证赋税徭役的征收与征发。
利用敦煌户籍不仅可对当时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对于当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也极有意义。如S.3287《吐蕃子年(808)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记载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于百姓的户籍控制与管理状况。再如S.323《唐大顺二(891)年团头名籍残卷》列举了第一至第九团的番号和各团团头姓名,对研究唐代军制亦有帮助。吐鲁番出土《武周载初元年(690)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记载了政府对宁和才等人实施
“貌阅”的状况。吐鲁番阿斯塔那所出《唐西州高昌县顺义乡诸里帐(草)》,记载了各里民户的姓名、老弱状况、丁男数目等情况。阿斯塔那35号墓《唐永淳元年(682)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记载了乡里官吏在造手实时,不仅仅是被动地根据当地土著居民的申报来填造手实,同时还要搜检当地当时所有的客寓之人。而这些记载多是正史所缺的。
S.0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是目前所知留存下来的十六国时代唯一的一件户籍文书,该写本前后残缺,只保留有兵裴晟、散阴怀、兵裴保、散吕沾、兵吕德、大府吏隋嵩、散隋杨、散唐黄等8户的户籍。从文书中这八户户主的称谓看,当时将户分为兵、散、大府吏等类,每户的人口又根据年龄、性别区分为丁男、次男、小男、女几种。此文书对了解西晋十六国时期户籍制的演变极为重要。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547)计帐残卷》,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户籍及均田赋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书。
二、土地制度研究
敦煌、吐鲁番遗书中存留了大批有关土地制度的文书,尤其是有关均田制的文书更多。传世文献中对于北朝均田制的记载十分简略,致使许多问题无法完满解决,但敦煌遗书中恰恰出土了有关此时期的均田制文书。如前所述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547)计帐残卷》,记载了北朝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田制、赋税数额等情况。其中田制记载了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正等内容。这些记载为解决北朝均田制实施中的种种细节提供了珍贵史料,弥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
敦煌文书P.2822《唐先天二年(713)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P.3877《开元四年(716)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P.
3897、3877
《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莫高乡籍》、P.
2719《天宝三载(744)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S.4583《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P.2596、3354《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S.0514《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等等,具体记载了唐代均田制下政府的授田、收田与百姓的受田、退田等实施过程中的详细情况。据之有学者认为,唐朝政府规定丁男应授土地百亩,实际上是国家允许授田的最高限额,并不是实际受田数。如果丁男占田超过百亩,那么国家就会干预没收。如果达不到应授田额者,可以请授。事实上,每户名义上所授给的田地,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家原有土地,只是政府通过手实与户籍将其登记在册,这些土地就变成了官府的授田。
除敦煌文书外,吐鲁番文书中也有较多反映均田制的写本。如吐鲁番《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前后西州高昌县退田簿》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西州高昌县给田簿》两件文书,记载了赵善忠在生前与死后田地的变化。文书记载,赵善忠生前自己买得的土地,不再退还,而是由其后人继承。这说明在均田制下并未触动私有土地制度,甚至连均田民中的一般下层人户的私有小块土地,也没有触动。朱雷先生在《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一文中谈到:这说明在均田制下,手实、户籍中有关已受土地的登录,是包括了通过均田令授予的土地,同时也登录了个人私有土地。从而表明在形式上,把私有的小块土地亦纳入均田轨道之中,但又并不侵犯这种私有土地主人的利益。通过此件文书我们了解到,在唐代户籍中所记载的已受土地数字,应是该户所有土地数字,并不存在户籍中的已受土地数字是通过均田令所“授予”,而个人私有土地另行登录的现象。
第六节
赋役制度、财政制度研究
根据《唐六典》记载,唐代人民承担的赋役主要包括租、调和各色徭役等。在均田制之下建立起了租庸调制,租是向国家纳粮,调是向国家纳布或麻,每丁每年服徭役20天,而庸则是指如不服役,可向官府交纳一定量的布或绢来抵,叫做“输庸代役”。唐代前期人民对国家担负的徭役有:正役(即每年服役20日)、杂徭、色役、工匠在官府作坊中及特定地区的服役、特种徭役。唐天宝以后,正役已完全被庸绢所代替。
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中含有不少反映唐五代赋役制度的文书,
P.2657、P.2803、P.3018、P.3559等《差科簿》文书就是其中的一种。唐代的“差科”具有征发徭役,特别是征发杂徭的含义。征发徭役的文簿就称为“差科簿”。从这些文书中反映出唐代在征发徭役时,将民户分成不同的户等,按户等的不同征发,在县和州均设置差科簿,县差科簿由县令亲自掌握。这些信息对于了解唐代赋役制度颇有助益。
再如2597号文书,记载了唐代高昌庸的执行情况,大谷文书1267号记载了徭役时间不应过长,大谷3025、2372、3364等文书中记载了唐代的兵役,5177、1308号文书则记载了唐敦煌差科的征发等,均很珍贵。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一批反映唐五代财政制度的写本,价值很高。上述文书中所反映出唐代赋役制度中的租、调等内容,同时也是唐代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又如勾检制度是唐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尚书都省领导中央各寺监及地方州县勾官对当司文案辑失勾检,以保证国家的行政效率,以及财务行政效率。勾官掌管中央的一切出纳,国家的收支都要先经过勾官,勾官检勘相符,才可进行。敦煌文书P.3559、3664、《天宝十二载(753)申比部勾征帐》保存了唐前期的勾征情况。
P.2763背(一)《吐蕃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P.2763背(二)《吐蕃巳年(789)七月沙州仓曹杨恒谦等牒》、P.2763背(三)《吐蕃午年(790)三月沙州仓曹杨恒谦牒》、P.2763背(四)《吐蕃午年?(790?)沙州仓曹状上勾覆所牒》、P.2654背《吐蕃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P.3346背《吐蕃巳年?(789?)沙州仓曹会计牒》等文书,均记载了吐蕃占领时期的勾检制度等。
仓廪制度是唐王朝财政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仓廪系统主要包括太仓、正仓、转运仓、军仓、常平仓、义仓等。敦煌、吐鲁番仓廪文书记载了唐代仓廪制的具体运行与细节,可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如吐鲁番出土文书《麟德元年(664)史玄政纳粮据》(64
TAM35:33号),记载了高宗时期借贷人向西州官仓纳利息一事。敦煌文书P.2803《唐天宝九载(750)八月至九月敦煌郡仓纳谷牒》,记载了敦煌郡仓有时也受纳地税。吐鲁番文书《唐开元八年(720)借贷仓粮纳本利帐》(72
TAM230:50<b>),反映了官仓借贷到期后还纳本利的情况。史籍对唐代军仓记载较少,敦煌吐鲁番文书则提供了此方面的可靠资料。如阿斯塔那出土的《伊吾军纳粮牒》(72
TAM226:5),记载了唐代军仓管理的相关问题。敦煌文书P.3348《天宝四载(745)河西豆卢军军仓牒》、《天宝六载(747)十月至十二月河西豆卢军军仓牒》,保存了唐玄宗时期军仓和籴的重要史料等。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保留了一些有关物价方面的写本。如大谷文书4894、1012、1011《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时估案》、大谷文书4893《唐天宝二年(743)八月某县上交河郡时估事牒》等,记载了市行会根据每旬市场实际交易情况进行的估价。敦煌文书P.2863背《唐天宝年间敦煌郡应现在帐》,记载了敦煌天宝年间一些物品的价格,如“五谷时价,小麦壹斗直钱肆拾九文,粟壹斗直钱叁拾肆文”等。吐鲁番文书《唐开元十九年(731)唐荣买婢市券》(73TAM509:8/12-1(a),2(a))、《唐开元二十年(732)薛十五娘买婢市券》(73TAM509:8/4-3(a)),记载了开元时期的奴婢、牛马贸易。以上这些文书对了解唐代敦煌及全国的经济状况、人民生活水平、物价、粮食产量的高低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第七节
敦煌法制文书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批为数不少的法制文书,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抄写的唐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典及律疏、令、格、式等的写卷、制敕文书、法律档案资料、地方官府的判案文书,而且还有大量的民间契约文书资料及唐中央政府及地方政权实施的经济法律制度。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律令格式及律疏写卷
据陈永胜等学者整理研究,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各类法典28件,其中律主要包括:《永徽名例律》,它由Дx.1916、3116、3155,S.9460A,Дx.1391三个残卷组成,主要记载了有关十恶、八议、关于官户、部曲、官私奴婢犯罪处理的规定、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等内容。《擅兴律》残卷,现分藏于日本、德国,记载了关于士兵征集、军队调动及营造方面的法律规定。《诈伪律》残卷,现藏于日本,编号为大谷4491、4452,是有关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规定。《贼盗律》残卷,现藏于日本,编号为大谷5098、8099,收录了有关盗贼、拐卖人口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职制律》残卷(包括《永徽职制律》和《垂拱职制律》),编号为北图丽字85号、P.3608,3252,记载了唐政府有关官吏的行为规范及驿传方面的法律规定。《户婚律》,卷号为P.3608、3252,记载了有关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内容。《厩库律》残卷,卷号为P.
3608、3252记载了有关唐政府管理国有与私有牲畜、仓库方面的法律内容。《捕亡律》残卷,现藏于英国伦敦,编号为ch0045,记载了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内容。
令主要包括:《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现藏于英国和法国,存215行,记载了有关东宫、王府职员设置标准等内容。《开元公式令》残卷,现藏于法国,全卷104行,记载了唐代的官文书情况。
格主要包括:《散颁刑部格》残卷,断为两片,分别藏于法国与英国,共存120行,记载了伪造官文书印、官吏贪污犯罪等的法律规定。《垂拱后常行格》残卷,仅存16行,记载百官奏事、出入门等的法律规定。《开元户部格》残卷,共存69行,现藏于英国。《职方格》残卷,仅存7行,记载兵部职方郎中的职掌等。《兵部选格》残卷,存18行,记载武将的选任等。
式主要包括:《吏部式》残卷,现藏于法国,卷号为P.4745,共存9行,记载了有关唐代官员叙阶及子孙用荫方面的规定。《度支式》残卷,共2卷,存30行,卷号为72TAM230:46(1)、(2),记载有关庸调之征输、折纳、分配的法律规定。《开元水部式》残卷,现藏于法国,卷号为P.2507,共存144行,记载了唐中央有关水利管理的法律规定。
律疏主要包括:《名例律疏》残卷,包含P.3593《开元名例律疏》残卷、河字17号《开元律疏卷第二名例》残卷,记载了十恶及官员任免的法律规定。《职制律疏》残卷,共1卷,现藏于法国,编号为P.3690,记载了御膳的制造、舆服御物的修整等法律规定。《贼盗律疏》残卷,共1卷,现藏于英国,编号为S.6138,对造谣惑众谋反罪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记载。《杂律疏》残卷,今下落不明,录文存80行。
唐代法律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律和疏两类,正史中有关令、格、式则几乎没有保存下来。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律、令、格、式残卷,几乎囊括了唐代法律的各个形式,填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同时,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法律文书,时间跨度大,涉及年代多,从中可探寻唐律的发展轨迹,具有极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
二、民间争讼文牒
敦煌遗书中保留了一批民间的争讼文书,是当时民众调节、处理家庭婚姻、土地田宅、财产继承、奴婢买卖、债务税收、户口徭役等民事纠纷的重要法律手段,为我们研究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和人身依附关系的提供了珍贵资料。
敦煌争讼文书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拟判文献。敦煌吐鲁番争讼文书中的拟判文献主要是指P.3813《文明判集》残卷和P.2593《开元判集》残卷。《文明判集》残卷现藏于法国巴黎,共存判文19道。《开元判集》残卷亦藏于法国,共存判文3道。两判集应是当时政府为规范各级官吏司法办案的判词范文,内容几乎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并在全国推广,影响较大。(二)关于土地、户口、徭役、税收等牒状及籍历。如P.2222B《唐咸通六年(865)僧张智灯状》记载了有关土地的纠纷。大谷2836背《圣历二年(699)三月二十日敦煌县检校营田人等牒》是有关营田的文书。P.3451《甲午年(994)洪润乡百姓氾庆子请理枉屈状》记载了土地税收的纠纷。S.3287背《子年五月左二将百姓氾履倩等户口状》是有关户口的文书。大谷2834《圣历二年(699)前后敦煌县受田簿》是有关受田的文书。S.2103《酉年(805?)十二月沙州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请地牒并判》是有关百姓请地的文书。P.3193背《年代未详有关土地税收纠纷牒及判》是有关土地税收纠纷的文书。P.3257《后晋开运二年(945)十二月河西归义军左马步押衙王文通牒及有关文书》是有关土地所有权纠纷的案件。S.6235背《唐大中六年(852)十一月唐君盈申报户口田地状》记载唐君盈申报自家田地户口。(三)关于奴婢、房宅、债务等状牒。如S.3876《宋乾德六年(968)九月释门法律庆深牒》是有关房宅纠纷的文书。P.3186《宋雍熙二年(985)牒》是有关债务纠纷的文书。P.3854背《唐大历七年(772)客尼三空请追征负麦牒》记载了债务追征。敦0298《唐天宝年代敦煌郡行客王修智卖胡奴市券公验》记载了有关奴婢买卖的纠纷。(四)关于婚姻家庭等的文书。如72TAM209:88.89.90《贞观中高昌县勘问梁延台雷陇贵婚娶纠纷事案卷》残卷是有关妻妾纠纷的案卷。P.3774《丑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涉及遗产分割。P.3744《僧张月光分家书》记载兄弟分家产。P.4525《放妻书一道》是有关夫妻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的文书。S.6417背《年代不详孔员信三子为遗产纠纷上司徒状》记载了一遗产纠纷案。(五)关于盗窃、违契、伤人等的文书。如TAM61:24、23、27《麟德二年五月高昌县勘问张玄逸失盗事案卷》记载张玄逸家中失窃之事。73TAM509:8(1)、(2)《宝应元年六月高昌县勘问康失芬行车伤人事案卷》记载张失芬驾车辗伤他人之事。中科图藏《开元中西州都督府处分阿梁诉卜安宝违契案》记载阿梁起诉卜安宝违反契约事。
三、契约文书
除了存有唐代国家的法律规定、民间争讼文书外,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还保留下来了有关民间普通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契约文书。据陈永胜等有关学者整理,敦煌吐鲁番出土契约文书资料约有600余件。契约时间上起西凉下至宋初,时间跨度较大,真实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契约的发展历程。
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买卖契约。这是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的最主要类型。如S.5820、5826《未年(803)尼明相买牛契》记载尼明相将牛卖于张抱玉,两人立契为凭。S.1946《宋淳化二年(991)押衙韩愿定卖妮子契》记载押衙韩愿定将家中女婢出卖于朱愿松,两人立契为凭。P.3649《后周显德四年(957)敦煌乡百姓吴盈顺卖地契》记载敦煌百姓吴盈顺卖地于琛义深。S.1285《后唐清泰三年(936)百姓杨忽律哺卖舍契》记载杨忽律卖房舍于他人,两人立契为凭。(二)互易契约。互易契约是反映物物交换的一种契约形式。如P.3394《唐大中六年(852)僧张月光博地契》记载僧张月光与他人博换土地,立契为凭。S.6233背《寅年(822)报恩寺寺主博换驴牛契》记载报恩寺寺主用驴一头外加细布若干博换成允恭牛一头。(三)借贷契约。如《唐麟德二年(665)张海欢白怀洛贷银钱契》是有关张海欢、白怀洛等人借贷银钱的契约。《唐乾封三年(668)张善熹举钱契》记载张善熹借贷左憧熹银钱,两人立契为凭。(四)租佃、租赁契约。如P.2858背《酉年(829)索海朝租地贴》记载僧善惠租佃索海朝的土地。吐鲁番文书《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索善奴夏田契》记载夏孔进租佃索善奴的土地。S.5927《唐天复二年(902)樊曹子租地契》记载刘加兴租赁土地十亩给樊曹子。吐鲁番文书《尼高参赁舍券》记载尼高参租赁房屋事宜。S.3391《丁酉年(937?)租用油樑水磑契》涉及油樑水磑的租用。(五)雇佣契约。如S.6341《壬辰年雇牛契》记载雷粉将黄牛雇于百某某。P.2652《丙午年宋虫雇驼契》记载宋虫雇同乡百姓八岁驼一头。S.3877《戊戌年令狐安定雇工契》记载令狐安定雇龙聪儿为工一年。(六)遗赠扶养契约。如P.5443《壬戌年(962)龙勒乡百姓胡再成养男契》记载胡再成收养清尕为养子,两人立契为凭。《宋乾德二年(964)史氾三养男契》记载史氾三收养原寿为子。P.4525背《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僧正崇会养女契》记载僧正崇收养女子的继承情况。
从敦煌吐鲁番契约文书中可见,契约条款一般包括时间、地点、双方的义务、责任等内容,立契人必须双方合意,而且必须要有保证人,可见契约水平达到了较高程度,并且契约涉及方面很广,可见当时民间已经广泛地使用这种自治调整的方式来规范普通民众的经济关系。
第八节
敦煌地理文书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大量地理方面的文献,对于历史地理和我国古代方志学的研究意义重大。这批地理文书除《大唐西域记》等少数几种外,绝大多数是我们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它们既不为历代官私目录所载,也不为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它们的面世大大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为地理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领域。这些文书可以粗略地分为5个部分,即敦煌地方志;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行记类写本;姓氏地理遗书等。
一、唐五代敦煌地方志
这一类文书包括:唐前期的《沙州图经》卷一(S.2593)、《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P.2005、P.2695)、卷五(P.5034)、《西州图经》(P.2009);《沙州伊州地志》(S.367)、《沙州图经》(S.788)、《寿昌县地境》、《沙州城土镜》(P.2691)、《敦煌录》(S.5448)、S.6014《始平县图经》等。其中《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盛唐时期沙州的河流、渠道、堤堰、湖泊、寺庙、驿站、故迹、祥瑞等50余项内容。《西州图经》记载了西州十一条道路与两所石窟和一区古塔。《沙州城土镜》、《沙州图经》及《寿昌县地境》,记载沙州及其所属寿昌县的山脉、湖泊、古迹以及唐鄯善镇附近城池沿革等。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载沙州寿昌县及伊州河流、湖泊、城镇、烽戍、寺院、物产、山川、部落等。《沙州地志》记载沙州寿昌县到鄯善一带山脉方位、城镇沿革、设置规模、土产和鄯善镇对外的六条道路的险易状况等。S.5448《敦煌录》,记敦煌境内效谷城、贰师泉、莫高窟、鸣沙山、甘泉水、金鞍山、阳关、玉女泉、石膏山、河仓城、长城等地理状况。S.6014《始平县图经》,记载武功县驿、槐里乡、汤台乡、龙泉乡等地。上述这些内容,较之《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地理志》等所记,要丰富得多、翔实得多。
二、敦煌地理杂文书。包括:S.5693、P.3721《瓜沙两郡史事编年》,P.3560《唐代敦煌县地方行用水细则》,P.2507《水部式》,P.3720背《莫高窟记》,S.6167、P.2690、P.2748、P.2983、P.3870、P.3929《敦煌古迹二十咏》,P.2625、P.4010《敦煌名族志》,S.6161、S.3329、S.6973、P.2762《张氏修功德记》,S.1889《敦煌氾氏人物传》等。其中《瓜沙两郡史事编年》记载了沙州设置至开元年间张孝嵩任刺史的史事。P.3560《唐代敦煌县地方行用水细则》记载了敦煌53条水渠及其行水灌田次第。P.2507《水部式》,记载了农田水利管理、碾硙设置及用水量的规定、内河航运船只及水手管理、海运管理、渔业管理等内容,是见于文献记载的由中央政府作为法律正式颁布的我国第一部水利法典,是唐代水利管理的一项重要创造。《莫高窟记》,记载了前秦建元二年(366)沙门乐僔首开莫高窟之举及其后世的建造情况。《敦煌古迹二十咏》为五言古诗20首,分别咏颂敦煌的三危山、白龙堆、莫高窟、渥洼池、阳关、玉女泉、墨池等20处名胜古迹。《敦煌名族志》主要记载敦煌张、阴、索氏家族渊源及名人。《张氏修功德记》,记载了张议潮父辈、张议潮、张议谭、张淮深的生平事迹。《敦煌氾氏人物传》记载敦煌氾氏家族的起源及名人。此文书与《敦煌名族志》及敦煌所出各种碑传、铭刻、赞、墓志共同反映出了各姓族起源、迁徙和形成的史实,是研究古代敦煌遗民史、民族融合史的珍贵资料。
三、全国性地志
共有三部。P.2522《贞元十道录》,为唐代中期著名舆地学家贾耽所撰,惜宋代以后亡佚。本卷存16行,记剑南道12州的州郡等级、名称、距两京里程、所管县名、古迹及土贡等。敦煌市博物馆藏58号《敦煌博物所藏地志残卷》,记有陇右、关内、河东、淮南、岭南五道138州府的情况,包括州府等第、名称、土贡、所属县名等第、县管乡数等,并保存了唐玄宗开元廿五年的行政区划、天宝年间州县名称的变更,以及陇右、关内、岭南诸道许多珍贵史料。P.2511《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卷第二》,为唐宣宗时著名学士韦澳所撰,亦在宋代佚失。本卷存206行,记载了河东道晋、太原、代、云、朔、岚、蔚、潞等八州府,每州府下详记府州名称、等第、建置沿革、郡望、地名。山川、民俗、物产等情况。如记民俗方面:蔚、云、朔、岚等州风俗与代州雷同,汉戎杂居,虽然都是编户齐民,但民风便更接近于戎胡,所以比其它地区更难以治理。
四、行记类写本
此类文书又可分为往西域行记、往五台山行记和全国性游记三类。
1、往西域行记。有P.3532《慧超往五天竺国传》,S.383《西天路竟》,P.2700、S.2695、P.3814、S.958《大唐西域记》、于阗文《使河西记》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慧超由海路入天竺的路线、历经各国之宗教、疆域、兵力、民俗、物产、服饰、语言等情况,可填补《大唐西域记》和《悟空行记》间的空白,反映了开元盛世时西域的政治与宗教状况。《西天路竟》首尾完整,共21行,记从东京开封到南天竺宝陀罗山的行程,其路线与北宋初年西行求法僧路线相同,可与《继业行记》等书相印证。《大唐西域记》四件残卷长短不一,分别为序、卷一、二、三的抄本,为目前所见该书最古的本子,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于阗文《使河西记》,记载了自于阗到沙州、瓜州、肃州、甘州、凉州、朔方等的行程。
2、往五台山行记。存P.2977《五台山志残卷》,P.3973、P.4648、S.397《往五台山行记》,P.3931《普化大师游五台山日记》。《五台山志残卷》存五台山得名,以及中台、东台等情况。《往五台山行记》,共有三卷,分别记载了某僧人从沙州出发,由朔州经雁门关入代州到五台山,即经晋北到达五台山的道路和自怀州经太原到五台山的道路,以及沿途所经州郡、驿站、关隘、村落、寺院等情况,保存了山西古代交通地理及佛教传播的珍贵史料。《普化大师游五台山日记》,记载印度普化大师自中印度至五台山游历各寺的情况。
3、全国性游记。仅存1卷,即S.529《诸山圣迹游记》,为五代后唐时某僧人游历各地州郡名山的旅行记。该僧人始足于五台山,历经太原、幽州、定州、沧州、汴州、扬州、洪州、杭州、抚州、福州、泉州、广州、韶州、洛京、关中等地,以及庐山、峨嵋山、罗浮山、终南山、嵩山、华山等名山寺院,其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史料价值很高。
五、姓氏地理遗书。
主要包括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B.8418《姓氏录》,P.3191《郡望姓源》,P.3421《氏族志》,S.5861《姓氏书》等。《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共存10道90郡,106行,记载了唐后期姓望的地理分布,反映出唐末魏晋以来门阀氏族势力的衰落及新门阀的兴起。据本卷所记,姓望的地理分布并不平衡,岭南道无姓望,陇右、山南、剑南、淮南道姓望亦较少,姓望主要分布在关内、河东、河北、河南、江南五道。姓望的分布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分布相一致,长安、洛阳、会稽、扬州等地,相应也是姓望集中的地区。《姓氏录》和《郡望姓源》,记载了初唐时期各州的姓望分布。《氏族志》记载了始平、扶风二郡姓望姓源。《姓氏书》由四片组成,第一、三、四片与B.8418相近,第二片记宋、阳、车、贾等姓望所出郡。唐代姓氏书保存至今者很少,而敦煌姓氏地理书却保存了唐代至五代时期的姓氏源流及分布,显得十分珍贵。
对于敦煌地理文书的价值,李并成曾总结为:
(一)敦煌地理文书关于各道统州县数、州县等级、处分语等方面的记载对于历史政治、军事地理的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如P.2522存剑南道12州,而《通典》遗曲真霸协四州,《元和郡县图志》遗保霸二州,《新唐书·地理志》遗协翼二州,均不及P.2522齐备。S.0529亦保存了全国许多节镇统州县数,可用以证史、补史及纠史之误。(二)关于各地经济物产的记载对于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P.2522、敦博58号列各州郡土贡,P.2511载物产,S.0529更是详记各州物产与特产。相比之下,《唐六典》卷3、《通典》卷6、《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仅仅简单列出各州郡物产土贡的种类,远不及敦煌文献详尽。(三)关于各地民俗民风的记载对于历史民俗地理研究意义重大。如P.2511专列“人俗”一项,细致刻画出各地的民风民俗,对于今天各地的民俗研究也甚有价值。(四)关于交通道路的记载为古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如往西域行记的几个本子,清晰记载了西行路线,依据此文书不仅可以复原出自长安或开封,穿越河西走廊、西域直至南印度等地的交通路线,以补正史之不足,而且还可使我们了解沿途国家的宗教、物产、民俗、兵力、语言等情况。(五)关于古代城址的记载在汉唐古地的考证以及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敦煌及其周围地区有不少古城址,其中有些城址在史籍中的记载混乱谬误迭出,敦煌地理文书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六)敦煌文书中关于水利方面的记载对于古代灌溉制度以及古渠道水系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七)关于地理景物的大量记载对于历史自然地理和环境变迁的研究意义重大。依据许多地理景物的纪实性描写,可以复原该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面貌,并进而研究古今地理环境的变迁,探讨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绿洲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并为今天的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服务。(八)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古地名对于历史地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文书中出现的古山名、河名、泽名、渠名、堰名、城名、关名、驿名、道路名、民族名、乡名等很多,并很注重对地名的诠释,反映了我国地名学的光荣传统。(九)关于礼佛求法的大量记载对于宗教地理学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十)文书中的古地志写卷对于我国古代方志学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