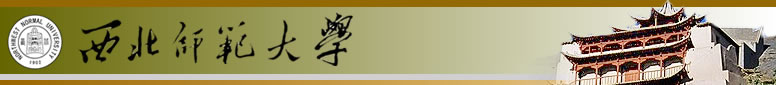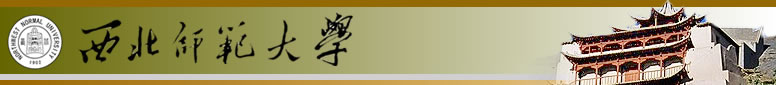第六章
敦煌文献与古代宗教研究
敦煌文书约90%为佛教经典,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的文献也不少,从而为古代宗教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第一节
敦煌佛教典籍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为汉唐时代中西交通道路上一大都会。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向内地传播,敦煌也因此成为佛教传人我国的最早落脚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中以佛经文献最为丰富,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粟特文等多种语种,约占约占整个敦煌文献的90%左右,仅从数量而言,敦煌遗书亦可称为“佛教遗书”。其中有确切纪年且年代最造者为日本书道博物馆《譬喻经》残卷,为曹魏甘露元年(公元256年,一说系前秦甘露元年,公元359年。荣新江对此说提出了疑义,他认为确切属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早写经是s797《十诵比丘戒本》,题“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具戒”这里的建初只能时西凉年号,即公元406年)。认为年代最迟者为俄国所藏32《敦煌王曹宗寿与夫人施帙写经记》,为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
公元前六世纪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前565-前485),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太子悉达多·乔答摩,释迦牟尼的生父为该国的国王净饭王,属刹帝利种姓。“悉答多”是名,意为事业成就者(亦译一切义成、吉祥),“乔答摩”是姓,意为最好的牛。由于他是释迦族的圣人,觉悟成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又称佛陀(意为觉悟者)、佛、如来、世尊、释尊等。
释迦牟尼在幼年时接受传统的婆罗门教的教育,成年以后逐渐表现出非婆罗门的思想。据说他29岁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道。起初释迦牟尼师从数论派修习禅定,即静坐思惟,专注一境(禅为禅那的略称,意为静虑,指寂静端坐,思惟审虑;定,又译为三摩地、三昧等,指止息杂念,专注一境)。后来因感到禅定境界并非是究竟之道,便改从苦行外道,用严格的绝食苦行进行修炼,以期得到灵魂的升华。他以食用野生果实为生,并且逐渐减少进食的数量,以至每天只吃一麻一麦。这样苦修了六年,使得他形容枯槁,也仍然没有得到解脱。于是他决定放弃苦行。他在尼连禅河里洗了澡,又喝了牧羊女供献的乳糜,恢复了体力。然后独自来到菩提伽耶(在今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城南约十公里处,阿育王曾在此建有大菩提寺)一颗毕钵罗树(释迦牟尼成佛后改称菩提树)下,铺上吉祥草,在草上结跏趺坐。发誓:如果不得无上菩提(智慧)宁可粉身碎骨,也终不起座。经过七天七夜得冥思苦索,终于大彻大悟,成就“无上正觉”。也就是说释迦牟尼发现了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找到了解救众生苦难的途径。在此后的四十年里,他把悟到的道理在恒河流域到处宣传,争取信众,形成教义,组成僧伽教团,建立了佛教。
释迦牟尼所传的佛法主要是四圣谛(有关人生的四种真理,即苦、集、灭、道)、八正道(八种正确的修行方法,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学(三门必修科目,即戒、定、慧)五蕴(构成众生的五项要素,即色、受、想、行、识)、十二因缘(构成众生生死流转的十二个因素或环节,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三法印(三项根本佛法,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
公元前321年孔雀王朝建立,到阿育王在位时(前273-前232)国势极强,几乎统一了印度全境。后来阿育王信奉佛教,派遣使臣高僧出国弘传佛法,佛教已传人我国西域地区。至于佛教何时传人我国内地的问题学术界不无争论。一般将《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注
引《魏略》所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之事,确定为佛教正式传人我国内地之始。
佛教在敦煌的传布可能稍晚于祖国内地,但可以确定在莫高窟开凿之前,敦煌已有佛教的活动了。最明显的就是“世居敦煌”号称“敦煌菩萨”的高僧竺法护的译经活动。竺法护在敦煌出家,他先后游历西域诸国,取回许多佛经,通晓梵文及西域诸国文字,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译佛经,是我国佛教史上早期知名的译经大师。
上文已经提到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有90%都是佛教文献,在这众多的佛典中,佛教所称的经、律、论三藏都有,而且还保存有不少久佚的经典。这些文献绝大部分是写本,少量是刻本,从写本的题记看,始自东晋,终于宋代,共五百七十多年,其中以隋唐时期的写本最多。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敦煌佛教的盛况。姜亮夫对重要经典的写本做了如下的统计:
《维摩经义记》 500——958年
凡7见
《胜鬘经义记》 504——515年
凡2见
《大般涅槃经》 506——627年
凡10见
《妙法莲华经》 550——930年
凡19见
《大方广佛华严经》
513——597年
凡4见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
530——809年
凡9见
《大智度论》 532——607年
凡3见
《金光明经》 541——848年
凡4见
《大比丘尼羯磨经》
543年
凡1见
《十地义疏》 565年
凡1见
《大集经》 583年
凡1见
《摄论疏》 601年
凡1见
以上为北魏及隋的写本
《大方便佛数恩经》
641年
凡1见
《佛说普贤菩萨证明经》
652年
凡1见
《阿毗昙毗婆沙论》
662年
凡1见
《金真玉光八景飞经》
692年
凡1见
《观世音经》
696年
凡1见
《佛说示所犯者瑜伽注境经》
707年
凡1见
《佛说阿弥陀》 709——728年
凡2见
《陀罗尼经论》 716——739年
凡2见
《大乘起信论略解》
763年
凡1见
《药师经》 764年
凡1见
《瑜伽师地论》
857年
凡1见
《大般波罗密多经》
868年
凡1见
《大佛陀罗尼经》
885年
凡1见
《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开戒品》
906年
凡1见
以上为唐代写本
《佛说佛名经》
920——934年
凡4见
《佛说无量大慈教经》
924年
凡1见
《佛说延寿命经》
959年
凡1见
以上为五代写本
佛经写本数量最多者为《妙法莲华经》,其他依次为《大般若经》、《金刚经》、《金光明经》、《维摩诘经》、《四分律》、《大般涅槃经》、《无量寿总要经》
方广锠将敦煌的佛教文献分为八大类:正藏、别藏、天台教典、毗尼藏、禅藏、宣教通俗文书、敦煌寺院文书、疑伪经等。
一、正藏
正藏是我国古代佛教大藏经最基本的形态。主要收纳由域外传入的翻译经典。由于编纂者的不同,有时也收纳一些中华佛教撰著,但数量都较少。在敦煌地区,直到张议潮归义军初期,各寺庙的正藏都是按照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来组织的。会昌废佛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以《开元录·入藏录》统一本地区、本寺庙藏经的趋势,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敦煌的正藏也改用《开元录·入藏录》予以组织。这一过程约于五代时完成,这可由敦煌遗书中所存的好几号《大唐内典录》、《沙州乞经状》、《开元录·入藏录》以及不少佛经目录得到证实。
《开元录·入藏录》共收经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分作四百八十帙。由于
放入藏经洞中的佛典不是一部完整的正藏,而是已经作废无用的残经破卷,所以现在敦煌
遗书中的佛典显得紊乱不齐,不成系统。有些经典所存特别多,如鸠摩罗什译《金刚经》,
总数约在一千八百号以上。《妙法莲华经》也至少有二千多号,它的卷一、卷二都超过五
百号,卷七则有七百多号。相反,不少经则一号也没有。据粗略统计,在一千零七十六部
经中,一号也没有的经典至少要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的经典虽有留存,但零卷碎帙,
已经凑不完整。例如《大般若经》一部六百卷,《大宝积经》一部一百二十卷。在敦煌遗书中虽有留存,均不完整。有些经典,如《大毗婆娑论》一部二百卷,在敦煌遗书中仅剩数号。
虽然如此,敦煌佛教文献中所存的正藏仍有较大的价值,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比较突出。
1.校勘价值:
敦煌遗书大抵为千年以前的古抄本,比起现代流通的各种藏经,它们更接近诸经之原
貌,因此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敦煌佛教文献中还保存了一些唐代官府的写经,是经过京城各寺的高僧大德反复校对过的,格式严谨,没有任何错字,是可以信赖的善本。有些佛经有许多副本可供比勘,有些写本本身已经用朱笔或墨笔校勘过。因此,这些古写本在校勘后世的《大藏经》刻本方面价值很高。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初编辑《大正新修大藏经》时就利用了部分敦煌写本来校勘《高丽藏》本。
2.研究价值
敦煌佛教文献中所存正藏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这些写经末尾所附的题记上。例如在北图藏雨字三十九《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五末尾有这样一段题记:“大周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巳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奉制於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正字;
翻经沙门婆罗门三藏宝思惟正梵义;
翻经沙门婆罗门尸利未读梵文;
翻经沙门七宝台上座法宝证义;
翻经沙门荆州玉泉寺弘景证义;
翻经沙门大福先寺寺主法明证义;
翻经沙门崇光寺神英证义;
翻经沙门大兴善寺复礼证义;
翻经沙门大福光寺上座波仑笔受;
翻经沙门清禅寺寺主德感证义;
翻经沙门大周西寺仁亮证义;
翻经沙门大总持寺上座大仪证义;
翻经沙门大周西寺寺主法藏证义;
翻经沙门佛授记寺都维那惠表笔受;
翻经沙门大福先寺都维那慈训证义;
请翻经沙门天宫寺明晓,
转经沙门北庭龙兴寺都维那法海.
弘建勘定。”
上面题记中出现的不少人都在中国佛教教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如宝恩惟翻译过好几部经典。弘景、复礼、法藏等都参加过《八十华严》的翻译。法藏更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的著名僧人。可见上述题记对于我们研究这些僧人的活动以及当时僧人隶寺制度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还有北图藏新字657号义净《新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卷末尾除了参与译经的僧人名录外,还有:
“中大夫检校兵部侍郎臣崔提润文;
太中大夫行给事中上柱国臣卢祭润文、正字;
太中大夫宗正寺少卿臣沈务本润文;
中大夫前吉州长史上柱国臣李无敬正字;
秘书省楷书令史臣杜元礼写;
典秘书省楷书令史臣杨乾僧;
判官朝义郎著作佐郎臣刘令植;
使秘书监驸马都尉上柱国观国公臣杨慎交。”
从这些题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武周时期译场的组织,工作方法,与朝廷的关系,僧俗人等在译场中的作用等等。正因为有这样的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规则,朝廷的大力支持,才能保证译经的质量。这种用集体力量来完成重要典籍翻译的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另外,在敦煌文书中还有一批佛典是在长安由写经坊抄出的,如P3278号《金刚经》残卷末尾就有这样的题记:
“上元三年(676)九月十六日书手程君度写
用纸十二张
装潢手
解集、
初校群书手
敬诲
再校群书手
敬诲
三校群书手
敬诲
详阅
太原寺大德 神符
详阅
太原寺大德 嘉尚
详阅
太原寺主 慧立
详阅
太原寺上座 道成
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
李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
阎玄道”。
象这样的题记在敦煌佛教文书中总共有三十多号。从这一类题记可以看出:1、当时
把写经当作一件十分严肃认真的大事,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并派专人管理,监督此事。2、抄经有一定的程式,一定的工作规范。整个抄经工作分解为若干环节,由人分别负责。3、抄写十分认真,抄后三校,并由四人详阅,以免错讹。参加者各自署名,以示负责。4、抄写佛经是由国家专门机构和寺院僧人协同进行。5、专门记载用纸多少,一方面说明经文格式已形成一定的规制,也说明纸张珍贵,不得随便浪费与贪污。6、这些经典出现在敦煌藏经洞,说明中央政府曾大规模向各地颁赐过佛经。7、参与详阅的太原寺主慧立,可能就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作者。他是唐玄奘的弟子,曾参与玄奘译场工作。在僧传中没有其传记,他的事迹散见于其他人的传记中。有些认为他是魏国西寺沙门。这个题记之发现,丰富了对他生平的知识。
写经题记中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社会生活、风俗习惯、职官制度以及史事等,
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3、文物价值
总的来说,敦煌遗书都是文物,都是稀世珍宝。但是在所有佛教典籍中正藏地位特别崇高,人们在抄写时也特别认真、虔诚,所以正藏的价值也就显得更高。前面已经提到敦煌文书中有一批宫廷写本,这批写本用纸精良,抄写认真,校勘精心,由专聘的官方楷书高手写出,其书品、字品都是上佳之作。历史上曾有一件唐太宗时期的宫廷写本《善见律》传世,被历代书法家、收藏家叹为至宝,展转流藏,至到今天。
《开元录》是撰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的一部经录。其后,在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僧人圆照曾撰《贞元续开元录》,将《开元录》撰成后六十余年间新译佛典逐一著录,作为对《开元录》的补充。这部目录以后也被人们作为造藏的依据。此外,宋代开国后,诸帝均较重佛事,专设译经院从事佛经的翻译,亦有经录专门记载其时翻译的经典及翻译概况。从《赵城金藏》与《高丽藏》的比较可知,宋刻《开宝臧》的基本结构是《开元录·入藏录》所收经;《贞元续开元录》所收经;再加宋朝新译经等三大部分。这就是10至11世纪我国佛教大藏经正藏的标准形态。敦煌地区的正藏也是如此,早在五代时,当地佛教教团就依《开元录·入藏录》配齐了本地藏经。《贞元续开元录》所载诸经也传入敦煌。现敦煌遗书中存有的一批不空译经,就属于《贞元续开元录》。宋朝时敦煌也曾受过宋廷赐予的新译佛典,因此敦煌当地的正藏与全国其它地区的正藏应无太大区别。敦煌的战乱较少;又未遭受会昌佛难,因此保存了一大批内地没有的经典。一是部分经典在开元十八年之前译出,内地已经亡佚,故智升未能见到,未能收入《开元录》中,敦煌却有保留,如北图藏海字64,题名《诸经佛名》卷上、《众经别录》,还有竺昙无兰译本《佛说罪业应报教化地狱经》,不空译本《梵汉翻对字音般若心经》等。二是部分经典在北庭及敦煌等地译出,未能传入中原,不为中原人士所知,仅流传于西北一带,并被保存在敦煌遗书中。如昙倩在安西翻译的《金刚坛广大清净陀罗尼经》,失译的《入无分别总持经》,失译《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诸星母陀罗尼经》、《萨婆多宗五事论》、《菩萨律仪二十颂》、《八转声颂》、《释迦牟尼如来像法灭尽之记》、《大乘四法经》、《大乘稻秆经》、《六门陀罗尼经》,失译《因缘心论颂》、《因缘心论释》,异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等。
上述两类经典,虽为敦煌独有而不为内地正藏所收,但按照中国大藏经的组织理论,它
们都是应该入藏的。敦煌藏经洞保存了这一批经典,是对汉文大藏经的一大贡献。
二、别藏
别藏是专收中华佛教撰著的中国佛教典籍集成。在中国大藏经形成过程中,出现两种类型的正藏。一种兼收域外译典和中华撰著;另一种正藏则几乎不收,甚至完全不收中华撰著。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发展,后一种形式逐渐成为编撰大藏经僧人们的首选。唐代所编的正藏大抵不收中华撰著。智升的《开元录》基本上沿袭了这种态度但也有少量的收纳,在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正藏中,属于中华撰著者仅四十部、三百六十八卷,只占全藏的百分之七,主要是僧史、目录、音义、集经方面的内容。还有唐代西明寺的道宣曾奉唐高宗敕命造一部大藏,高宗要求把毗赞佛教有功的中华撰著也收编入藏,道宣无奈只好在所编的西明寺大藏中专门设有“杂藏”一目,收录法苑、法集、僧史之类的中华撰著。但是在他自己编定的《大唐内典录·入藏录》中把那批中华撰著统统删去,不留一部,甚至连自己所撰的大批律疏、《唐高僧传》等一批著作都不予保留表明了“正藏不收中华撰著”的鲜明态度。其实及至唐代中国人所撰的佛教著作,总数已超过万卷。
由于正藏不收中华佛教撰著,便有人将这些撰著专门汇集起来,结集为“别藏’.但是在大多数佛教僧人看来,收有中华佛教撰著的别藏的地位远远比不上传统的正藏。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别藏不被重视,以至只能自生自灭,大批中华佛教撰著散佚无存。值得庆幸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则保留了大批古逸中华佛教撰著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佛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中华佛教撰著大体可分为:1、经律论疏部、2、法苑法集部、3、诸宗部、4、史传部、5、礼忏赞颂部、6感应兴敬部、7、目录音义部、8、释氏杂文部等八类。
其中,尤其以各种疏释数量最多。如《般若心经》是般若经典的精要,历代注疏者甚多,但历代大藏所存有的唐代以前注疏仅有八种,而在敦煌遗书中则存有唐以前的《般若心经疏》十种。其中仅一种已为传世大藏所收,其余九种均是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这样,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唐以前《般若心经》的注疏就有十七种了。敦煌遗书中所存的《般若心经》注疏有不少诠释精要,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另外,如昙旷所撰《大乘二十二问》,《净名经关中集解疏》,唐法成的《瑜珈论手记》,《瑜珈论分门记》等,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从史传资料来讲,王锡的《顿悟大乘正理决》是研究西藏佛教史中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相互交流史的重要资料
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题目。研究这个问题,主要地不是领先翻译的典籍,而要靠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著作。在这一方面.敦煌遗书为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天地。随着对敦煌遗书的全面系统的整理,敦煌遗书一定会为这一研究课题提供更多、更宝贵的资料。
三、天台教典
天台教典是天台宗编纂的阐述弘扬本宗宗义的典籍。它最初由灌顶撰成,包括慧思、智
颧、灌顶三人的著怍,其后随着天台宗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唐代早、中期,天白宗曾兴盛
一时,天台教典在全国流传,也传到了敦煌。敦煌遗书中存有《天台分门图》、《天台四教
义》、《天台四戒分门》、《天台智者大师发愿文》及一批天台宗的经疏。晚唐五代时,天台宗的典籍遭到极大破坏,几乎荡然无存,以致天台宗的高僧们对自己的宗义也搞不太清了。后在吴越王的支持下从朝鲜、日本找回了若干天台宗典籍,但毕竟已无从恢复旧观。在敦煌遗书中所存天台宗典籍的数量虽不多,远不能凑成一部天台教典,但对研究天台宗义及天台教典的情况仍有极大意义。
四、毗尼藏
毗尼的梵文意思为律,毗尼藏也就是律藏。毗尼藏原系律宗所编的本宗典籍的结集。约产生于唐高宗时期。由于它专门论述戒律的意义,守戒之规范、要求,不过多涉及佛教义理,而遵守戒律又是佛教各宗各派的基本信条,故毗尼藏在一定程衷上可说宗派色彩最少。其后在全国各地流传,也传到了敦煌。如在罗振玉编《莫高窟石室秘录》载有《寺历》三卷,中有“前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大德三学教授兼毗尼藏主赐紫翟和尚邈真赞”、“敦煌唱导法将兼毗尼藏主广平宋律伯采真赞”、“前敦煌都毗尼藏主始平阴律伯真仪赞”等,说明毗尼藏在敦煌颇为人们所重视。现敦煌遗书中所存道宣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抄》、《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怀素的《四分律开宗记》等等,实际上都是原毗尼藏的内容。
五、禅藏
禅宗是彻底中国化了的宗教,八世纪以来禅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因其简单易行而得到士大夫和广大下层百姓的普遍欢迎和热衷信仰,同时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和提倡。
禅宗的盛行,也随之产生了大量的中国禅僧所写的著作。但是由于安史之乱、会昌法难的打击和禅宗内部的斗争,以至一些早期的禅籍渐渐亡佚,其教法也不为后世所了解。而在敦煌遗书中大量保存了一批早期禅宗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反映早期禅宗思想的语录,如慧能的《六祖坛经》,神会的《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迄今为止,已经发现敦煌写本中有五个《坛经》抄本,其中最好的写本现存于敦煌市博物馆的任子宜旧藏本。还有反映北禅宗灯史的《传法宝记》和《楞伽师资记》等。《传法宝记》是成书于唐玄宗初年(713年)的一部北宗灯史,早已亡佚,敦煌写本中发现有P.2634、P.3559、P.3858、S.10484四个写本;《楞伽师资记》是稍迟于《传法宝记》成书的又一部北宗灯史,也早已亡佚,而在敦煌文书中已发现八件《楞伽师资记》写本,其中三件可能属于一个写本(S.2045、P.3294、P.3436、Dx.1728+P.3537+S.4272、.3703、P.4564)。学者们根据这些文献对早期禅宗史作了许多卓越的研究。但这些禅宗典籍为什么会如此集中地保存在敦煌藏经洞,这个问题便无人能回答了。现在问题已经清楚,这批典籍原来都是传到敦煌的禅藏的一部分。
禅藏是由唐宗密编纂的关于禅学与禅宗典籍的集成。编成后时间不长,即逢会昌废佛,
故中原地区的禅藏大抵在劫难逃。偶然流传下来的,后来也因种种原因而亡佚。所以敦煌藏
经洞保留下来的禅藏残卷便格外珍贵。
关于这部禅藏的内容、结构,宗密在他为禅藏写的总序《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讲得很清楚:“故今所集之次者,先录达磨一宗,次编诸家杂述,后写印宗圣教。”(宗密《禅源老诠集都序》卷下)。他还具体点了一些著作的名称:“或因修炼功至证得.即以之示人,(‘求那、僧稠、卧轮之类);或因听读经教生解,而以之摄众(惠闻禅师之类);或降其迹而适性,一时间警策群迷(志公、傅大士、王焚志之类);或高节而守法,一国中轨范噌倡(庐山远公之类)。这样,我们便可以根据宗密的记述把这部禅藏恢复出来。
《神会语录》、《坛语》、《法海本坛经》、《二入四行论》、《楞伽师资记》、《历代法宝记》、《达嘻祥师观门》、《观心沦》、《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等一批禅宗文献的发现,已使中国弹宗研究的面貌完全改观。存于敦煌遗书中的禅藏的恢复,必能将禅宗研究提高到新的更高的阶段
六、宣教通俗文书
所谓宣教通俗文书是指寺院向僧俗人等宣传佛教教义以启导正信的一些通俗作品。它
们大抵是根据经义敷衍而成。根据其不同特点,可分作讲经文、讲因缘文、变文等三大类。另外,象押座文、解座文亦可附入此类。
传统佛教高僧们对这一类宣教通俗文书是很不以为然的。如唐文宗时著名俗讲憎人文溆开俗讲时,“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甚至唐文宗也采用文溆俗讲的声调创作新曲,名叫“文溆子”。可是正统派学者、文人却评论说:“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传统的《高憎传》中也从来不收文溆这样俗讲僧的传记。其实,僧人的俗讲不但影响了当时的广大民众、当时的文学体裁,而且对后代民众佛教、文学艺术都有重大影响。所以近代以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七、敦煌寺院文书
藏经洞中还收藏了一大批反映敦煌当地寺院活动的文书。其中有寺院宗教活动文书。如大批的礼忏文、羯磨文、授戒文等等;有寺院宗教史传文书,如关于高僧事迹的载述、藐真赞等等;有寺院经济活动的文书,如各种买卖、典押、雇工、借贷、请便契、便物历等等;有关于寺院佛典的目录,如藏经录、勘经录、流通录、转经录、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等;有关于石窟、壁画的文书,如白画、画稿、榜题以及木刻画、彩绘等等。
敦煌寺院的各类文书为我们描绘出丰富多彩的敦煌寺院生活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研究
敦煌佛教的重要依据。我们知道,中国佛教虽是一个整体,但从早期起,各地区的佛教便
呈现出不同的区域性特点。如东晋释道安时期,凉土佛教、关中佛教、荆襄佛教、东鲁佛
教、建康佛教便各有自己的特色。南北朝时期,南北佛教显示出显然不同的风格。随着隋
唐的统一,南北佛教的交融,学风也相互渗透影响。但是,各地佛教各有其特点的情况并
没有完全改变。研究不同地区的佛教的不同特点,乃是佛教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资
料的局限,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大批敦煌寺院
文书为我们研究敦煌地区的佛教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使我们可以把敦煌佛教当作一个标本来进行解剖分析,其价值之高,自不待言。
八、疑伪经
按照佛藏理论,凡属“经”,都应是由佛口授的。凡属非佛口授,而又妄称为“经”者,杜属于伪经。为了保持佛教传统的纯洁,正本清源,中国佛教从来十分重视经典的真伪之辨。并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辨别真伪的具体办法。也就是检索传译的记载,鉴别经典的内容及文风。对于那些一时无法确定其真伪的经典,则一般称之为“疑经”,置于藏外待考。敦煌遗书中就存在一大批传统被视怍疑伪经的经典。
仔细考察这些疑伪经,可以发现它们均反映了中国佛教的某一发展断面,具有极高的
研究价值。例如《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是在梁武帝提倡断屠食素的背景下撰成的,它可
与《广弘明集》中的记载相印证,说明了汉传佛教素食传统的形成经过。如《高王观世音
经》反映了观世音信仰在中国的形成与流传。《十王经》反映了地狱观念的演变,如此等等。
疑伪经实际上反映了印度佛教怎撵一步步地中国化,从而对中国佛教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已
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传统被认作疑伪经的某些经典,有些实际上的确是从域外传入,并非中国人伪造的。不过由于它们不是在正规的译场中译出,传译过程不大为人们所知,有的文字又比较质朴,或者表达的思想与前此的正统佛教思想不甚吻合,因而被人们视作疑伪经。如敦煌遗书《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就是一例。这类经典的发现,告诉我们对传统视为疑伪经的经典必须区别情况,具体分析。同时,这类经典的发现,也丰富了我们对印度佛教典籍的知识。
第二节
敦煌道教文献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奉老子为祖师,尊称“太上老君”,其《道德经》是道教的根本经典之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积累了大量的经籍文书,后多编入《道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兴起于东汉中后期。至魏晋时,已传入河西地区。敦煌出土的魏晋时期的道教木简符篆,证明当时张氏天师道在河西可能已有传播。十六国河西五凉政权统治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常可以见到道教所崇奉的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的形象,最典型者为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笙绘画。《晋书》卷一百二十九也有关于北凉沮渠蒙逊“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中有玄石神图”的记载。敦煌石窟中的北魏第249窟和西魏第285窟顶部壁画,绘有东王公、西王母分别驾龙凤车出行,前面方士开路,后有神兽随行的场面。这些都说明河西地区崇奉西王母由来已久。北魏统一河西之后,河西道教进入鼎盛时期,其明显的证据,是敦煌石室中发现的一批古道教遗书。
据研究统计,敦煌道教遗书(一般亦称敦煌道经),包括《老》、《庄》、《文》、《列》诸子,道教经典、科戒、论著、类书及诗赋变文等,共计约五百余件。其中若干卷可以缀合为一,所以实际数字,可能没有五百,与庞大的佛教经典相比,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比仅二百余件儒家经典要多。
这些道教文献的发现,对于道教研究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们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乏,揭示了河西道教发展的状况。敦煌道教文献中,有数十件抄本末尾附有题记或盟约,它们记载了当时抄写或校对道经的道士及官员们的姓名、身份、抄经的地点、年代、事由,以及传授道经的程序,是研究河西地区道教发展的重要依据。据考证,敦煌道经抄写的年代,约在六世纪中叶至八世纪中叶,也就是北朝后期至唐中期之间约二百余年的时间。敦煌道经抄本题记中出现的年号,起于隋大业八年(612),止于唐至德二载(757),尤其以唐高宗、武后至玄宗时的年号最多。据史书记载,北魏统一河西之后北朝境内的道教经寇谦之的改革及魏太武帝、周武帝等统治者的提倡而大为兴盛,道书的整理编目工作获得了很大的进展。
唐代前期,尤其是高宗、武后至玄宗时,由于统治者的崇奉,加上李唐与老子同姓,以老子为远祖,尊崇道教,道教的发展达到鼎盛,成为与儒佛二教并立的三教之一,《道藏》的编修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随着内地道教的繁荣,加上封建国家强盛、中西交流畅通,河西地区的道教发展也臻于极盛,大批道经集中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敦煌。从道经题记中可以看出,唐时沙州敦煌有神泉、清都、白鹤、冲虚(女道观)、开元等数座道教宫观,参加写经或盟受道经的道士、女冠及道教弟子的名字达数十人,遍及敦煌各乡。甘肃武威博物馆也收藏有垂拱三年(687)的道教天真造像碑。可见当时河西道教之盛。而这种盛况又是与内地道教的影响不可分的。
敦煌道经多数为当时内地流传的《道德经》、《灵宝经》、《上清经》及道教类书、科戒等,单是一部隋唐时流行的《太玄真一本际经》,就有抄本一百零三件之多。许多经典题记标明原写于内地的道观,如京师玄都观、景龙观、河南府大弘道观等,参与校写监督的还有隋唐中央政府秘书省、国子监的官员(参见S.2295,P.2457、3725等抄本题记)。敦煌道士也有入京为皇室写经的。如贞松堂藏《本际经》卷五题记称:“冲虚观主宋妙仙入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这里所谓的“一切经”,实际上是唐代《道藏》。s.1513《一切道经序》,据考证其内容是唐高宗或武后为悼念“孝敬皇帝”(即太子李弘)之病逝,而敕令抄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参与这一活动的有内地的道观,也有敦煌道观,S.1513《老子像名经》抄本为一证据,又如P.3233《洞渊神咒经》卷一题记也注明“麟德元年(664)七月廿一日奉敕为太子写于灵应观”。可见当时中土与河西道教的密切关系。
唐代佛教发展也很兴盛,但在统治者的推崇下,道教尚能与佛教争得一席之地。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吐蕃乘机攻据河西地区,占领瓜、沙诸州将近百年,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地区不再用唐朝年号,而以干支纪年,大兴佛教,河西地区汉族所信奉的道教,在失去唐王朝支持的情况下,可能因此而日渐衰落。现存敦煌道经题记中,自至德童年以后,不再出现唐朝年号。除个别卷子(如P.2350、P·4659等)外,以干支纪年的道经题记极少。许多道经被撕裂或重新粘贴后,作为习字纸在背面另写了佛经。敦煌变文中,属于道教的变文,也只有一部约成书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叶净能诗》(s.6836)留传下来。这些情况都说明自唐中期以后,河西道教渐趋衰微,残存的道经也受到兴盛的佛教的破坏。此后敦煌道教在历史上长期未见于文献记载,出现一大段空白。清代道光十一年(1831)刊《敦煌县志》卷三,记载敦煌城西三里有雍正八年(1730)所建道教的西云观,城东南有乾隆五十年(1785)所建太清宫,说明清代道教在河西恢复了活动。至清末,又因道士王圆篆,而使敦煌遗书重见于世。
敦煌道经发现的价值,还在于它能弥补《道藏》之不足。现存的《道藏》,编成于明正统至万历年间,距唐代始修《道藏》已有六、七百年。这期间经历代兵火战乱及元代焚毁道经之祸,许多早期道经佚失残缺。尚保存的部分亦不免真伪混杂、文字舛谬、篇卷互异。敦煌道经抄写既早,而且半数以上卷子全部或部分未见于《正统道藏》,故其于存佚补缺、纠谬辨伪、解决道教研究中一些悬而难决的问题,有极重要的价值。例如《老子道德经》,在北京、巴黎、伦敦三处都有所藏,巴黎所藏最多,也最完整。约有二十余件。P·2584是全部的《道镜》,P·2420、P·2471两卷是全部的《德经》,而且完好无损。还有如P·2375、P2347等卷可以拼合成全卷。《道德经》是道教的更本经典之一,敦煌不仅有大量的抄本,而且还发现六种注疏,即河上公注(P·2639、S·477、S·3926)、想尔注(S·6825)、李荣注(P·2954、P·2864、P·3237)、成玄英义疏(P·2517)、唐玄宗注及疏P·3592、P·2823)、佚名注等。其中《老子想尔注》和成玄英的《义疏》是《道藏》未收的佚书。《老子想尔注》共两卷,唐人称出自张鲁或张道陵之手,敦煌残卷(S·6825)有饶宗颐先生做的老子想尔注校证,从内容看是五斗米道信徒的著述,反映了早期道教思想,十分珍贵。还有对《道德经》的各种题解,如《老子道德经序诀》(S·75、P·2407)、《老子道德经开题》(P·2517)、《玄言新记明老部》(P·2462)等。这些文献对老子和道教的研究都很重要。
再如老子化胡之说,早在东汉桓帝时就出现了,西晋道士王浮根据传说,编成《老子化胡经》称老子出关,西越流沙,入夷狄为佛,教化胡人,显然是道教徒为攻击佛教而编造的。在南北朝隋唐的佛道斗争中,产生了一系列《化胡经》类的著作,从唐朝开始,统治者为了调和佛道二教的矛盾,不时禁毁《化胡经》,至元代焚经后《化胡经》失传,致使研究者难知其究竟。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不止一种《化胡经》,其中有十卷本《化胡经》的序、卷一、二、八、十和《太上灵宝老子化胡妙经》,不但使近人王维诚、福井康顺等人对化胡说之探讨大为深入,而且也成为研究佛道论衡和思想史,以及研究唐代对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还有如《无上秘要》、《太平经》二书,均为研究早期道教的重要文献,可惜现存《道藏》本残缺很多,而且没有完整的目录,其史料价值也因此而降低。敦煌《无上秘要目录》及唐抄残本,以及《太平经目录》之发现,使二书全貌得以显露,而且可略补《道藏》本《无上秘要》之缺,证实现存《太平经钞》甲部之伪。成书于北朝末年的《升玄内教经》和隋唐初增补成书的《太玄真一本际经》是广泛流传的两部道经,敦煌道经写本分别有22件和119件,吐鲁番写本中也有残片发现,但以后这两部道经得先后佚失,今本《道藏》分别仅存一卷内容。敦煌写本为研究这两部道经的产生、流传和影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中外学者研究敦煌道教与道经之论文与专著,已不下百种。日本吉冈义丰《道教与佛教》一书,是利用敦煌遗书研究佛道二教之名著。日本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积数十年研究之功,从北京、伦敦、巴黎、列宁格勒、台北、日本、柏林等各处所藏敦煌遗书中,发掘道经抄本共四百九十三件,分别著录其标题、卷号、题记、保存情况,并考证其年代、作者,与《道藏》本之关系及文字校勘,末附目录、道观表、道士名表、纪年表、引用经名表,《敦煌道经图录编》则选印《目录编》著录的道经影片。这是迄今较为完整的整理敦煌道经的文献。
第三节
祆教、景教、摩尼教文献
一、祆教文献
祆教是古代中国人对传入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的称呼。该教原为古波斯人查拉斯图拉(后人因袭古希腊人的讹音,称之为琐罗亚斯德)所立。其创立年代,学术界尚多争论。传统认为查拉斯图拉生活于公元前628年至前551年,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多有学者相信其应生活于公元前1700年至前1400年之间。该教奉《阿维斯陀经》为根本经典。
由于该教宣称宇宙万物无非分为善恶二大类,分别为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和恶神安格拉·曼纽所创造,故多有学者认为该教系典型的善恶二元论宗教;鉴于该教的原始经典又称善恶二神本为孪生兄弟,只因偶然的选择才变为仇敌,故有的学者认为该教应属不彻底的善恶二元论宗教;鉴于该教号召信徒唯善神是尊是从,跟随善神以最后征服恶神,故不少学者又认为该教应归一神教之列。折衷并更为当今一般学者所接受的说法是:该教在神学上为一神论,在哲学上为二元论。因为该教信徒把日月星辰等视为最高善神之属神加以崇拜,故古代中国人以为其拜天。唐之前史书载西域诸民族中有事奉天神、胡天神者,其中有的便属该教之范畴。唐初专造了一从示从天的“祆”字,称该教为祆教,称其所事之神为袄神。是因为该教视圣火为其最高善神之化身,日常祭祀之,故又常被称为拜火教或火教。
古代中国人还综合该教拜火拜天的特征,称其为火袄教。波斯萨珊王朝时期(224—651),该教被奉为国教,遂在波斯国中臻于鼎盛,并在中亚地区广为流播;其传入中国内地,也当在这一时期。中国史书对该教的明确记录,可追溯到六世纪初;但其在华活动的痕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多有学者追溯到五世纪中叶。若从古代中西交通密切的程度推断,该教信徒之进入中国,则尚应早于五世纪。
从唐代直至北宋,该教信徒曾在敦煌地区广为活动。虽然祆教的原始经典尚未在敦煌文书中发现,但有关祆教的记载敦煌文书中多有提及。研究中国祆教的经典文章――陈垣的《火祆教入中国考》,根据正史的记载,认为火祆之名闻于中国,自北魏南梁开始。荣新江根据对敦煌长城烽燧下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内容的释读,确证祆教早在公元四世纪初就由粟特人带到中国。在敦煌文书中,我们可以得知唐朝时沙州城东有祆祠。歌咏敦煌名胜古迹的《敦煌二十咏》,也有一首《安城祆咏》。敦煌归义军官府的支出帐中常常有“赛祆”的记载,说明归义军时期祆教仍在敦煌流行,而且敦煌的祆祠赛神已被纳入中国的传统祭祀当中,使人们认识到祆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侧面。敦煌藏经洞中还保存的一幅祆教图像,姜伯勤认为其年代应当是十世纪的。它证明了祆教的存在,并为艺术家判定祆教图像提供了完整的资料。至于该教的原始经典,敦煌文书中则尚未发现。
二、景教文献
基督教传人中国在初唐
之时,时称“大秦景教”或“大秦教”。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
据建中二年(781)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唐代官方文献的记载,贞观九年(635),该教传教士阿罗本等人经波斯来中国长安,唐太宗派宰臣房玄龄率仪仗队去西郊迎接。阿罗本在唐廷受到很高的礼遇。太宗听了其教义后,也大加赞赏,于贞观十二年下诏说:“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于长安义宁坊赐建景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太宗觉得景教合于道家之旨,有利于教化,所以也给予了支持。在唐高宗时,还准许诸州建立各自的景教寺,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不少教士还担任了朝廷和军队中的重要职务。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灭佛,祸及一切外国宗教,景教也遭到毁灭。“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见《旧唐书》)。于是景教在内地被禁绝。但在边远地区仍有景教在活动。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的大量敦煌遗书中,有该教的汉译经典抄本,已确认的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大秦景教宜元本经》、《志玄安乐经》、《序听迷诗所经》、《一神论》等。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与《尊经》共成一卷(P·3847),“三威”即圣父、圣子、生灵“三位一体”,“蒙度”为仰望救赎之意。全经有七言诗四十四句,是教会举行宗教仪式时诵唱用的赞美诗。相当于拉丁文本的,荣归上帝诵》。此经为叙利亚文本的汉译本,译者为八世纪来华的景教传教师景净;《尊经》简要介绍了景教经典的数量以及汉译的情况,颇有史料价值。
这些文献是我们研究景教在唐代的传播、以及景教仪式和教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三、摩尼教文献
摩尼教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宗教。我国旧译为明教、末尼教、牟尼教、明尊教、而尊教等。该教在琐罗亚斯德教的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诺斯替教派、佛教等多种宗教的成分,而形成自己的信仰体系,并创立了一套独特的戒律和寺院制度。
摩尼教以“二宗三际论”为其核心,“二宗”是指光明与黑暗两种对立的力量,“三际”是指二宗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发展阶段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主张善恶二元论。该教创立不久,即在萨珊波斯帝国境内广为传播,并迅速传入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一带,并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内地;从大西洋西岸直到中国东南沿海,都有过其教徒活动,时间长达千年之久。该教在西传时逐步基督教化,在东传时则日益佛教化。教主及其尔后的门徒,都十分重视经典的撰译。二十世纪来已发现大量该教经典的残简,包括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突厥文、科普特文、希腊文等十余种文字;至于汉文经典则见于敦煌遗书,计有《摩尼教残经》、《下部赞》、《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三种。
《摩尼教残经》(北图宇字56、新字8470)是我国迄今收藏的唯一汉文摩尼教经典,经文主要以教主对弟子答问的形式,阐发摩尼关于人类自身并存明暗二性的教义,对于研究摩尼教及其在中国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部赞》(S·2659)是中国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诵唱用的赞美诗,在现存各种文字的摩尼教赞美诗中,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据考证,此经系唐代后期的译作。《摩尼光佛教法仪略》(S·2659、P·3884)系唐玄宗时在华摩尼传教士奉诏撰写的一个解释性文件,其主要内容为简要介绍摩尼教的起源、教主摩尼的主要著作、教团的组织、教义的核心等。对研究当时中亚地区和中国内地的摩尼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摩尼教曾在唐代中国合法盛行了一段时期,至会昌五年(845),遭唐武宗敕禁,中亚传教师被驱逐,遂失去与国外教团的组织联系,自行在中国境内,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传播,上层逐步道化、佛化,下层则汇入民间秘密结社。至明初,仍有该教明显活动的痕迹。由于该教在中国传播时逐渐华化,故后期多被称为明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