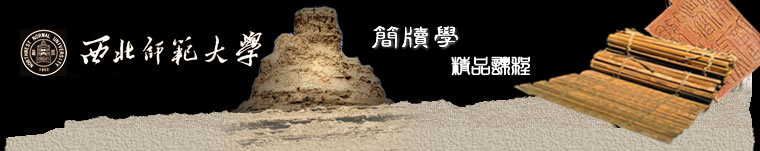第八章 简牍中的民族政策及民族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出土简牍主要反映秦汉时期生活在北方和西北广大地区的匈奴、羌、乌孙、于阗、鄯善、康居、大月氏等民族同中原王朝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贡使往来,这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秦简反映的民族政策
一、云梦秦简反映的民族政策
1.《属邦》的记载
秦律《属邦》记载,“道官相输隶臣妾、收人,必署其已稟年日月,受衣未受,有妻毋(无)有。受着以律续食衣之。”这条简文的大意为:“各道官府输送隶臣妾或被收捕的人,必须写明已领口粮的年月日数,有没有领过衣服,有没有妻。如系领受者,应依法继续给予衣食。”
“属邦”即秦国的“典属国”管理下的被征服的非华夏民族国家,亦称“臣邦”。这条记载的标题里提到了“属邦”一词,在内容中也提到了“道”,“道”指少数民族聚居的县,这说明秦朝已经制定了对少数民族“罪犯”的处罚政策。但这种处罚政策只是针对少数民族中的被统治阶级而言,例如在《法律问答中》提到的对有些人想要脱离其“主长”的管理从而进一步脱离秦的统治,他们的这种行为是不予允许的。
2.《法律答问》记载
《法律答问》规定,“‘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着,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该简文的大意为:“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的人,对其主长补满而想去夏的,不予准许。”什么叫“去夏”?想离开秦的属境,称为“去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为‘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谓是;‘真’。·可(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这条简牍所表达的意思是:“真臣邦君公有罪,应判处耐刑以上,可命赎罪。”什么叫“真”?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的父母所生子,以及出生在其他国的,称为“真”。什么叫“夏子”?父为臣属于秦的少数民族,母亲是秦人,其子称为“夏子”。
“可(何)谓‘赎鬼薪鋈’?可(何)谓‘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爵当上造以上,有罪当赎者,其为群盗,令赎鬼薪鋈足;其有府(腐)罪,【赎】宫。其它罪比群盗者亦如此。”该条简牍所表达的意思为:怎样是“赎鬼薪鋈”?怎样是“赎宫”?臣邦真戎君长,相当于上造以上的爵位,有罪应准赎免,如为群盗,判为赎鬼薪鋈足;如有应处宫刑的罪,判为赎宫。其它与群盗同样的罪也照此处理。
秦王朝以实行严刑峻法著称于世,对少数民族地区也执行严格的法律,但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支持与拥护,巩固其统治,对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法律上特别加以宽容,在民族地区实行轻于内地的刑事惩罚政策。《法律问答》中关于民族政策的另外两条记载就反映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规定了一些在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如在“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一条的记载中,就表明,如果是“臣邦”的统治阶级犯罪了就可以用金钱进行赎买。而在另外一条的问答中,则详细说明了爵位在“上造”以上的少数民族首领在犯罪时赎罪的细节:如为群盗,判为赎鬼薪鋈足;如有应处宫刑的罪,判为赎宫。其它与群盗同样的罪也照此处理。
另外,云梦秦简中还有关于民族成分的法律规定。如《法律问答》中记载的“……可(何)为“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谓是“真”。·可(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这条内容对少数民族的血缘关系及民族成分做了严格的规定,认为只有父母都是少数民族,所生的孩子或是在其他国家所生的孩子才能被认为是少数民族,而“臣邦父,秦母”所生的孩子还是被认定为“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民族成分的法律条文,这种规定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适用范围也有限,但却是第一次提出,因此意义非凡。同时这条法律也表明秦的统治阶级允许秦人与少数民族通婚,并且为了保证秦本身人口数量的增长,规定了秦人与少数民族所生的孩子为“夏子”,而非少数民族。
二、云梦秦简反映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作用
第一,秦朝的民族政策具有一定的阶级性。秦朝政府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的利益是竭力维护的,律文的目的是在保证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对被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而对于少数民族下层来说,他们的待遇就没有那么优厚了,犯罪之后所受到的惩罚同秦的被统治阶级所受到的惩罚相同,同样是被压迫和剥削的对象。
第二,秦朝的民族政策并不是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作用。例如对于巴国和蜀国的少数民族,秦朝的优待安抚以及惩罚政策都起到了很好的凝聚作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但是对于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就作用不大,如义渠。义渠距秦的统治中心虽然很近,但却始终与秦为敌,战乱不断。《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至周贞王八年(公元前461),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于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44),秦伐义渠,掳其王,后十四年(公元前430),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公元前335),义渠败秦师于洛。”
第三,秦王朝制定的民族政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云梦秦简的《属邦》一条中提到了“道官”一词,这里的“道”史书上解释为:“县有蛮夷曰道”,这就表明早在秦朝就已经建立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专门的管理机构。同时,从《法律问答》记载的对少数民族上层的优待政策可以看出秦朝已经开始利用少数民族的首领对当地的人民进行统治。这种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某些习惯法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内部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处理纠纷的民族政策为后代的封建王朝所承袭和发展,成为唐代的“羁縻政策”、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的开端,可以说是后代的这些民族政策滥觞于秦。
第二节汉简反映的汉羌关系
羌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的古羌人集中在今陕、甘、川、宁的广大地区。《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文献中将其称为“羌戎”、“西羌”或“西戎”。《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说明羌人源于姜姓。“姜”字从女,本为姜族女子的氏,“羌”字从人,本为一种有别于他族的群的族名。羌、姜乃一音之转。“姜之与羌,其字出于同源,盖彼族以羊为图腾,故在姓为姜,在种为羌。”两汉时期,大量西羌迁入内地,汉王朝采取了较为积极的管理措施,并对其实施了许多优待政策。中原王朝对羌族所采取的诸多优惠政策,在当时的汉羌民族融合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羌的内迁,也加速了羌族的社会发展,更推动了其汉化的进程。
汉朝与羌的关系,大量汉简的出土和发掘为这一问题的研究补充了新的资料。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关羌人的简有近百枚,保存了关于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资料,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在中央和地方专门设置管理羌人事务的官吏的状况、汉政府对羌人的具体管理措施以及对其所采取的许多优惠政策等情况,这些资料对于我们探讨有关汉羌关系和中原王朝对羌人的诸多政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有重要意义。
一、两汉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羌人的职官制度
两汉时期,为了加强对羌人的有效管理,中原王朝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置专属官吏,采取相关举措,以便对羌族实施有效地管理。根据悬泉汉简所反映的情况,这些官吏的设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羌族社会发展和中原王朝稳定的重要保证。所设官吏的具体职务及职能简述如下:
1.护羌校尉
护羌校尉是两汉时期管理羌人事务的高级官吏。护羌校尉始置于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汉官仪》载:护羌校尉“武帝置,秩比二千石,持节,已护西羌。”其职责是“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持节代表中央出守地方,直属于中央政府,那么必然与中央政府联系密切,公文往来频繁。简文中就有反映:
简1.七月壬午,御史大夫下吏护羌校尉将军…… (Ⅱ90DXT0314②:179)
简2.阜布纬书两封,大司徒□□□诣府□□ 入西蒲封□□□□□□□□□□诣府 入西蒲封□□□□□□□□□□诣府 板檄一,护羌从事掾□□□□□ 板檄一,护羌从事掾□□□□□ (Ⅱ90DXT0114②:275) (Ⅱ90DXT0114②:275)
简3. 于掾府,一诣御史,一诣左冯翊府,一诣武威府,一诣京兆尹府,一诣安定,一诣赵掾府,一诣金城,一诣南河尹府,一诣…… 于掾府,一诣御史,一诣左冯翊府,一诣武威府,一诣京兆尹府,一诣安定,一诣赵掾府,一诣金城,一诣南河尹府,一诣…… □□一诣护羌,一诣渊泉,一诣宜禾督(蓬杰下),一诣宜禾酒泉督(蓬杰下),一诣定汉尉。(VI91DXF13C①:25) □□一诣护羌,一诣渊泉,一诣宜禾督(蓬杰下),一诣宜禾酒泉督(蓬杰下),一诣定汉尉。(VI91DXF13C①:25)
简1是记载御史大夫下达给护羌校尉的朝廷公文,简2是一份西达邮书的记录,与护羌校尉有关,简3是一封邮书简,文中的“护羌”,可能为“护羌校尉”的省称,护篷、尉均为边郡基层军事机构,此简反映的内容与军情有关,总之,悬泉汉简中的这三条简文,反映了西汉宣帝以后至东汉年间护羌校尉的存在和活动情况。
2.护羌使者
护羌使者一职史书无记载,悬泉汉简中却有记载,简文如下:
简4: 护羌使者,行期有日,傅舍不就 护羌使者,行期有日,傅舍不就 (Ⅱ90DXT0214①:72) (Ⅱ90DXT0214①:72)
简5:护羌使者方行部,有以马尾谴,长必坐论。过广至,传马见四匹,皆瘦。问□吏,言十五匹送使者,大守用十匹。(Ⅱ90DXT0215③:83)
简6:出护羌使者传车一乘,黄铜五羡一具,伏兔两头,柅两头,亶带二币,(革因)(革伏)、韦书簿各一。故(早上一丿)复盖蒙,完;蚤具毋金承。
根据简文看,护羌使者设有幕府,开府治事,并可巡行各部,似应有相当秩级,不是护羌校尉的属官。
3.主羌史
两汉地方政府对于羌人的管理较为重视,敦煌郡由于内外有诸种羌分布就设有主羌使一职。如简:
简7: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疆、守部侯修仁行丞事,告督邮吏众√欣、主羌史江曾、主水史众迁,谓县:闻往者府掾、史、书佐往来,□案事公与宾客所知善饮酒传舍请寄长丞食货数。(Ⅱ90DXT0216②:246)。
简8:七月一日庚申,主羌史李卿过,西。从吏一人,用米六升,肉一斤。(Ⅱ90DXT0115②:5)
从简文看,“主羌史”一职,当为敦煌太守的属官,简文“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疆、守部侯修仁行丞事,告督邮吏众√欣、主羌史江曾、主水史众迁,……”表明,敦煌地处西陲,境内羌人由太守府专设主羌史一职管理,这种制度异于内地的郡县制度。
4.护羌从事
《续汉书·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本注:‘主护南单于。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乌桓校尉所置亦然’”。简文中亦有反映:
简9:入东合檄一,护羌从事马掾印,诣从事府掾。建始□□□□(□/)(Ⅱ90DXT0214②:535)
简10:入□□□□具币;裴一,完;履□一,新;(革因)(革伏)簿出,完;雨衣一,完;帘一,完缇。绥和元年五月乙亥,县全置啬夫庆受敦煌□佐并,送护羌从事。 (Ⅱ90DXT0111①:303)
简11:□□□□护羌从事治所。(Ⅱ90DXT0215①:22)
史籍结合简牍材料,我们可知,护羌从事应为护羌校尉的属吏。
以上四种官吏是两汉时期常设的较为重要的职位,中原王朝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不同的官吏来加强对羌人的管理。护羌校尉主要在行政军事上对羌人进行管理,而护羌使者主要是对凉州管理羌人及其他的大小官吏进行监督,两者的分工与合作保证了羌人正常的社会秩序,除此此外,中原王朝还在个别临羌边郡设置了主羌史,这对羌人的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羌人反叛及汉朝的对策
(一)两汉时期羌人的反叛
西汉时期,汉与羌人的矛盾虽不像东汉那样尖锐,但由于边吏的侵夺和执驭不当,羌人也多次反叛,悬泉汉简中保留了宣帝至王莽时期羌人起事的零星记载:
简12:琅何羌□君疆藏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二乘传。十一月辛未皆罢。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Ⅰ90DXT0210③:6)
简13:讨羌人入徼盗发数移。(Ⅱ90DXT0215④:7)
简14:·闻羌人买穀民间,持出塞甚众。长史废不为意,未有坐者,务禁防之。(Ⅱ90DXT0216②:39)
简15:一封长史私印,诣广校候,趣令言羌人反状。 □在广至。闰月庚子昏时,受遮要御杨武行东 □在广至。闰月庚子昏时,受遮要御杨武行东 江趣令言羌反状。博望候言:羌王唐调言檄发兵,在澹水上。(Ⅱ90DXT0216②:80) 江趣令言羌反状。博望候言:羌王唐调言檄发兵,在澹水上。(Ⅱ90DXT0216②:80)
简16:博望雕秩候部见羌虏为盗 。(Ⅲ92DXT0809④:35) 。(Ⅲ92DXT0809④:35)
简17: □□□普张崇钦言:羌人黠,连殴击背,若首发。(Ⅱ90DXT0113①:39) □□□普张崇钦言:羌人黠,连殴击背,若首发。(Ⅱ90DXT0113①:39)
简18:益广广校候部见羌虏,疑为渊泉南,籍端□□□ (92DXH11:1) (92DXH11:1)
简12、13两枚反映的是宣帝神爵间西羌反叛的情况,简14、15反映的是元帝永光建昭年间陇西羌人反叛时河西羌人与之呼应的记录。简16、17、18反映的是王莽时期西平羌人起义时河西羌人的动向。
这一时期,羌人叛服无常,羌汉关系呈现出许多反复性。中原王朝为了解决归附羌人的稳定问题,对羌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敦煌悬泉汉简为此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佐证。
(二)汉朝对羌族的管理措施
1.优待归附羌族首领
中原王朝为了有效地管理归附诸羌,对其给予一定的赏赐和优待,对诸种羌豪仍然承认其统治地位,并封以“王”或“侯”的称号。如对羌支豪酋封爵受印,如简:
简19:敦煌太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羌侯人十二 (Ⅰ90DXT0210③: 6)
简20:出粟一石,马五匹,送羌王索卢掾东…… (Ⅱ90DXT0113①:4)
简21:出粟一斗八斤,以食守属萧嘉西罕侯封调,积六食,食三升。(Ⅱ90DXT0111①:174)
简22:出钱六十买肉十斤﹦六钱……以食羌豪两人。(Ⅱ90DXT0213②:106)
其中的“羌侯”、“羌王”、“ 西罕侯”等当为中原政府封授的归附羌豪,并且使其在本种支内拥有与原来几乎一样的地位和权力。这些都是中原政府对归附羌人所采取的优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平复了羌豪的“反叛”情绪,有利于羌族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对下层羌人则减免赋税,使其保留原有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等,这对于处于困境的羌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2.保障羌人的基本权益
在解决羌汉之间或羌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中原王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员本着“公平公正”的律法原则,对羌人的诉讼事务给予法律上的保障,这是中原王朝有效管理羌人的又一重要举措。
如简23—25:年八月中,徙居博望万年亭儌外归(艹取)谷,东与归何相近。去年九月中,驴掌子男芒封与归何弟封唐争言斗,封唐(Ⅱ90DXT0214①:124)以股刀刺伤芒封二所,驴掌与弟嘉良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卅匹、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匹、羊五十(Ⅱ90DXT0214①:26)九头,以畀归何。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儌外,在赦前不治,疑归何怨恚,诳言驴掌等谋反。羌人逐水草移徙(Ⅱ90DXT0114③:440)
儌通徼,徼即塞外,可见,羌人虽居塞外,但发生纠纷还要告当地官处理,说明他们已经归顺为郡县官府管理下的臣民。
三、归义羌人及汉朝的羁縻政策
武帝以后,羌人出没于祁连山南北。《汉书·西域传》载,天山南路诸国从东到西,都“南与婼羌接”,说明东自祁连山,西至昆仑山、帕米尔,南面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悬泉遗址中出土一个归义羌人的完整册子和散简数枚,反映了活动在河西的羌人部落。
简26—31:
归义聊臧耶茈种男子东怜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唐尧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蹄当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封芒
归义木盖良种羌男子落蹄
■右木盖良种五人
简32:
 归义(广聊)羌王使者男子初元五年七月 归义(广聊)羌王使者男子初元五年七月
 余输皆奉献诣仁行长史事 余输皆奉献诣仁行长史事
 乘传当舍传舍 乘传当舍传舍 (Ⅴ92DXT1210④:3) (Ⅴ92DXT1210④:3)
简33:出粟一石,马五匹。送羌王索庐掾东。元始五年十一月癸丑,县泉置佐马嘉付敦煌御任昌。(Ⅱ90DXT0113①:4)
简26—31为一完整的册子,是记载归义羌人的名籍。同层出土的纪年简主要是成帝河平以后的,说明该册为西汉晚期遗物。宣、元两朝,都有羌人反叛起义之事,后经朝廷的镇压安抚,陆续归顺。简文中反映的是宣、元之后羌汉和睦相处的情景。简32、33说明,各归义羌人由“王”统治,是汉朝对羌人实行羁縻政策的明证。以上所见,中原王朝对羌人的管理,运用拉拢怀柔的羁縻政策,在保证诸种羌豪原有地位和权力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一系列优待政策,从而保持了羌族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有效加强了对羌人的管理和统治。
总之,羌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深远的影响,它是一个与汉族长期族群互动的特殊群体,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对羌族的各种管理措施有效地推动了羌族的社会发展,加速了羌族的汉化进程。汉羌生产、生活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和谐与发展,汉羌文化的交融,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辉煌篇章。
第三节简牍反映的汉朝和匈奴的关系
匈奴,亦称胡,“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匈奴最高的统治者曰单于,其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候。”秦汉之际,冒顿单于并匈奴诸部,势力渐强,汉文帝初年,冒顿灭月氏、乌孙等二十六部,势力强盛,不断侵扰汉边。宣帝时匈奴因国内政乱而臣服于汉,成为汉之藩邦,王莽当政和建立新莽政权之后,匈奴摆脱了对中原王朝的臣服关系,又强盛一时。但为时不久,又因国内争权斗争而于东汉建武年间分为南北匈奴。北匈奴国势甩尾,在鲜卑、南匈奴和汉朝的侵犯下,逐步西迁,南匈奴降汉,居于汉北边诸郡,成为汉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后,匈奴的名称已不见于记载,它的名字被稽胡、部落稽、京西胡、山胡等所代替,到了唐代,匈奴已完全融合于汉族和其他民族。
匈奴与西汉政府的关系,史籍中的记载不尽详细,西北各地出土的简牍材料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这些史料对研究汉代与匈奴的关系的某些问题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一、郅支单于之死
关于郅支单于之死,《汉书》相关传纪中虽有描述,但未见呼韩邪单于参与的迹象。居延汉简为我们补充了一段重要的史料,为澄清呼韩邪单于在攻灭郅支事件上的作用和态度提供了有力证据。简文如下:
简1—12:
肩水候官令史,□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熹,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
十二月乙酉,广地候
□檄曰:甲申,候卒望见塞外东北
火四所,大如积薪,去塞百余里,臣熹愚
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
就屠与甸奴呼韩邪单于谋
夷狄贪而不仁,怀挟二心,请为
邵支为名,未知其变.
塞外诸节谷呼韩邪单于
往来技表是乐
小月氏仰美人
愚赣触讳忘言顿首。
简册中的“皇帝陛下”应为西汉元帝;“车骑将军”应为许嘉,小昆弥为乌孙王号,根据史籍以及出土简文,可以看出,公元前49年左右,乌就屠小昆弥被郅支击败,从此过上逃亡生活。到公元前36年之际,他见郅支实力与人气皆不及以往时,便下定决心将其殄灭。又恐一已之力不足以对抗郅支时,就去求助西汉和呼韩邪单于。此时呼韩邪已北归单于庭,在汉朝的帮助下,听乌就屠之谋,派兵增援乌孙。从简犊中可以推测出,呼韩邪单于,虽未亲自参加,但他态度鲜明的派重兵支援了该行动,并且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塞上烽火品约”所反映的预警制度
居延和敦煌地区发现的大量屯戍遗简为研究汉代烽火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汉代烽火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匈奴人,故从汉朝的烽火制度中亦能窥测出匈奴人进犯汉塞的情况。在汉代传递烽火信号的具体规定称之为“烽火品约”。其简文如下:
简13:匈人奴昼入殄北塞,举二烽,□□烽一、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离合苣火,毋绝至明。甲渠、三十井塞上和如品。《新简》EPF16:1
简14:匈人奴昼甲渠河北塞,举二烽,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二苣火,毋绝至明。殄北,三十井塞和如品。《新简》EPF16:2
简15:匈奴人昼入甲渠河南道上塞,举二烽、坞上大表一,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二苣火,毋绝至明。殄北、三十井塞上和如品。《新简》EPF16:3
简16:匈奴人昼入三十井降虏隧以东,举一烽,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一苣火,毋绝至明。甲渠、殄北塞上和如品。(F16:4)
简17:匈奴人昼入三十井候远隧以东,举一烽,燔一积薪,堠上烟一,夜入,燔一积薪,举堠上一苣火,毋绝至明。甲渠、殄北塞上和如品。《新简》EPF16:5
简18:匈奴人渡三十井县索关门外道上隧,天田失亡,举一烽,坞上大表一,燔二积薪;不失亡,毋燔薪,它如约。《新简》EPF16:6
简19:匈奴人入三十井诚□北隧县索关以内,举烽燔薪如故,三十井县索关诚□隧以南,举烽如故,毋燔薪。《新简》EPFI6:7
简20:匈奴人入殄北塞,举三烽,后复入甲渠部,累举旁□烽,后复入三十井以内部,累举堠上直上烽。《新简》EPFI6:8
简21:句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下燔薪者,旁亭可举烽、燔薪,以次和如品. 《新简》EPF16:9
简22:塞上亭隧见匈奴人在塞外,各举烽如品毋燔薪,其误,亟下烽灭火,候尉吏以檄驰言府。《新简》EPF16:10
简23:夜即闻匈奴人及马声,若日旦入时,见匈奴人在塞外,各举部烽,次亭晦不和。夜入,举一苣火毋绝,昼□、夜灭火。《新简》EPF16:11
简24:匈奴人入塞,候尉吏亟以檄言匈奴人入,烽火传都尉府、毋绝如品。《新简》EPF16:12
简25:匈奴人入塞,承塞中亭隧,举烽、燔薪□□□□烽火品约,官□□□举□□烽,毋燔薪。《新简》EPF16:13
简26:匈奴人即入塞,千骑以上,举烽,燔二积薪,其攻亭鄣坞壁田舍,举烽,燔三积薪。和如品。《新简》EP16:14
简27:县田官吏:令长丞尉见烽火起,亟令吏民□□□诚□北隧部界中,民田畜牧者□□……为令。《新简》EPF16:15
简28: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烽火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急疾。《新简》EPF16:16
简29:右塞上烽火品约。《新简》EPF16:17
《塞上烽火品约》规定了各种具体情况下应使用的不同联防示警信号,是汉代候望烽燧系统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条令,它规定了具体要求,协同性高,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从实践出发而制定的,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应当发出不同的信号,并采取其它措施,它可行性高,较前期的烽燧示警制度是一个较大的发展和进步。敦煌汉简中对此亦有反映。
二、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
王莽即位后,对匈奴采取了一系列不当政策,首先是更改匈奴名号。居延汉简中对此有相关的记载。
简30:诏书曰:除匈奴之号 EPT59:144
简文中的诏书,即皇帝制发的文书。这条简反映的是王莽下诏书除匈奴名号的文书。王莽篡位后,屡次更改名称,如曾下令“更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而天凤二年以后的简牍中确实有称匈奴为“恭奴”的记载。敦煌汉简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如:
简31:今共奴与鄯善不和,则中国之大利也。臣愚以为钦将兵北。《敦》66
简32:共奴遮逆虏《敦》68
简33:炬恭奴遮焉耆,殄灭逆虏《敦》98
以上这样的简牍,在敦煌汉简中共有八条,这说明王莽时期确有更“匈奴”为“恭奴”的事情,而且有时还写作“共奴”。
另外,王莽篡位后不仅更改匈奴、单于名号,而且还将匈奴分裂为十五部,分封十五位单于。史籍对此记载不详,而《额济纳汉简》中有一部册书记载了这一事件,这不仅证明王莽分封十五单于事情的真实性,而且还补充了史籍未见的细节。
简34:者之罪恶深臧发之。□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封稽候□子孙十五人皆为单手(于),右致庐尔候山(王),见在常安朝郎南为单手(于),郎将作士大夫南手子蔺苞副有书。 2000ES,9FS4:1-11
简35:校尉苞、□远度益寿塞徼,召余十四人当为单手(于)者,苞、□上书谨□□为单手(于)于者,其一人葆(保)塞,稽、朝候威妻子家属及与同群知之将业。
以上简牍详细记载了史籍未曾言及的细节,即“见在常安朝郎南为单手(于)”,自此可知,在具体的分封过程中,蔺苞、戴级在出塞前已经在京师率先分封了一位单于,因此,蔺苞、戴级二人出塞所要分封的就只有十四位单于了,简文“校尉苞、□远度益寿塞徼,召余十四人当为单手(于)者,苞、□上书谨□□为单手(于)于者”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简文还提供了具体的地点, 云中益寿塞,与史籍记载相吻合,
王莽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匈奴乌珠累单于,他便下令“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庐訾及左贤王乐将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是后,单于历告左右部都尉,诸边王入塞寇盗,大辈万余,中辈数千,少者数百,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收,缘边虚耗”。在这样的情形下,王莽也不甘示弱,“估府库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至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正是由于分封未果,这次王莽便下了更大的决心,欲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分封单于。王莽的这种做法,不仅失信于匈奴,更为严重的是失信于西域诸国,使西域与匈奴重新联合起来,共同劫掠边境,双方又陷入较长时期的战乱中。
三、东汉时期的汉匈关系
王莽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覆灭,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即位。自天凤三年西域之战后,西域“自此与汉朝绝”,这给匈奴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趁机重新占据西域,简牍中记载了匈奴对甲渠候官塞诸烽燧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简文如下:
简36—55:
甲渠郭守候君免冠叩头死罪,奉职数毋状,罪当
万死,叩头死罪死罪。十月廿八日胡虏犯塞略得吏
士,毋状,当伏重诛,靡为灰土,叩头死罪。
夏良叩头言:抹厶坐前毋恙,起居安平甚善。先日欲诣门
下,迫蓬起草草,不及诣门下,毋状,叩头叩头。得掾明时数
又壬午言虏燔烧孝隧,其日出时乘鄣□□张骏等候望
册余骑皆衣铠负鲁攻隧,又攻坏燔烧第十一隧以北
见塞外虏十余辈从西方来,入第十一隧天田屯止,虏四、五
攻坏燔烧第桼隧以南,尽昏□烟火不绝。又即日平旦
万岁部以南烟火不绝,虏或分布在块间,虏皆
第八随,攻候鄣,君与主官谭等格射各十余发,虏复从塞
百骑,亭但马百余匹、橐他四十五匹,皆备。贺倂塞来,南燔
乏卒,以鄣中□米糒给,孤单,卒有万分恐不能自守,唯
恐为虏所攻得.案:官中候以下□□。
力□,奈何。反遣吏去,而稀“,而从后逐之,时烽起至今,绝留
府。叩头死罪死罪,敢言之.
攻居隧不居隧,尽坏坞
将军衰贳货罪法,复令见日月,“叩头死罪死罪。
□白.起居毋它,叩头叩头一日厚踢,叩头叩头。谨言口。《新简》EPF16:36—55
从简文看,匈奴发动进攻的时间是这一年的十月廿八日,此次进攻从早晨开始,攻击的地点有甲渠候官塞的十一燧以北,第八燧、侯官鄣、万岁部以南,涵盖了整个甲渠塞,匈奴人横行甲渠塞,在广大的区域内,在较长的时间里,发动了多次的袭击。这次进攻,甲渠塞遭到严重的破坏,最后只有候官郭苦苦支撑,但是由于弹尽粮绝,军心已经跌落到极点,唯恐城门不保,沦为阶下囚。这些简牍生动的说明了东汉时期汉匈之间关系的不和平。
综上所述,不论从宏观上来讲,还是从微观上来讲,汉简中有丰富的匈奴史料,这些资料,或直接或间接记录匈奴的事情,内容相当珍贵而且丰富,如对这些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分析、考证,合理的使用将会解决很多匈奴史的难题,对匈奴史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简牍所反映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
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西汉时期,西域东北与匈奴相接,西北与乌孙相连;东汉时期,东北接匈奴、鲜卑,西北通匈奴、乌孙。两汉时期的城郭诸国,先有三十六,后又分为五十余。《汉书·匈奴传》载:“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后汉书·西域传》载:“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间(公元前6年至公元5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然而康居、大月氏、罽宾、乌弋不在其内,故《汉书·西域传》载:“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为五十余,……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种。”
一、简牍反映的汉朝与西域南道诸国的关系
简:二月甲午以食质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车使者二人扜阗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踈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绝
□斗六升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弥使者一人乙未食渠勒副使二人扜阗副使二人贵人三人拘弥副使一人贵人一人莎车副使一人贵人
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精绝副使一人—乙未以食踈勒副使者一人贵三人凡卅四人(Ⅱ90DXT0213③:122)
这条简文反映的是悬泉置接待西域使者的记录,简文内容反映的是郑吉都护西域前后,西域南道十国对汉朝朝贡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朝贡的国家之多,达到了十个,使节人数也有三十四人之众,身份也不尽相同,有质子、使者、副使、贵人等。说明这些国家相互之间关系比较融洽,并且同汉朝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二、简牍所反映的汉朝与乌孙的关系
乌孙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公元前2—1世纪兴起于我国的西北部,游牧于祁连、敦煌间(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乌孙起初势力较小,常遭相邻的月氏攻击,在得到匈奴的支持后,击败大月氏,占有了伊犁河流域,自立为国,为摆脱匈奴的控制,向西迁到今吉尔吉斯斯坦国境内的伊塞克湖。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至乌孙,最终促使乌孙与汉结亲,“匈奴闻其与汉通,怒欲击之。又汉使乌孙,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属不绝。乌孙于是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天子(按:汉武帝)问群臣,议许,曰:‘先必内聘,然后遣女。’乌孙以马千匹聘。汉元封(公元前110年至前105年)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乌孙在汉朝的帮助下,击退了匈奴的侵扰和进攻。
汉宣帝本始二年至三年(公元前72年至前71年),汉乌双方共同出兵二十万,大破匈奴,汉乌关系发生根本转变。自此之后,乌孙内附汉朝,从政治上正式归属西汉王朝,成为西汉王朝的一部分,受西域都护府管辖。东汉继续设西域都护府,乌孙仍由西域都护府领属。后来由于东汉势力衰退,加之乌孙地处西境,渐渐关系疏远。南北朝时,因受东部柔然的进攻,乌孙被迫再西迁葱岭山中,不久为柔然所亡。
1.汉简反映的汉乌交往
自汉遣公主与乌孙和亲直到西汉末年的一百多年间,汉与乌孙始终保持着友好往来,悬泉汉简中有大量反映汉与乌孙频繁往来的事实,而这一切,都与长罗侯常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直到王莽始建国五年(13年),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王莽设座小昆弥使坐大昆弥上,师友祭酒满昌因此力持异议也被罢官。随着王莽的积失恩信,乌孙才结束了同汉朝的往来。
悬泉汉简中有许多反映汉乌频繁往来的记录:
简1:出粟四斗八升,以食守属唐霸所送乌孙大昆弥、大月之所……(V92 DXT1712⑤:1)
简2:出粟二斗四升,以食乌孙大昆弥使者三人,人再食,食四升,西。(V1611③:118)
简3:□乌孙小昆弥使者知适等三人,人一食,食四升。(V1504②:4)
简4:出粟六升,以食守属高博送自来乌孙小昆弥使,再食,东。(I0110②:33)
简5:鸿嘉三年三月癸酉,遣守属单彭,送自来乌孙大昆弥副使者薄侯、左大将掾使敞单,皆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傅,凡二人。三月戊寅东。敦煌长史充国行大……六月,以次为驾,如律令。(II0241②:385)
简6:出粟十八石,骑马六十匹,乌孙客。都吏王卿所送。元延四年六月戊寅,县(悬)泉啬夫訢付敦煌尉史(衣中印左矛右)马。(II0114③:454)
简7:建平四年八月己卯,遣守属……大昆弥左大将……(IV0317③:1)
简8:出(革因)(绞左伏)各二,左部骑士高谊里,建平五年二月送昆弥使者……(I 0114①:70)
简9:出麦四斗,己。建平五年闰月□□,县(悬)泉啬夫付宜禾书佐王阳,给食傅马二匹,迎昆弥。(II 0114④:53)
简10:元始二年二月己亥,少傅左将军臣丰、右将军臣建,承制诏御史曰,候旦受送乌孙归义侯侍子,为驾一乘轺傅,得别驾载从者二人,御七十六。大……如……(I 0116 S 14)
以上列举的悬泉汉简的材料反映了西汉甘露年间以后,西汉与乌孙交往的史实,但我们结合史料,可以以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为界分两个阶段来认识西汉与乌孙的关系。张骞出使乌孙到西域都护的设立,在这一阶段,西汉、乌孙在特定的形势下,提出了和亲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西域和中原的稳定,推动了西汉和乌孙的交流,为乌孙的内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后,汉与乌孙的关系,变为隶属关系,西汉政府全面管理乌孙,稳定了西部边疆的局势,扩大了疆域,有利于汉朝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
2.汉乌友好往来的使者
在汉与乌孙的友好往来中,解忧公主、冯嫽、常惠等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在简牍中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1)解忧公主
解忧公主是汉高祖的弟弟刘交之孙楚王刘戌的孙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嫁到乌孙仅四、五年的细君公主因病去世,为继续与乌孙和亲,完成联西域、断匈奴右臂的计划,汉武帝将解忧公主嫁给乌孙昆莫军须靡。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生活了五十余年,共生三男两女,曾三任国母,在西域和乌孙之地位及威望不同一般,为加强汉族与西域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巩固汉朝在西域的统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悬泉汉简的简文中亦对此有记载:
简11: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驿)骑当富,县(悬)泉译(驿)骑朱定付万年译(驿)骑。(II 0113③:65)
简12:甘露三年十月辛亥,丞相属王彭,护乌孙公主及将军、贵人、从者,道上傅马车为驾二封轺傅,□请部。御史大夫万年下谓(渭)成(城),以次为驾,当舍傅舍,如律令。 (V1412③:100)
(2)长罗侯
长罗侯,名常惠,太原人,早年与苏武出使匈奴被拘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才回。汉“嘉其勤劳,拜为光禄大夫。”因“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后转典属国、右将军。本始三年(前71年),护乌孙兵与汉兵五道击匈奴,因功封长罗侯。先后六至乌孙、一伐龟兹,代表汉朝政府统领乌孙部队,协助册立“昆弥”,处理乌孙与各部首领之间的纠纷,对汉代乌孙社会经济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悬泉汉简的发现,使人们对长罗侯有了新的认识。
简13—30:
·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县掾延年过。
入羊五,其二(上四下幸),三大羊,以过长罗侯军长吏具。
入鞠三石,受县。
出鞠三石,以治酒之酿。
入鱼十枚,受县。
入豉一石五斗,受县。
今豉三斗。
出鸡十双一枚,以过长罗侯军长史二人,军候丞八人、司马丞二人,凡十二人。其九人再食,三人一食。
出牛肉百八十斤,以过长罗侯军长史廿人、(广内干)候五十人,凡七十二人。
出鱼十枚,以过长罗侯军长史具。
出粟四斗,以付都田佐宣,以治疗庚。
出豉一石二斗,以和酱食施刑士。
入酒二石,受县。
出酒十八石,以过军吏廿,(广内干)候五人,凡七十人。
·凡酒廿,其二石受县,十八石受县,十八石置所自治酒。
凡出酒廿石。
出米廿八石八斗,以付亭长奉德、都田佐宣以食施刑士三百人。
·凡出米册八石。(I90DXT0112:③61-78)
悬泉置出土的《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为悬泉置接待长罗侯军吏的一份账单,此简虽对过往人数、开销招待情况记之甚详,但对长罗侯此次的使命,我们只有结合史籍及其他简牍分析方可知,此简反映的是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送公主出塞前,长罗侯常惠奉命使乌孙迎聘礼路过悬泉置时,悬泉置招待常惠属吏的开支账目。另外还有许多反映长罗侯常惠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可补史籍之不足。比如:
简31:神爵二年正月丁未朔己酉,县泉置啬夫弘敢言之:遣佐长富将传迎长罗侯,敦煌稟小石九石九斗,薄入十月,今敦煌音言不薄入,谨问佐长富稟小石九石六斗,今移券致敦煌□□。(I91DXT0309③:215)
简32: 县泉置度侍少主长罗侯用吏。(II 90DXT0214②:298) 县泉置度侍少主长罗侯用吏。(II 90DXT0214②:298)
简33: 鱼离置为长罗侯军吏士,置傅一封轺□ 鱼离置为长罗侯军吏士,置傅一封轺□ 。(I91DXT0309③:309) 。(I91DXT0309③:309)
(3)冯嫽
解忧公主的侍女,后为乌孙右大将的妻子,她头脑灵活,足智多谋,能“史书”,“内习汉事,外习西域诸国事”,曾“尝持汉节为(解忧)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邦诸国,西域人敬信之”,都尊称她为冯夫人。冯嫽长年活动于西域各国,对于沟通西域人民与乌孙和汉朝的友好联系,繁荣乌孙经济文化、抗拒匈奴侵略,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史书对她记载甚少,悬泉汉简中相关文献的发现,成为我们了解冯嫽及其汉朝与西域关系的珍贵史料。
简34: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啬夫禹移县(悬)泉置,遣佐光持傅马十匹,为冯夫人柱,廪(禾廣)麦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今写券墨移书到,受薄(簿)入,三月报,毋令缪(谬),如律令。(II 0115③:96)
简35: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涫)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傅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个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舆世等。敢言之。(V1311④:82)
三、简牍所反映的汉朝与于阗的关系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是西域南道中国势最强的国家之一。因位居丝路贸易的重要据点而繁荣一时,且为西方贸易商旅的集散地,东西文化的要冲地带,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汉书·于阗国传》载:“于阗国,王治西城,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君、东西城长、译长各一人。东北至都护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河原出焉。多玉石。”于阗的地域较广,南至昆仑山,北至塔里木盆地中部,东于田,西皮山,于阗河从中流过。
敦煌悬泉置汉简中一枚记载西汉元帝永光五年汉朝送于阗诸国来客的史料,对研究西域于阗史有着重要价值,说明永光年间,西汉与于阗之间已友好往来,且在发生纠纷时,有完善的处理纠纷的措施。今将简文列之如下:
永光五年七月癸卯朔丁巳,使送于阗王诸国客,卫司马参、副卫侯临,移敦煌太守,一过不足以考功,致县略察长吏居官治状,侍客尤辨者。渉头、渊泉尽治所。(Ⅱ0216②:54)
从此简来看,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西汉元帝时于阗国曾派出使者到汉朝。由于敦煌太守、长吏、使客待于阗客人不周,故朝廷责成卫司马参和副卫侯临彻查此事。永光五年汉朝送于阗王诸国客之事,史书未见记载。考虑原因有:一,元帝初元元年“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永光年间又连年饥馑,永光二年“夏六月,诏曰:‘间者连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劳于耕耘,又亡成功,困于饥馑,亡以相救。朕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伤焉。其赦天下。’”二,羌变。从永光元年“秋七月,西羌反”开始,羌变持续不断,导致“边竟不安,师旅在外,赋敛转输,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三,元帝永光三年冬,地震。四,“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可见,元帝永光年间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之际,根本无暇西顾,直到建昭三年才见甘延寿、陈汤伐西域之事。但这枚简记载了即使在汉朝困难重重之时于阗国仍遣使来朝,由此可见汉朝与于阗的交往甚密,并未受到羌乱等的影响。
因此,简牍记载的永光五年西汉与西域于阗国之间的关系往来的史实,填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四、简牍所反映的汉朝与楼兰(鄯善)的关系
许慎《说文解字》云:“鄯善,西胡国也,从邑善,善亦声。”《汉书·鄯善国》载:“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万四千一百,胜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西北去都护治所(今甘肃张掖)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可见鄯善即楼兰。楼兰作为政治实体从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史记·匈奴列传》引述匈奴冒顿单于致汉文帝的一封书信,信中匈奴威胁汉文帝称破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同书《大宛列传》记载“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即今之罗布泊。楼兰国位于罗布泊西部和南部地区。
两汉时期,鄯善因处于西域交通的中枢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匈奴与两汉争夺的焦点。随着匈奴、两汉势力的消长,楼兰(鄯善)与汉朝的关系出现过不同的形态:一是在汉朝帮助下建立亲汉政权,与汉朝形成合作关系,楼兰改鄯善,就是亲汉政权建立的标志。傅介子斩杀楼兰王,开启了鄯善与汉朝关系的新篇章,此后,两国进入了贡使往来和经济文化友好交流的阶段;二是在政治上接受汉朝的领属,成为汉王朝管理下的地方政权;三是同汉朝和亲,从血缘上巩固两者的依附关系。这些过程和形态,除了传世文献外,出土简牍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真实性。
1.使者往来
简1: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Ⅱ90DXT0115②:47)
简文中的“楼兰王以下”当包括了楼兰王。“当东”即东行,可能是入汉朝拜天子。全文大意应为楼兰王及其所属260人要东来汉地,敦煌太守或效谷县廷事先给悬泉置下达的接待通知。据载:“元凤四年,傅介子斩楼兰王尝归,悬首北阙下,立尉屠耆为王,改国号为鄯善”。此简所记当是元凤四年以前的汉代与楼兰的关系。
另外,还有简牍反映了楼兰改国名后与汉朝的友好往来的记录。
简2:以食守属孟敞送自来都善王副使者卢口等再食西(I 90DXT0116②:15)
内容大意是:守属孟敞送都善王副使卢某等返回都善,路过悬泉置,悬泉置出粟若干,供膳两次,西行而去。都善王副使属于“自来”而非朝廷正式邀请。同前简一样,是一份招待过往使节以及开支情况的登记文件。时代当在宣帝以后。因为该探方所出,从宣帝五凤年间到王莽居摄时期各个年代的纪年简都有。这条简反映了鄯善同汉代的民族交往以及贡使往来。
2.宫女和亲
元凤四年,傅介子斩楼兰王,更其国名为鄯善,立曾在汉为质子的尉屠耆为王。汉朝“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尉屠耆不仅受到汉文化的熏陶,而且带着汉朝的宫女回国,鄯善和汉朝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简3:出粟一斗六升以食鄯善王 赐妻使者□□□□二人再食四升西(Ⅰ90DXT0116②:41)
这条简文的大意为:出粟一斗六升。以食鄯善王、王赐妻使者□□、□□、二人,人再食,食四升,西。鄯善王和王妻所派使者二人,路过悬泉置用饭两次,每饭每人四升,用粟一斗六升。由东向西,从汉地回国。这是一份典型的接待记录,内容包括被接待者的身份、姓名、人数、用饭次数、接待标准、开支情况以及客人去向。这枚简牍虽然文字简单,但说明来汉朝朝贡的,不仅有国王的使者,而且有王妻的使者。这个王妻,很可能就是汉朝的宫女,这枚简牍生动地再现了汉朝和鄯善以宫女和亲的历史事实。
3.羁縻政策,
神爵二年,汉设西域都护府管理西域。鄯善、焉耆、危须三国,同时与汉朝保持了经常的使节往来和朝贡关系,一方面接受西域都护的节制,一方面又作为特殊地区常来京师朝天子,保持着政治上的羁縻关系和丝绸之路的畅通。
简4: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大守 属汉刚送客移过所县置自来焉耆危须鄯善王副使匹牛 车七两即日发敦煌檄到豫自办给法所当得都尉以下逢迎客县界相(V92DXT1310③:162)
这是一份敦煌太守派员迎送西域使者的过所抄件。永光元年二月癸亥,即二月十六日,公元前43年4月3日。三国使者及马若干匹,牛车七辆,从敦煌出发,沿途所需自行采买,都尉以下要在县界迎接。从行文看,三国使者由西向东,刚刚入境,前往京师途中。
简5:
鸿嘉三年正月壬辰遣守属田忠送
敦煌长史充国行大守事垂晏谓敦煌
自来鄯善王副使姑丽山王副使鸟不(月缘右)奉献诣
为驾当舍传舍郡邸如律令
行在所为驾一乘传六月辛酉西(II 90DXT0214②:78)
这是一封为西域使者提供食宿乘车的传信,类同于后世的官方介绍信。但不是原件,只是抄录了主要内容。鸿嘉三年正月甲戌朔,壬辰为十九日,公元前18年2月20日。此时,都善王副使姑丽、山王副使鸟不(月缘右)到京师朝贡回国,朝廷派守属田忠护送,驾一乘传,即四匹马拉的车。敦煌太守不在署,而以长史充国和垂晏的名义签发文件,要求境内传舍和郡邸,按规定安排食宿。
综上所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既有使者的友好往来,也有和亲以加强两国的关系,还有羁縻政策的影响。这充分说明了汉朝和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友好关系。鄯善与汉朝的关系史,反映了中国两汉时期对西域的统治和经营,从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时起,西域已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五节汉简反映的汉朝与中亚诸国的关系
一、汉朝和康居的关系
西汉时期,康居国乃西域大国,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未归之前就已遣使汉廷,是最早朝汉的西域邦国。它不仅在中亚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且因其处于丝路要冲地带,故在中西交通史上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据研究,康居地处今锡尔河流域及其以北广大草原地带。《史记·张骞列传》载,康居乃“行国”,“控弦者八九万人”,“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可见此时康居势力相对弱小,至公元一二史记,据《汉书·西域列传》载,“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从户口及兵力数量看其实力在当时已仅次于乌孙,成为西域第二大强国。然而,因史料有限,对于康居与汉代的关系,认识依然非常模糊。
近年来悬泉汉简和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中搜集到近二十条关于康居的记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康居和汉朝在政治上的朝贡和侍子、经济上“贾市为好”和其他商贸往来、文化上碰撞、交流、影响的关系,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康居国的基本情况及与西汉王朝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材料。
1.宣帝时期的汉康关系
与康居有关的纪年汉简中,明确为宣帝时期的有3枚,简文如下:
简1:甘露二年正月庚戍,敦煌太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 罢,军侯成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 罢,军侯成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如玉门关,已阁□ 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如玉门关,已阁□ (Ⅱ90DXT0213㈣:6A) (Ⅱ90DXT0213㈣:6A)
简2:黄龙元年六月壬申,使臣宏,给事中,侍谒者臣荣□□制诏侍御史自送康居诸国客。卫侯义与□□□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Ⅱ90DXTO114:377)
简3:传送康居诸国客,卫侯臣宏、副□、池阳令臣忠,上书一封。黄龙元年 (Ⅱ90DXT0214㈣:109 ) (Ⅱ90DXT0214㈣:109 )
悬泉汉简这3枚汉简的出土,证明早在宣帝甘露二年和黄龙元年,康居与汉朝已有交往。这与我们从史籍中得知的情况完全不同。其中,第一简明确记载甘露二年正月康居王遣使贡献,敦煌郡给酒泉郡发公文,通报此事,要其做好接待工作。这条简说明在宣帝甘露年间,康居和汉朝就有了贡使关系。而《汉书·西域传》载“至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的说法只对了一半;第二、第三简则记载黄龙元年汉政府送康居诸国客回国的情况。总之,这一时期因西域都护设立和呼韩邪单于使汉等因素,康居与汉朝有通使往来。
2.元帝时期的汉康关系
这批汉简中,明确为元帝时期的有7枚,即《康居王使者册》,记载了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遣使贡献的情况,简文如下:
简4—10:康居王使者杨佰刀、副扁阗,苏薤王使者姑墨、副沙囷,即贵人为匿等,皆叩头自言:前数为王奉献橐佗入敦煌][关,县次购食至酒泉昆归官,太守与杨佰刀等杂平直肥瘦。今杨佰刀等复为王奉献橐佗入关,行直不得][食至酒泉,酒泉太守独与小吏直畜,杨佰刀等不得见所献橐佗。姑墨为王献白牡橐佗一匹、牝二匹,以为黄。及杨佰刀][等献橐佗皆肥,以为瘦。不如实,冤。
永光五年六月癸酉朔癸酉,使主客、谏大夫谓侍郎:当移敦煌太守,书到验问言状。事当奏闻,毋留,如律令。
七月庚申,敦煌太守弘、长史章、守部候脩仁行丞事,谓县:写移书到,具移康居、苏薤王使者杨佰刀等献橐佗食用谷数,会月廿五日,如律令。 掾登、属建、书佐政光。 掾登、属建、书佐政光。
七月壬戌,效谷守长合宗、守丞、敦煌左尉忠谓置:写移书到,具写传马止不食谷,诏书报,会月廿三日,如律令。 掾宗、啬夫辅。(Ⅱ90DXT0216④: 877-883) 掾宗、啬夫辅。(Ⅱ90DXT0216④: 877-883)
全文主要讲述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的情况。简文中的苏薤王是康居五小王之一,从简文看,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可以直接和汉朝使节往来,说明早在两千年前,今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就已经和汉王朝有了友好往来。《康居王使者册》生动的见证了这一事件。
3.成帝时期的汉康关系
这批汉简中明确为成帝时期的只有1枚,内容为送康居王质子的文书。简文如下:
简11:阳朔四年四月庚寅朔庚寅……送康居王质子乘(传)……如律令。(Ⅱ90DXT0215: 17)
据简文可知,阳朔四年(前21年)康居王曾向汉遣送质子。据史料记载,汉成帝时,康居曾两次遣子侍汉,悬泉汉简反映的应是第二次遣子侍汉的情况,而第一次遣子侍汉的时间在成帝继位之初。敦煌博物馆在玉门关附近掘得的数百枚汉简,其中就有关于康居与汉朝在此之后使节往来的记录。如:
简12:阳朔二年四月辛丑朔甲子,京兆尹信,丞义下左将军,使送康居校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四月丙寅,左将军丹下大鸿胪、敦煌太守,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诏书。
这是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朝廷下发文件的记录。可以看出,康居和汉朝的关系在消灭北匈奴以后一段时间又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至汉末,“终羁縻而未绝”,在西汉后期的一个世纪里,基本上保持了使节往来和朝贡羁縻的外交关系。
二、汉朝与大月氏的关系
月氏原来是游牧在河西的一个游牧民族,《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汉书·西域传》载:“大夏本无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稟汉使者”。《李广利传》转载汉天子大宛战役后封李广利为海西侯的诏书中叶说到:“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故雁门守攘”这都说明,月氏虽远徙大夏,但与汉朝始终保持着使节往来。
关于汉代和月氏的往来,过去的文献缺乏记载,悬泉汉简中有关大月氏的简文,都是西汉宣帝以后至西汉末年之物,宣、元时期的居多,这些简作为地下出土的第一手记录,对了解当时的汉代和大月氏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简1: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大司马车骑将军臣□承制诏请□:大月氏、乌孙长□凡□□□富候丞或与斥候利邦国、候君、候国、假长□□□中乐安世归义□□□□□□□□□。为驾二封轺传,十人共□,二人共戴。御史大夫□下扶凤□,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十月□。(Ⅰ91DXT0309③:59)
这条简有明确的纪年,即神爵二年(公元60年),是目前为止汉与大月氏往来的最早的实物见证,简文中的“大司马车骑将军”,结合史料分析,应该是龙(各頁)侯韩增,
另外,还有朝廷派人送大月氏使者的记载。
简2: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诏御史曰□都内令霸、副候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与(广干)候张寿、候尊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戴。御属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风□,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简3:客大月氏、大宛、踈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扞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Ⅰ91DXT0309③:97)
简4: 校尉丞义,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从者一人,凡二人,人一食,食三升。(Ⅴ92DXT1311③:129) 校尉丞义,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从者一人,凡二人,人一食,食三升。(Ⅴ92DXT1311③:129)
总之,汉代和大月氏的关系,史书虽有记载,但多不详细,这些汉简中记载的汉代和大月氏的关系,填补了汉代和大月氏关系的许多空白,对了解他们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汉朝与罽宾、乌弋山离等国的关系
1.汉朝与罽宾的关系
罽宾,大致在今天的克什米尔,《汉书·西域传》载:“户口胜兵多,大国也。……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侯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成帝时不再派遣使者报送其使,而罽宾使者“数年而一至云”,悬泉简关于罽宾的简牍有两条,这两条简对研究汉代与罽宾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简1: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竝√弃贺所送莎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Ⅱ90DXT0113②:24)
简2: 以给都吏董卿所送罽宾使者□ 以给都吏董卿所送罽宾使者□ (Ⅱ90DXT0213②:37) (Ⅱ90DXT0213②:37)
简1所记董竝和弃贺所送的西域使者有莎车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特别是最后说到的“祭越”应该是西域国家的名字,史籍未见记载,为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简2无法判断,只能看到“以给都吏董卿所送罽宾使者”字样。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掘材料的增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必将会有所突破。
2.汉朝与乌弋山离的关系
乌弋山离国,是塞人建立的国家。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的记载:“王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大国也。东北至都护治所六十日行”。“东与罽宾、北与扑桃、西与犁靬、条支接。……绝远,汉使希至。”因此,我们知道,乌弋山离国在罽宾西北、安息东南、朴挑之南、犁靬和条支之东。并且由于远离汉朝,故而“汉使希至”。悬泉汉简中有一条关于乌弋山离使者路过悬泉置的记载,简文如下:
 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 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
 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 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
 □以食使者弋君(Ⅱ90DXT0214S:55) □以食使者弋君(Ⅱ90DXT0214S:55)
悬泉汉简中关于乌弋山离国的记载虽有一条,却弥足珍贵,这条简文说明乌弋山离国虽和汉朝相隔甚远,但还是有贡使往来。另外,简文中的“折垣王”不见史籍记载,应该是和前述“祭越”一样,是一个以前不见史籍记载的西域国家的国王。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孙言诚《秦汉的邦属和蜀国》,《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同上。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史记》卷5《秦本纪》。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史记》卷10《孝文帝本纪》
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7册下。
《史记·匈奴列传》
大庭修著、林剑明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肚,1991年版,第253页。
《后汉书》卷28《桓谭列传》。
《汉书》卷94下《匈奴列传》。
《汉书·西域传》
《汉书·西域传》卷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