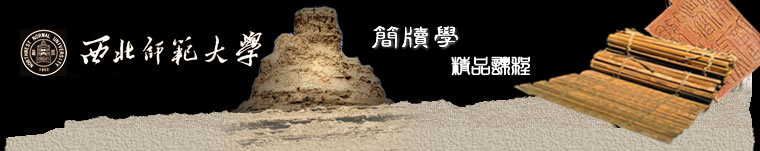政治制度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与之相关的各项制度,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文书制度、职官制度、爵位制度、监察制度和军事制度等。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各种制度不断改革、发展,是今天历史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
文献史料中有不少政治制度史内容。“二十四史”大都有专门的《百官志》、《职官志》,对具体时代的政治、职官制度予以记载。《通典》、《文献通考》、《秦会要》等典制、会要体史书中相当大的篇幅也是对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记录和考证。
丰富的文献史料促成了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繁荣局面,但传世文献的局限也相当明显:第一,其大部分都是二手资料,即使有个别撰述者与记述时代接近,也要受到具体地域和具体时间的限制;第二,很多政治制度相当复杂,真正的当局者未必能“清”,不同记述者对同一制度常有歧义的看法;第三,史料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舛误;第四,记述者对基层制度的一般性忽视。这种史料局限,最终导致了传统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分歧多、基层政治制度研究薄弱、常以点代面等问题的出现。
20世纪以来,作为原始行政记录的大批简牍材料的出土,无疑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尤其是秦汉魏晋政治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它们不但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更珍贵的是包含了在许多传世文献中记载甚为简单的基层行政资料。而不同时间点和不同地点相近内容简牍的出土为我们探索具体制度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演变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可以说,简牍材料的出土,促成了古代政治制度史上许多问题的解决,加深了我们对一些具体制度的认识,拓宽了研究领域,极大推动了秦汉魏晋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1914年,王国维先生根据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晋文书而著的《流沙坠简·屯戍丛残考释》中对政治制度研究已给予高度重视。《屯戍丛残考释》计有簿书、烽燧、戍役、廪给、器物、杂事六部分内容,对汉代的边郡组织系统、烽燧制度、军事制度有较多涉及,开辟了中国学者以简牍材料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先河。20世纪30年代居延汉简出土后,学术界更加重视简牍材料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制度史研究的价值,产生了许多高质量论著。由于居延、敦煌汉简的特殊性质,当时的制度史研究仍集中在以烽燧、亭鄣、屯田、边塞为主要内容的边郡屯戍制度上。但也有一些以汉简材料研究地方行政制度、乡亭制度、职官制度、仕进俸禄制度、法律制度、文书行政的尝试,取得了不小成果。建国后,以居延、敦煌汉简为主要材料进行前述课题的研究仍是海峡两岸秦汉制度史研究的主流,陈直、陈梦家、劳榦、严耕望等学者尤其取得了丰硕成果。70年代后,随着以甲渠候官、肩水金关、马圈湾为代表的新一批居延、敦煌简的出土,更多中青年学者投入到简牍研究中来,边塞制度、屯戍制度、文书行政等传统课题仍受关注,方兴未艾。
但建国后,尤其是近三四十年以来,出土简牍无论是在时代、地域,还是涵盖内容上都有了不小突破,大大拓宽了依靠简牍材料进行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领域。从时代上说,20世纪70年代前用以进行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要是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前期的简牍,研究成果无疑主要是汉制,而今天则可以通过包山楚简、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等材料研究战国、秦代、三国的制度。即使同是汉制,今天可以通过张家山汉简研究汉初制度,可以通过甘谷汉简、长沙东牌楼汉简研究东汉后期的制度,时代范围也大大拓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简牍材料涵盖了战国中后期、秦、汉初、西汉中后期、东汉、三国各个时间段,基本不存在大的缺环,这就为我们以长时段的视角探索战国秦汉魏晋时期各种具体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可能。从地域上说,70年代前用来进行政治制度研究的简牍材料主要出土于以居延、敦煌为中心的西北地区,这些材料主要反映了汉代西北边郡的政治实践,由其得出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全国,我们并不清楚。而今天可资利用的简牍材料的地域范围已大大拓宽,除了西北边郡材料继续出土外,湖北地区有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凤凰山汉简等重要简牍出土,湖南地区有里耶秦简、东牌楼汉简、走马楼吴简等材料出土,江苏地区有尹湾汉简出土,这些简牍分别反映了江南地区、中原地区的政治实践情况,将其与西北边郡简牍进行综合、对比研究,无疑会大大加深我们对秦汉政治制度史的认识。从内容上说,70年代前出土的简牍材料主要是关于边塞屯戍、防御的,虽然其中也会有涉及其它政治制度的内容,但材料往往较少且不集中,这就使得当时除了边塞屯戍制度以外的其它政治制度研究呈现出细节化、不系统、分歧大的特点。而今天简牍材料的内容则非常丰富,在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很多具体领域都有集中的简牍材料出土,为系统、准确的研究提供了良好史料基础。法律制度研究,有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的秦律、汉律支持,地方行政制度研究有尹湾汉简支持,宗室制度研究有甘谷汉简支持,军事制度研究有银雀山汉简、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支持等等,这些材料扩充了学界对这些具体制度的认识,推进了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顺利开展。
政治制度的内容很多,下面以职官和郡县制度的相关问题来说明简牍材料在推进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二、职官制度研究
职官的设置与管理,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世文献中关于秦汉时期的职官设置、管理情况,以《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的记载最为详备。但《汉书·百官公卿表》主要是以西汉末年的职官设置为据,《续汉书·百官志》是以东汉中后期的材料为据,对于职官设置的演变都着力不多。此外,传统文献比较重视中央官署的官吏设置,而对基层行政机构和下层官吏的情况往往忽视,也缺乏关于官吏除授、迁免等管理制度的系统记载,可以说存在一定缺陷。20世纪简牍材料的出土,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之处,推动了秦汉魏晋时期职官设置和管理制度的研究。
职官制度是简牍学研究最早关注的课题之一。王国维在《流沙坠简》中就曾对汉代边郡地区的一些职官如士吏、尉史等做过考证。此后,随着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简牍的不断出土,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简牍学的热点问题之一。与传统文献相比,简牍材料对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研究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推进了对行政机构职官设置体系的研究。如前所述,《汉书·百官公卿表》和《续汉书·百官志》中有对汉代中央行政机构职官设置体系的记载。但这些记载,概括性强,比较简单。居延、敦煌汉简出土后,以出土的诏令、公文等简牍材料,研究汉朝中央机构吏员设置体系的工作迅速开展,学界据此对上公、三公、九卿、中朝官、将军等中央职官体系予以重新梳理,取得了不小成绩。
利用汉简进行行政机构职官设置研究,更重要的成就体现在对地方行政机构和属吏设置体系的研究上。由于传统文献缺乏系统记载,长期以来我们对汉代地方行政系统的属吏设置体系一直都不甚了然。西北汉简出土后,许多学者以这些边郡材料为依据,开始了对此问题的探索,通过对各种官文书中出现的上下关系、统属关系分析排比,取得了很大突破。劳榦先生有对地方属佐的专门研究。陈直和日本学者滕枝晃曾对太守府、都尉府、属国都尉府、县廷的机构做过分析。陈梦家先生《汉简所见太守、都尉二府属吏》不仅对具体属吏予以考证,还将太守、都尉府机构分为阁下与诸曹,详细分析了郡府的机构划分情况。严耕望先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一书在大量使用汉简材料的基础上,从郡府组织、郡尉、郡国特种官署、县廷组织、乡官、郡县学官等方面对秦汉时期各级地方行政系统的机构和职官设置体系进行了总结,对各部门的长官、佐官、属吏系统进行了考察。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张家山汉简,尤其是尹湾汉简的公布,利用汉简从事地方行政机构职官设置的研究再次掀起高潮。尹湾6号墓的墓主曾在西汉晚期担任东海郡负责人事管理的郡功曹,其随葬品中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等关于郡府组织和属吏设置的原始记录。尤其是《东海郡属吏设置簿》,直接记录了东海郡在任掾史等属吏的设置情况。通过此簿,可以知道,西汉后期东海郡府计有掾史属吏93人,其中25人为正式在编的员吏,15人为君卿门下,13人“以故事置”,29人“请治所置”,还有赢员21人。
出土简牍不仅促进了汉代行政机构职官设置体系的研究,还推动了对其它时期职官设置的研究。关于秦的职官设置,传统文献记载很少,睡虎地秦简出土后开始有学者对此问题予以关注。今天依据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的材料,学界对以内史、廷尉、司空、工师为代表的秦中央职官系统和郡县乡里等地方职官系统已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其次,活跃了对秦汉魏晋时期一些具体职官的研究。有些职官,传世文献对其有较多记载,人们对它并不陌生,但作为原始材料的简牍的出土使人们在各个方面对其的传统认识有所突破,对其执掌、从属、设置情况有了更清晰的了解,近年来简牍学界对内史、都尉、督邮、卒史、戊己校尉等官职的研究与争论就是如此。以戊己校尉为例,由于《汉书》和《后汉书》对其的记载有分歧,史学界就其是一个职官,还是戊校尉和己校尉两个职官,曾展开过长期争论。西北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出土后,学界对其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今天有学者提出,“西汉自元帝初元元年至平帝元始年间之前,一直设戊、己二校尉;至少从平帝至新莽时期,合为戊己校尉一职。东汉明帝时始设戊、己二校尉;和帝及桓、灵二帝时期则设戊己校尉一职。” 这一结论与原来非此即彼的争论相比,明显有所进步。还有些职官如尉史、候长、燧长、都吏、啬夫等,在传统文献中出现较少,一直未引起学界的过多关注。简牍材料出土后发现了大量关于它们的材料,人们对其研究,不但加深了对具体职官的了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当时职官体系的认识,这方面的例子以对“啬夫”的研究为代表。西北汉简中有不少关于乡啬夫、库啬夫、关啬夫的记载,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出土后人们更是发现在秦及汉初的基层职官系统中,“啬夫”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啬夫分为有秩啬夫和斗食啬夫,地位不高,但其有具体负责的行政部门,与协助长官进行文书处理的史类属吏有很大差别。对“啬夫”的研究促使一些学者重新思考秦汉时期的整个基层职官体系,取得了一定成果。
最后,推进了对职官管理,如仕进、升迁、废免等制度的研究。传统史料对上述制度的系统记载较少,而出土简牍中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睡虎地秦简中有秦代“除吏律”和“置吏律”的简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汉初的“置吏律”、“史律”和“秩律”,尹湾汉简《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明确记载了当时东海郡所辖38个县、邑、侯国以及盐铁官的长吏的官职、籍贯、原任官职和迁除理由,这些材料在研究秦汉时期官吏迁除制度方面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三、郡县制度研究
郡县制,萌芽于春秋,发展于战国,秦始皇统一后彻底推行于全国,至两汉日渐完备,是秦汉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关于郡县制的情况,传统史籍有较多介绍,但由于时代久远、史料歧异,其中有些细节问题不甚明了也在所难免。20世纪以来秦汉简牍材料的出土,虽没有在大的方面改变我们对郡县制的认识,但在细节上确对传统认识有所补充,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解决也有所裨益。
出土简牍提供了许多传统文献中没有的郡县建置信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从廷尉李斯之议,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36郡。但由于《史记》未明确36郡是始皇二十六年初行郡县制时之郡数,还是有秦一代总郡数之追述,所以传统学界尤其是乾嘉学者对秦郡数目的争论非常激烈。20世纪40年代,谭其骧先生著《秦郡新考》,考证出“秦一代建郡之于史有征者四十六”,并审慎地指出46郡只是可以通过史料考证得出的,至于秦郡总共有多少并不能断言。此后,关于秦郡数目的争论逐渐平息下来。里耶秦简出土后,随着其资料的逐步公布,学界关于秦郡设置的探讨又渐趋热烈。里耶简中有洞庭郡、苍梧郡的设置,这两郡未见于文献记载。新郡名的出现一方面使我们对秦郡的设置有了更多认识,另一方面也促使一些学者对传统考据方法从方法论上重新思考,这无疑推动了此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县以人户多少可分为大、小两等,万户以上为大县,长官称县令,秩在六百石至千石;万户以下为小县,长官称县长,秩在三百石至五百石。然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则显示了一种与此不同的县的分等方法,补充了我们对汉初大小县分等的认识。《秩律》中的县分为五等,其长官秩次分别为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和三百石,其中三等以上的县占绝大多数,四五等的小县寥寥无几。众所周知,由于长期战乱,汉初人口剧减,万户以上的大县数量应该不多,《秩律》中绝大多数县长官秩次超过六百石,表明当时大小县的划分可能并非以六百石为界,而划分的标准也应不仅仅是根据人户的多少。
在秦汉郡制研究中,汉代河西四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武威郡)设置的先后顺序,也一直是学界聚讼不已的问题。居延、敦煌、悬泉置等地出土的纪年简中有不少内容直接与上述四郡有关,这就为讨论河西四郡的建置问题,提供了很多原始资料。今天学界在四郡设置问题的探讨上充分利用了这些出土简牍,虽说在具体时间点上大家还有争论,但在酒泉、张掖郡所设较早,敦煌郡稍后,武威郡晚至昭宣时期的大方向上已争议不大。
出土简牍所反映的郡府、县廷具体行政内容也充实了我们对秦汉时期郡、县职责分工及相互关系的认识。郡县制是以郡统县的制度,郡府是县廷的上级机构,这些都毋庸置疑。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郡府、县廷的职责重心不同,双方的关系也存在一定差异。从秦及汉初的法律及公文简中,可以发现当时地方上的日常行政管理一般都由县负责,县级行政机构员吏众多、组织复杂,而郡府属吏则较少,主要承担对县廷的监督及军事方面的职责。而通过尹湾汉简,则可以发现到西汉后期郡府的日常行政功能已大为加强,郡府机构日趋细密,数量有限的员吏不敷使用,出现了大量赢员性质的属吏,县廷在日常行政上受到郡府越来越多的干预。
出土简牍中关于政治制度史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上面介绍的以外,西北汉简中的“吏俸赋名籍”对于俸禄制度,尹湾汉简《集簿》对于上计制度,悬泉汉简对于邮驿制度,睡虎地秦简的《军爵律》和张家山汉简的《爵律》、《复律》、《户律》对于爵制的研究也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官文书制度研究
官文书是官府为处理政治、人事、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事务而形成的文书形式,可以包括公文、簿籍、录课、司法文书等。而官文书制度,则是关于这些官文书的制作、运行、管理方面的制度。
一、官文书的分类
睡虎地秦简《内史杂》载:“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明确规定下级向上级请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说明秦代的行政管理工作已是文书行政。到汉代,官文书更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所谓“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 官府内部进行管理,各官府之间相互沟通都要依靠文书的形式予以实现。官文书是了解秦汉政治生活的窗口,对秦汉政治史、制度史的研究有重大价值,但传统文献中对当时官文书制度的记载则颇为欠缺。《史记》、《汉书》等正史对基层官府间的行政文书极少涉及,在中央层面虽摘引了一些诏令及章奏文书,但多为片段,且大部分都经过史家的重新编排,能反映文书原貌的材料较少。蔡邕的《独断》、刘勰的《文心雕龙》对秦汉魏晋官文书制度有所叙述,保存了一些材料,价值很大,但此后的学者在材料及研究上都未能更进一步。可以说自蔡邕、刘勰后,直到20世纪简牍材料大量出土之前,这项研究基本是处于停顿状态的,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就是“文献不足徵”。
20世纪以来相关秦汉魏晋简牍材料的出土,大大改变了上述情况,结束了汉晋文书制度研究沉寂的局面。迄今中国出土的简牍中,文书类简牍占四分之三强。具体到官文书,数量也相当庞大,里耶、睡虎地秦简,居延、敦煌、悬泉置、张家山、东牌楼汉简,走马楼吴简,尼雅、楼兰汉晋简的内容可以说主要是官文书,这些简牍材料内容广泛、原始性强,极大丰富了学界对秦汉魏晋官文书制度的认识。
从内容来说,今天见到的简牍官文书大致可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官府往来文书、簿籍类文书、案录文书和司法律令文书。司法律令文书,本章第四节还要专门介绍,这里不再详谈。诏令文书是帝王的专用文书,主要包括命书、制书、诏书、策书和戒敕等。命书使用于秦始皇统一之前,统一后改称“制书”或“诏书”,1979年出土的青川木牍,就包含有秦武王关于更修《为田律》的命书。制书是秦汉皇室处理涉及制度法规等重大问题时所用的文书,一般以“制诏某官”作为文书的开始,发布对象主要是两千石以上的高官。居延、敦煌汉简中包含许多制书的片段,接受制书的有纳言、酒泉太守、御史等官。比较完整的制书,可以参考1977年玉门花海出土的七面菱形觚,其以“制诏皇大子”开始,是汉代某帝的遗诏。诏书是皇室最常用的命令文书,一般用于处理常规行政事务,其内容丰富,形式也较为多样。既有皇帝单方面下达的含“告某官”用语的命令文书,也有皇帝以“制曰可”、“已奏如书”或具体意见批复臣民上书而形成的文书。“告某官”的命令文书在形式上与制书区别不大,传统文献中较为多见。批复式诏书则主要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臣下的奏文,第二部分是皇帝的指示,这种诏书在居延、敦煌汉简中比较常见,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居延肩水金关简E﹒J﹒F16:1—16就是一则较为完整的丞相、御史大夫向皇帝恳请恤灾的批复式诏书。策书主要用于对诸侯王、三公的除封、免罢及诔谥等事项。戒敕又称戒书,是皇室对下级臣僚的训诫文书,往往有“诏敕某官”的用语。今天所见的出土简牍中,能明确判断为策书和戒敕的材料不多,而不完全符合策书、戒敕特点但性质又较近似的材料则有一些,关于这些材料的性质,要留待更多简牍材料出土后才能判定。
章奏文书是臣民向君主上奏、陈事所用的文书。根据使用环境及形式的不同,传统上将朝廷高官向皇帝上奏、请示的文书分为章、奏、表、议几类。由于简牍材料主要是基层行政文书,所以严格意义上的章、奏、表、议在出土简牍中并不多见。简牍中有大量地方官员,乃至普通百姓,向皇帝汇报战争情况、紧急事件的文书,这些文书无疑也属于章奏文书的范畴,根据内容可分为一般的上奏书和变事书。一般的上奏书是行政官员在正常情况下给皇帝汇报情况的文书,马圈湾所出新莽简中就有不少关于西域军情的上奏文书。变事书则是向皇帝汇报紧急、非常事件的文书,其内容特殊,可以越级上报,日本学者大庭脩在《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中曾根据居延汉简复原过一篇关于汉匈军情的变事书残册,可以参看。
官府往来文书是各官府间互相行文而形成的文书,包括奏记、牋记等上行文书,教、下行记等下行文书和平行官府之间的文书。其反映了各个行政部门的日常行政活动,史料价值巨大。传统文献中关于官府往来文书的记载很少,出土简牍里则有大量此类文书,丰富了学界对文书行政的认识。一方面出土简牍中有很多官府间使用的记、教、檄、传的实物,可以补充我们对这些文书形式的认识。另一方面,简牍中还有大量传统文献失载的文书形式,可以使我们对当时文书制度的细密有所了解。如睡虎地秦简有郡守训诫下属官员的语书;居延、敦煌等汉简有涉及人事升迁、任免、调动的除书和遣书,有上级官员纠举下级过失的举书,有涉及日常管理的直符书、调书、予宁书、病书、视事书等等。
统计与会计用的簿籍类文书在官私文书中都存在,数量较大,作为官文书其主要用于经济和行政管理。簿是账簿,籍是名籍,秦汉时期簿与籍的区别主要在于“簿常以人或钱物的数量值为主项,而籍大多以人或物自身为主项”。 简牍中簿籍名目众多,簿有集簿、月言四时簿、校簿、计簿、廪食粟出入簿、守御器簿、被兵簿、日作簿、日迹簿、传置道里簿等20余种,籍有吏名籍、卒名籍、吏俸赋名籍、功劳墨将名籍、吏射名籍、吏缺除代名籍、吏换调名籍、以令赐爵名籍、坐罪名籍、休名籍等30余种。 简牍所见比较完整、有代表性的簿籍,主要有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128·1—77)、居延新简《劳边使者过界中费》(E﹒J﹒T21:2—10),悬泉汉简《元康四年鸡出入簿》(Ⅰ0112 :113—131)、《过长罗侯费用簿》(Ⅰ0112 :61—78),尹湾汉简《集簿》(D1)、《东海郡吏员簿》(D2)、《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D3—4)、《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D5正面)、《东海郡属吏设置簿》(D5反面)等。
课录文书,又称案录文书,是处理公务的记录。其以实录为主,具有凭证备查的功能,主要有案、录、刺、志、课等形式,其中课还包含有考核的内容。居延汉简中即有《行塞省兵物录》、《当食者案》、《入官刺》、《出俸刺》、《廪食月别刺》、《表火出入界刺》、《邮书刺》、《表火课》等课录文书。
二、官文书的用语特征
秦汉魏晋时期的官文书受收付双方地位的制约,长期演进,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用语特征。要准确把握某份官文书的含义及行文关系,就必须对这些特定用语有所了解,而作为原始资料的出土简牍极大丰富了我们的认识。“昧死”一词在先秦时期已作为臣民向诸侯言事时的敬词使用,自秦统一至西汉晚期其是臣民上奏皇帝文书的必用语,在武威、居延出土的西汉章奏文书中,可以多次见到“昧死再拜”、“昧死言”、“昧死上书”等用语。王莽代汉后,革新制度,从此到东汉,臣下上奏文书中不再用“昧死”,而改用“稽首”、“顿首”,这些也已被居延、敦煌出土的新莽简所证明。 与上奏文书不同,下级官府的上行文书一般要用“叩头死罪”、“敢言之”,尤其是“敢言之”在出土简牍中使用非常普遍,几乎已成为下级官府对上级官府行文时的必用语。上级官府的下行文书则一般有“告”、“谓”、“下”等习用语。而“移”则主要用于平级机关的行文中。“敢告”一词较为特殊,其主要使用于地位相近的两个机构之间,表示一定的敬义,从简牍材料来看,一般用于郡府之间的行文及本郡太守对都尉的行文中。除了表示上下行关系的习用语外,简牍官文书还有“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书到言”等具有特殊要求的习用语,值得重视。
三、文书运行制度
文书制度除了类型、格式等制度外,还包括与传递收发、管理存档等密切相关的文书运行制度。
在秦汉文书行政的大背景下,国家对公文的收发、传递、启封等制度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这些在简牍材料中有所体现。出土秦汉法律简牍中,有“行书律”,其对公文的登记制度有严格要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行书》中明确规定,传送或收到文书必须登记发文和收文的准确时间,以便以后追查。征诸汉简,可以发现这种制度有日益严格的倾向。通过对西北文书简的整理,我们知道汉代县级以上官府中一般有负责封印、收发、启封文书的小吏。对于每次发送的文书,官府都要予以登记,如居延136·44号简“卒胡朝等廿一人自言不得盐言府·一事集封? 八月庚申尉史常封”就是一则有关发文登记的简。公文抵达收文单位后,收文单位的小吏也须登记,一般是在来文的封检上记录下收文时间、传递者和来文的用印情况。收文完毕,就要启封公文,启封时也须登记文书的件数、印文、启封时间及启封者的姓名,居延214·51号简“书二封檄三,其一封居延卅井候,一封王宪,十月丁巳尉史蒲发”就是一则启封公文,这里的“发”是拆封的意思。发文单位将正式文书发出后,一般还会留副本备查,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出土汉简中有一块签牌,其正面文字为“永元二年七月以来发书刺本事”,背面文字为“功曹”,应是自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七月起由功曹发出的书刺文书副本的存放处的标识。 从这些稍显繁琐的登记制度中,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公文制度的严密。
公文传递讲究时效,睡虎地秦简《行书律》对公文的传递有严格规定:命书及标明急字的文书,应立即传送;不急的,当天送完,不准搁压,搁压的依法论处。在居延、敦煌汉简中,有邮书刺和邮书课。邮书刺是关于传递邮书过程的实录文书,邮书课则是根据邮书传递情况对相关传递人员的考评,其考评结果有“中程”、“过程”、“不及行”之分,“中程”指传递使用时间与规定时间相符,“过程”指迟到,“不及行”指提前,而传递文书“过程”者显然将受到一定惩处。
出土简牍中不但有正式的官文书资料,还有许多官文书的草稿,这些草稿以上行文书居多,字体较为潦草,发文人名常以符号或“君”替代。将它们与正式文书对比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官文书制度的认识。
第三节? 简牍所见政治风云
出土简牍不仅能补充传世文献中有关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记载,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时有涉及。由于材料本身的原始性,其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传世文献语焉不详、真伪难辨的缺陷,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一些历史事件有重要意义,是先秦秦汉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书籍和文书是今天所见简牍材料的两种主要内容。它们都包含着一些对认识具体历史事件有价值的材料。《晋书·武帝纪》和《束皙传》记载了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汲冢书”的出土,其中的数十车竹简中即有《纪年》13篇,记载了从夏以来到战国中晚期的历史,有不少可订正和补充经传史记的地方。《晋书·束皙传》称:“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这里对“益干启位”、“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和”等政治事件的描述,皆与《史记》不同。遗憾的是,这部西晋时重见天日的竹简本《纪年》,在唐宋之后又逐渐散佚殆尽,至今日只有王国维、方诗铭等先生的辑本存世。
20世纪是简牍材料大发现的时代,其中一些久佚书籍的重新发现,对认识某些政治现象有重要意义。1994年,上海博物馆曾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一千多枚战国楚简。整理后发现,其中有不少记载上古及春秋史事的书籍。《容成氏》篇记载了汉儒已不能明其事的“文王平九邦”。《子玉治兵》和《两棠之役》等篇记载了春秋时期楚国参与争霸战争的一些情况,内容涉及晋楚城濮之战和邲之战。《三郤之难》篇则是关于春秋中期晋厉公为加强君主权力与以三郤为代表的异姓卿大夫进行政治斗争的记载。这些内容补充了今本《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的相关记载,有重要史料价值。
再如庞涓和马陵之战的问题。《史记·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六国年表》、《商君列传》和《孟尝君列传》都说齐魏马陵之战中魏太子申被虏、将军庞涓被杀,《孙子列传》称庞涓“自刭”。《战国策·魏策二》说:“齐魏马陵之战,齐大胜魏,杀太子申”,未提庞涓,而《齐策一》又说:“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禽庞涓”,几种说法互有歧异。1972年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已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其中《擒庞涓》和《陈忌问垒》两篇分别谈到“击之桂陵而擒庞涓”和“取庞□而擒太子申”。据简文可知,庞涓作为魏将,不只参与过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也参与过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在桂陵之战中其战败被擒,但之后他可能被放回魏国,并再度为将,十二年后在马陵最终身死。 庞涓与桂陵之战的关系,及其被擒与被杀的细节,借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出土而大白于世。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名著,以“文直”、“事核”著称于世,但由于其有关战国、秦代的记载,主要是依据“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的《秦记》,所以也存在着史实疏漏,甚或纪、传相互矛盾的问题。而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则大大扩充了我们对战国后期及秦代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的认识。尤其是其中的《编年记》53简,记述了从秦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将近九十年间,秦通过战争手段灭亡六国至于统一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印证、补充乃至订正《史记·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等文献的作用,加强了我们对秦统一过程的理解和认识。《史记·秦本纪》和《六国年表》都提到,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魏献故都安邑于秦,但未言魏献城的原因。《编年记》载:“(秦昭王)廿年,攻安邑”,这条史料补充了《史记》的缺漏,使我们明白魏的献城是以前一年秦对安邑的进攻为前提的。化名张禄的范雎在秦昭襄王统治后期相秦,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是战国后期著名历史人物。其曾保荐故人郑安平和王稽分别担任秦的将领和河东守。长平之战后,郑安平投降赵军,不久河东守王稽也因“与诸侯通”而“坐法诛”。《史记·范雎列传》记载,范雎因这两件事心中不安,“谢病请归相印”,最终将秦相的位置让与燕人蔡泽。而《编年记》中关于此事的记载与《史记》不同,直称昭王五十二年(公元前255年)“王稽、张禄死”。这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林剑鸣先生据此认为,《史记》相关记载有误,范雎与王稽被同时处决,实不得良死。
关于秦王政亲政后积极剪灭六国的过程,《编年记》载:
十七年,攻韩。
十八年,攻赵。……
十九年,□□□□南郡备敬(警)。
廿年,……韩王居□山。
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属。
廿二年,攻魏粱(梁)。
廿三年,兴,攻荆,□□守阳□死。四月,昌文君死。
【廿四年】,□□□王□□。
这里秦攻灭韩、赵、魏、楚四国的过程,与《史记》的记载基本一致。而关于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南郡备警”的记述则可以与秦并天下后始皇诏书里“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的诏文相印证。从“十九年”到“廿四年”的记载中,除“攻魏粱”一条外,“其余所记是前后有关连的一件大事,涉及韩灭亡以后的余波和楚国被灭时几次反复的战役。” 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和二十三年“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的记载参看可知,韩王被徙引发了韩人的反秦斗争,这一斗争又促成了韩王之死,此后有楚王室血统的秦国贵族昌平君居于其地,又被项燕立为楚王领导反秦战争,最终失败。
不仅简牍书籍中有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内容,为数甚巨的秦汉魏晋出土文书,虽以反映下层吏民的屯戍、经济生活为主,但其中也不乏对当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1977年8月出土于玉门花海的一枚七面菱形觚中就含有汉代前期某位皇帝的遗诏: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谋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侅(亥)自次(恣),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欠。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惕惕),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怯。
这位皇帝临终前教育太子要以胡亥为戒,善遇百姓、存贤近圣,与汉初诸帝的历史形象基本一致。
西汉昭宣时期,王朝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经济和文化都有所进步,被史家称为“昭宣中兴”,但征诸史籍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并不平静,围绕最高政治权力曾展开许多斗争。昭帝时期,大将军霍光秉政,于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十月镇压了以燕王刘旦、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治集团。昭宣易代之际,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觊觎皇位,宣帝即位后,仍“使巫祝诅”,后事发,自杀、国除。1974年肩水金关遗址出土大量汉代简牍,其中有后来被命名为《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的木牍三枚,是汉政府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发布的通缉大婢外人的命令,外人因具备“故广陵王胥御者惠同产弟”和“故长公主盖卿大婢”的双重身份而被通缉,反映了宣帝时期对广陵王等谋反集团的追查,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西北汉简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到王莽政权。居延甲渠候官和卅井候官遗址出土的简牍中有对居摄元年(公元6年)汉安众侯刘崇和居摄二年(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及一些刘氏宗室起兵反抗王莽的记载,反映了王莽篡汉之前与汉朝皇族的尖锐矛盾。王莽称帝后,采取了一些错误的民族政策,激起了西域诸国的反叛。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莽派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出西域,与焉耆等西域政权发生了激烈战争,敦煌汉简中有不少关于此事的记载,其中不乏当事者给王莽陈述军情的上书,为我们理解这一战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99年至2002年间,额济纳汉代烽燧遗址又出土了500余枚汉简,其中有王莽登基诏书和封匈奴单于诏书,非常珍贵。
王莽政权败亡之后,河西地区处于窦融的管理之下。居延汉简,尤其是居延新简中有相当多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记载,甚至有窦融策应刘秀进攻隗嚣的内容,这对我们了解窦融的政治立场和东汉前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形势有重要价值。
第四节? 简牍所见法制文书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时期,其间产生了大量法制文书。据《汉书·刑法志》,汉武帝时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读。”法律数量不可谓不大,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法制文书大都没有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给后人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不便。
20世纪以来出土了大量战国秦汉魏晋简牍材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法制文书,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律令,也包括司法文书,这些材料的出土为中国法制史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持,意义重大。比较有代表性的出土法制文书主要有荆门包山楚简的《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云梦睡虎地秦简的《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效律》、《法律答问》、《封诊式》,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奏谳书》等。此外,云梦龙岗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居延、敦煌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材料中也有较多司法、律令方面的文书,值得重视。
法制文书从大的方面可分为律令和司法文书两类。
一、律令类
律令多以条款形式见存,由朝廷以及相关部门制定,在出土秦汉魏晋简牍中一般又可分为律、令、科、品、式、法律答问诸类。
1.律
战国时期李悝著《法经》6篇,后商鞅改法为律,从此律成为秦汉时期律令类文书的主要形式,其主要是针对某一类或某一部门事务所作的规范性规定。出土的秦汉简牍中,律目形式众多,据李均明先生统计,至少有贼律、盗律、囚律、捕律、杂律、效律、户律、厩苑律等45种。
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律文发现较少,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末尾附抄了两条魏国法律,分别是关于户籍管理的《户律》和发配特殊人群从军的《奔命律》。
出土简牍中有关秦律(包括秦国和秦王朝)的内容较多,主要有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青川木牍等,其中尤以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和《秦律杂抄》最为集中。《秦律十八种》是《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军爵律》、《置吏律》、《效》、《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等十八种秦律的摘抄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工律》、《工人程》、《均工》主要体现了秦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生活的管理,其它法律则多属于行政法规。《属邦》的内容与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有关,《内史杂》和《尉杂》则基本是对内史和廷尉两官府职责的法律规定。除了《秦律十八种》有《效》外,睡虎地秦简和江陵王家台秦简中还有专门的《效律》简,其内容更详细,主要与官府物资账目、度量衡器的核查有关。《秦律杂抄》所抄录的律文,有的有律名,有的没有,存在的律名计有《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牛羊课律》、《傅律》、《敦表律》、《捕盗律》、《戍律》11种。青川郝家坪木牍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秦政府对《为田律》的修改情况。云梦龙岗秦简则主要是关于秦代“禁苑”的一些法律条文。
20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和336号墓分别出土了一批汉律。247号汉墓的下葬年代系吕后时期,墓中《二年律令》的出土使亡佚已久的汉律得以重现,价值巨大。大部分学者认为《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前186年)施行法律的抄本。简文包含了当时汉律的主要部分,计有27种律和1种令。其中27种律分别是:《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其内容有与睡虎地秦简所出秦律重合的部分,为对比秦与汉初法律制度异同提供了珍贵资料。也有超出秦律的部分,尤其是包含有《贼律》、《盗律》这种传统法律系统的主体,意义重大。336号墓所出汉律内容大体与247号墓《二年律令》相类,不同者是有关于流放的《迁律》和关于朝觐礼节的《朝律》。1987年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出土部分东汉简牍,其中包含汉代《贼律》律文数条。以居延、悬泉为代表的西北汉简中也有不少零星的汉律资料,前者有《囚律》、《捕律》,后者有《贼律》、《囚律》等。
2.令
令,即法令,主要指皇帝针对时政所颁布的命令。在汉武帝时期担任廷尉的杜周曾说:“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 《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引文颖曰:“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由此可知,“令”主要是统治者根据不同情况对“律”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出土简牍所见之“令”,几乎全是汉令,主要有王杖诏书令、津关令、功令、挈令、军令、赏令等名目。
王杖诏书令? 是关于优抚持有王杖的老人的法令,这一法令与汉政府对“尊老”、“养老”的提倡有密切关系。1959年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曾出土10枚王杖诏书,被称为“王杖十简”。1981年,文物部门在当地又征集到26枚类似简牍,简册以“王杖诏书令”作为书题,较为完整。
津关令? 津是渡口,关即关卡。津关令是有关津关通行的法令,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功令? 是有关考核和选任、嘉奖官吏的法令,见于居延汉简。功令包含许多条款,居延汉简中的功令主要是“功令第卌五”,是边塞地区关于秋射考核的法令。
挈令? 是有关执法机构根据本部门或本地区的需要,从国家法令条款中抄录有关内容另编成册而形成的法令,根据适用对象不同,可分为很多种,有以地区命名的,也有以机构命名的。 居延汉简中有不少“北边挈令”,是关于北方边塞事务的法令摘录。此外,武威汉简和敦煌汉简曾分别提到“御史挈令”、“卫尉挈令”、“兰台挈令”和“大鸿胪挈令”、“大尉挈令”,只是大都没有具体的令文。
军令? 古代军事律令或作战条例的统称,见于大通上孙家寨汉简,原简中具体的令名有“军斗令”、“合战令”等。
赏令? 关于赏赐的法令。敦煌汉简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主要是对击匈奴有功者予以奖赏的法令。
汉代法令众多,有以甲、乙、丙顺序结集者,称《甲令》、《乙令》、《丙令》或《令甲》、《令乙》、《令丙》。武威汉简有“民作原蚕,罚金二两,令在乙第廿三”的简文,即是说“民作原蚕,罚金二两”这条令文摘录于《令乙》的第23条。
3.科、品
科、品是律令条文的补充。居延新简有《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其由《捕匈奴虏购科赏》和《捕反羌科赏》两部分组成,规定了根据捕获敌方人员的级别和数量予以奖励的方法。“品”在简牍中较“科”普遍,其规定多与级次相关,主要有居延新简的《罪人入钱赎品》和《塞上烽火品约》等材料。此外,敦煌汉简中也曾提到《守御器品》、《伏虏品约》、《敦煌郡烽火品约》等品。
4.式
《说文解字》称:“式,法也。”式有范例、模式的意思,可以用来规定行政、司法中应遵循的原则、程序。简牍所见的“式”,主要有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封,查封、查抄;诊,检验、勘验。《封诊式》是治狱文书的样本,通过归纳以前办案过程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为此后审讯、侦察、收捕等法律行为提供范式。其共分25节,除《治狱》、《讯狱》两节是关于审案的基本要求外,其余各节都是关于调查、审讯、法医检验的具体记载。由于其内容包括很多经典案例,所以李学勤等学者认为它的性质可能类似于后代的“比”。
5.法律答问
见于睡虎地秦简,是律令条文的重要补充。其采用问答形式,对有争议的律令予以官方解释,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二、司法文书类
司法文书是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形成与使用的专用文书。其与作为条文的律令不同,是司法实践的直接产物,体现了对成文法的执行与运用。包山楚简、张家山汉简、新旧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及走马楼吴简等简牍中都有不少司法文书。
包山楚简司法文书大都是各地官员向楚国中央政府呈报的案件记录,包括《集箸》、《集箸言》、《受期》、《疋狱》四部分。其中《集箸》和《集箸言》是有关案验名籍的案件。《受期》是受理各种诉讼案件的时间与审理时间及初步结论的摘要记录。《疋狱》即“记狱”,是关于起诉的简要记录,主要涉及杀人、逃亡、土地纠纷、继承权之争、强占妻妾等案件。
长沙走马楼吴简总计10万余枚,内容丰富,包含部分司法文书简。《许迪割米事》文牍即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例,记载了长沙郡某属县的录事掾奉督邮敕对本县县吏许迪贪污官府余米案的审讯经过。
出土简牍中的司法文书,仍以秦汉时期的最具代表性,大致可以分为劾状、爰书、推辟验问书、奏谳书等类型。
劾状即起诉书,通常由劾文、状辞、呈文三部分组成。劾文是对被告身份及犯罪事实的陈述。状辞是原告的自述,内容与劾文相似,但更为详细。呈文则是呈送劾文与状辞的报告。20世纪70年代在居延破城子68号探方出土的简中就有8例较完整的劾状简册。
爰书是司法过程中产生的笔录文书,包括对原告、被告、证人验问言辞的记录,现场勘验的记录,查封财产的记录,追捕犯人的记录等等。 其名目繁多,简牍所见有“自证爰书”、“相牵证任爰书”、“证任名籍爰书”、“驿马病死爰书”、“骑士死马爰书”、“射爰书”等。居延新简中有部分爰书实物,《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是当时边郡一件民事诉讼案的原始卷宗,详细记述了案件始末和验问判决过程,其中即包含有“乙卯”、“戊辰”、“辛未”三份验问爰书。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也曾引用过一些爰书作为范例,可参看。
推辟验问书主要是针对一些客观现象进行调查的文书,与验问爰书有相似之处。70年代破城子22号房屋遗址出土的汉简中有不少属于推辟验问书,如《驹罢劳病死册书》就是较完整的一例。
奏谳书是下级官府将疑难案件呈报上级的上行文书及上级所作的议罪、判决之词。张家山汉简247号墓出土有《奏谳书》,共包含22个奏谳案例,其中春秋案例2则,秦案例3则,汉初案例17则。须奏谳的案例,大都是疑难案件,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成文法的不完善而导致下级机关上奏以求上级定夺的。经上级议定过的这种案件,之后可以作为下级司法机关判决类似案件的标准。这样,包含典型案例的奏谳书逐渐就有了“比”的性质。张家山汉简《奏谳书》集中了22则这种案例,解决了许多成文法存在的问题,在当时主要作为下级官员判案时的参考。
简牍法制文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对战国秦汉魏晋史和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概括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诉讼制度以及刑罚制度的认识。
第二,极大推动了古代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制度史研究。出土律令主要是当时国家进行行政、经济、社会管理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必然涉及作为各领域内办事规程和行动准则的制度。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为例,其《置吏律》、《秩律》推动了职官制度研究,《置后律》推动了继承制度研究,《传食律》、《行书律》推动了驿传制度研究,《兴律》、《徭律》推动了徭役制度研究,《户律》推动了户籍制度研究,《钱律》、《金布律》推动了货币管理制度研究,《津关令》则推动了关市制度研究。
第三,法律规定了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其律令条文和司法实践加深了我们对古代阶级关系、家庭关系、经济关系等社会现象的认识。如在出土的秦汉法制文书中,平民和奴婢犯罪量刑标准不同,就是当时阶级关系的反映。又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有以下几条律文:
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 32
妻殴夫,耐为隶妾。??????????????????????????????????????? 33
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34
父母殴笞子及奴婢,子及奴婢以殴笞辜死,令赎死。??????????? 39
这里妻、子、奴婢对夫、父母、主人的犯罪,与夫、父母、主人对妻、子、奴婢的犯罪在量刑上的巨大差别,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具有特色的阶级关系和家庭伦理关系。
第四,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路,有助于专题研究的深化。出土简牍既有秦律,又有汉初律令,两相比较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传统上“汉承秦制”说法的认识。从睡虎地秦简出土秦律可以发现,秦政府非常重视行政效率,对官吏的管理几近苛刻,而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往往是“赀甲”、“赀盾”,这些信息体现了秦政权的追求效率和军事化特征。在战国晚期,最终实现统一的是秦,而不是其它六国,千百年来学者对其中原因争论不息。云梦秦简出土后,直接促使我们在思考此问题时,会考虑到秦的行政效率及国家机器军事化在其中的作用,这无疑深化了此项研究。
第五节? 简牍所见诉讼世界
上节概述了出土简牍法制文书的基本情况,本节拟以这些法制文书为基础勾勒秦汉魏晋时期的诉讼制度。
诉讼指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诉讼程序、司法原则、刑罚制度是其重要内容。关于秦汉魏晋时期的诉讼制度,传统文献记载不多,近年来简牍法制文书的出土对这项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尤以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及《二年律令》中的《囚律》、《捕律》、《具律》、《告律》、《收律》等材料最为重要。
根据出土简牍的记载,秦汉时期的诉讼程序主要可分为告劾、逮捕、审讯、论报、乞鞠等环节。
告劾是起诉环节,“告”主要指由私人进行的告发,包括受害人自诉、当事人自首、他人举报等。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中对起诉应遵循的原则有详细规定,主要有:(1)自告减罪,但子女杀伤祖父母、父母,奴婢杀伤主人的案件例外;(2)诬告及告人不审,都要负法律责任,《告律》载:“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3)禁止匿名控告,有以“投书”即匿名信的方式告发别人的,官府不但不予受理,反而有权对控告者予以拘捕;(4)子女、奴婢不得告尊长,告发者弃市;(5)未满十岁的儿童及刑徒没有告发的权力。
告劾被受理后,就要控制相关嫌犯的自由,对于所涉案件较大的则须进行拘捕。如果嫌犯已经逃跑,政府就要发布通缉令,要求各地官府协助追捕,这在简牍中一般被称为“名捕”。一些影响较大的犯罪则会由中央机关以诏书的形式通缉,这种诏书即是“名捕诏书”,今天在居延汉简中有写有逃犯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身份、相貌、所犯罪行的名捕诏书,可参看。
逮捕到嫌犯后,诉讼就可以进入审讯程序。根据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的记载,在正式审讯前,审判机关有时还会进行搜索并查封嫌犯家庭、勘验犯罪现场、鉴定犯罪事实等侦查活动。当时对各类案件的勘验、检查都有一套规程,其中甚至有不少关于法医鉴定的内容。如《封诊式》的“经死”节记载了关于区分自缢和他杀的标准,规定遇到所谓自缢案件,应仔细查看绳结和死者尸体,通过观察尸体的具体形态来断定是否属于自缢;“疠”节记载了对麻风病的鉴定方法;“出子”节是一则关于孕妇甲与女子丙发生争斗而导致流产的诉讼案件,司法机关在接到诉讼后,对已流产的胎儿和孕妇甲分别进行了医疗鉴定,以判断是否真有流产情节。
在审讯过程中,重视人证、物证的作用,如果证人做伪证,则要受到惩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规定:“证不言请(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出入罪反罪之。”
审讯的方式主要是诘问,司法官员根据被告人陈述中的漏洞,层层追问,直至被告人无从辩解为止。睡虎地秦简《封诊式》对诘问的讯狱方式有具体要求:审讯者须听完被告人的陈述再提问,即使明知中间有欺骗的地方,也不要打断;陈述完毕后,审讯者对其中不清楚或有矛盾的地方提问,要求被告人作出解释;听完其解释后,再找出漏洞予以提问,直至把案情理清。原则上来说,审讯过程中,不提倡刑讯,“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治(笞)谅(掠)而得人情为上;治(笞)谅(掠)为下,有恐为败”。 不依赖刑讯,通过侦查、分析破获疑案的官员,会受到官府表彰。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一则被称为“不知何人刺女子婢最里中”的案例,女子婢在巷中行走,后面过来的人用刀将其刺伤,并抢走1200钱,狱史顺等人破不了此案,另一狱史举 受命接办,通过调查凶器、合理的讯问而破案,其案“以智”求得,最终狱史举
受命接办,通过调查凶器、合理的讯问而破案,其案“以智”求得,最终狱史举 以“能得微难狱”受到奖励。当然,如果在审讯中被告人多次欺骗,并且不断改变口供,行为已够得上“笞掠”的,讯狱者有权对其依法笞掠,笞掠过程则要以“爰书”的形式予以记录。
以“能得微难狱”受到奖励。当然,如果在审讯中被告人多次欺骗,并且不断改变口供,行为已够得上“笞掠”的,讯狱者有权对其依法笞掠,笞掠过程则要以“爰书”的形式予以记录。
从律令上看,秦及汉初政府对刑讯是有严格限制的,但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杜绝刑讯显然只能是一个理想。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秦代的“黥城旦讲乞鞫”案,即是一则狱吏通过严刑拷打断案,最终制造出冤狱的实例。有个叫毛的人,因为盗牛被官府抓捕,官府要求其供出同伙,其回答没有,官府不信,对其进行刑讯,直至“血下污地”。其不能忍受痛楚,便诬称一个叫讲的人为同谋。官府抓来讲,讲不承认有谋盗牛的行为,官府又对其予以刑讯,笞其背十余伐,并用水浇其受创的背部,直至讲承认自己谋盗牛为止。后来检查毛和讲的身体,讲背部的伤痕大如手指的有13处,小的瘢痕互相交叠,由肩至腰,密不可数;毛的背部、臀部、两股也都是瘢痕累累,惨不忍睹。由此可见,当时审讯过程中用刑的酷烈。
审讯结束后,如果案件在适用法律或其它方面确有疑难,则须进入奏谳程序,由上级审判机关评议、断决。如果是一般的案件,则进入论报程序。论报,又称为“鞫”,是法官对审讯案件作出的结论。从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保存的一些案件鞫词来看,其应该包括审定的事实、适用的律令条文、对案件的断处决定等几项内容。在论报过程中,徇私舞弊、论狱不直的官员,一经查实,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载:
鞠(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止(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
治狱者有故纵、不直,及故意不仔细侦查、审问行为的会受到严厉惩罚。如果治狱者并非故意舞弊,只是因疏忽大意误用刑罚,一经发现,也要受到“失刑”罪的处理。
至此,诉讼程序已基本完成。但如果被告对判决不服,则可以按照法律规定“乞鞫”。“乞鞫”,就是请求重新审理,类似于今天的上诉制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中有关于“乞鞫”的法令,以《具律》为例:
罪人狱已决,自以罪不当欲气(乞)鞫者,许之。气(乞)鞫不审,驾(加)罪一等;其欲复气(乞)鞫,当刑者,刑乃听之。死罪不得自气(乞)鞫,其父、母、兄、姊、弟、夫、妻、子欲为气(乞)鞫,许之。其不审,黥为城旦舂。年未盈十岁为气(乞)鞫,勿听。狱已决盈一岁,不得气(乞)鞫。气(乞)鞫者各辞在所县道,县道官令、长、丞谨听,书其气(乞)鞫,上狱属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都吏所覆治,廷及郡各移旁近郡,御史、丞相所覆治移廷。
乞鞫必须发生在案件审理结束后一年之内,被告人乞鞫后,上级机关会派人“覆”狱,即重新审理。如果乞鞠内容有虚假,则罪加一等,如果成功,不仅要撤销原判决,还要赔偿因错判而给被告人造成的损害。前述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秦时的“黥城旦讲乞鞫”案,就是一则被告人由乞鞠而沉冤得洗的案例。被告人讲因不实的“谋盗牛”罪被黥为城旦,受刑后其向上级司法机关上诉“乞鞫”,上级司法机关接受了上诉,重新审理后认为这是冤狱,处理的结果是为讲平反,讲的妻、子受此案的牵连前已被卖为奴,这时政府为其赎回,被查抄卖掉的家产,作价偿还。
出土秦汉简牍中的案件,大部分都是刑事诉讼。与今天民事诉讼较接近的案例则有居延新简的“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这起诉讼由甲渠候粟君提出,是一则军官与普通百姓的经济纠纷案。此案由居延县审理,在24天的时间内,经过了3次验问,4次“爰书”,最终以普通百姓寇恩的胜诉结案。此案审判程序完备,对于汉代法制史研究来说,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例如我们都知道《汉书·百官公卿表》是研究西汉官制的最重要史料,但其中对西汉官制的记载很多是西汉末年的定制,而对西汉中前期制度的记载并不十分清楚。如果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中,将其记载视为是可以囊括西汉一代的制度,以点代面,就很容易发生错误。
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制考》,《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
李均明、汪桂海等学者对秦汉官文书制度有较多研究,本节内容主要参考了李均明《简牍文书学》、《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等著作的相关成果。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7页。
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247页。
参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4页。
骈宇骞、段书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49页。
参杨宽《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页。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276页。
马雍《读云梦秦简〈编年记〉书后》,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
关于“爰书”的具体性质,学界有不同意见。此处主要采纳了刘海年、初师宾、李均明等学者的观点。日本学者籾山明则认为爰书就是由负责官吏所作成的、为了进行公证的文书,其所证明的事实既可以成为诉讼之际的书证,也可用在与司法完全无关的场合。(籾山明《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