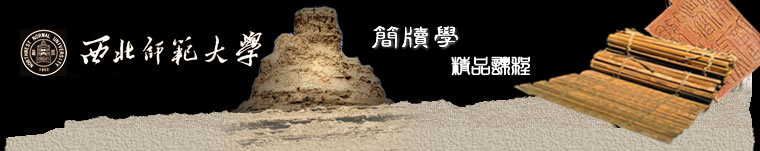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张世超:《殷墟甲骨字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7页。
此牍现藏大英图书馆东方部,详胡平生、李天虹:《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55页。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63-64页。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页。
大辞海编辑委员会《大辞海·语言学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赵平安:《隶变研究》“张振林序”,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
吴白匋:《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年第2期。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7、68页、72页。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196页。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李学勤序”,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0页。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107页。
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页。
简帛文献语言研究课题组:《简帛文献语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67页。
李学勤《汉字——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97-102页。
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74页。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11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郭店楚简”专号)》第十七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8月,第486页。李零:《上博楚简校读记(之二):〈缁衣〉》,《上博馆藏战国楚竹简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3月,第412页。
赵平安《从楚简“娩”的释读谈到甲骨文的“娩 ”——附释古文字中的“冥”》,《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55-59页。
”——附释古文字中的“冥”》,《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55-59页。
陈剑《说慎》,《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207-214页。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