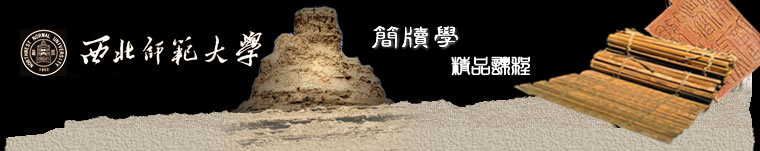第五章 简牍中的经济制度
简牍中也有不少反映经济制度的文书,主要集中在睡虎地秦简法律类文书、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的“簿籍”类文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及《算术书》、尹湾汉简行政类文书、凤凰山汉牍、纪庄汉牍等,内容涉及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上计制度、契约制度等,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史籍之不足,为我们了解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全新的史料。几十年来,经过爬梳整理,学界已在利用简牍材料研究秦汉经济史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第一节张家山汉简所见土地及赋税制度
战国至魏晋时期的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但由于史料的匮乏,学界存在分歧和争议。可喜的是,随着近年来大批简牍材料的相继面世,尤其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出土,这些问题逐渐清晰起来。
一.“名田宅”制度
1.田宅的授予标准
《史记·商君列传》载:“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说明商鞅变法时曾经建立过一套按照人身尊卑和爵位等级分配土地的“名田宅”制度。《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上书云:“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赡)不足,塞兼并之路。”又载哀帝时下“限田令”云:“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时期也曾实行过某种以爵秩为基础的“名田“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具体情况如何?各种史籍均无明确记载。2001年公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则展现了田宅的详细授予标准:
关内侯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袅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户律310~312号)
宅之大方卅步。彻侯受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二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袅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宅,公卒、士伍、庶人一宅,司寇、隐官半宅。(户律314~316号)
律文清楚地表明二十等爵制的划分是西汉早期的“名田宅”制度的基础。不同爵位的人占有田(宅)的数量从一百零五宅到一顷(宅)半不等(律文没有规定列侯应当占田的数量,大约是因为列侯有封国,故不受田),其中左庶长以上十种爵位占有量较多,公大夫以下七种爵位占有量较少,五大夫、公乘两种爵位占有量居中。律文还规定没有爵位的公卒、士伍、庶人也可占有田(宅)一顷(宅),甚至连受过刑罚的司寇和隐官也可以占有田(宅)半顷(五十亩)地,说明这项土地制度几乎覆盖了整个社会人群。
2.田宅的继承与转让
《二年律令》还对田宅的继承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无)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312~313)”律文规定的是田宅的继承顺序及田宅数量达不到相应标准时的补偿条件:受田者不幸亡故后,可让他的继承人(长子)优先选择田地,然后再分配给其他儿子。其他儿子想要独立为户,可把“其□田”分配给他。其他儿子虽已立户但没有田宅或者田宅数量没有达到相应的标准,可以补足。但补足宅地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和原有宅地相连。
《二年律令》所见田宅的继承还需履行一定的法律程序:“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叁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户律336~简334)”律文显示如果有人要立遗嘱分割死后田宅,乡部啬夫必须亲自到场并书写券书,并按上户籍的程序上报有关机构,作为法律依据,(以后)后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就严格按照遗嘱办理。如果乡部啬夫不按规定写下“先令券书”则要罚金一两。可见西汉政府对于田宅的继承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二年律令》显示女子也可以继承田宅:
女子为父母后而出嫁者,令夫以妻田宅盈其田宅。宅不比,弗得。(置后律384)
寡为户后,子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子田宅。(置后律387)
第一条律文大意为:在女子已经继承了父母遗产后又出嫁的情况下,国家可以用妻子的田宅来补足丈夫田宅的不足。但宅地如果不相连,则不能拿来补足。可见在无男性继承人的特定情况下,女子也可以继承父母田宅。第二条大意为:在寡妇作为继承人的情况下,其田宅数量按其子继承户主应该占有的标准继承。如果寡妇不具备立户条件而坚持立户的,其继承的田宅数量,只能以庶人的标准继承。此条又说明如果子女尚未成年,寡妇也可以继承田宅。
《二年律令》显示国家所授予的田宅可以买卖或赠与:
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不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户律320)
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户律321)
第一条律文对普通百姓扩展宅地的买卖进行了详细规定,即百姓所想买入的宅地必须要和原有宅地相连,否则不予准许;但官吏及为皇帝宦者不在此列。我们推想这一规定可能与当时的什伍制度有关,百姓的户籍及居住地不能随意变动。第二条律文规定受田宅者如果将其田宅赠与或出卖给别人,不能再次授田。这两条律文虽然对田宅的买卖和赠与行为进行了种种限制,但透过律文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西汉初期,国家所授田宅是可以买卖或者赠与。
《二年律令》还显示田宅买卖后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代户、贸卖田宅,乡部、田啬夫、吏留弗为定籍,盈一日,罚金各一两。”(户律322)律文中提到田宅买卖后相关吏员必须迅速办理过户手续,不得拖延。超过一日,每人罚金一两。可见西汉政府对于田宅过户的法律程序是相当重视的。
此外,《二年律令》还制定了对几种非法占有田宅行为的处罚规定:“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它如律令。”(户律323~324)律文规定若发现“不为户”(疑为不在官方登记户口或办理过户手续而私自占有田宅)、“有田宅附令人名”(疑为自己已有田宅还以某种形式占有他人田宅)及“为人名田宅”(疑为以某种形式将自己的田宅转让给他人)者均要处罚戍守边防二年,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田宅。但若“为人名田宅”者有告发非法占有田宅者的情形,则可以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国家还可将其所转让田宅赐予他。
3.田宅的收回
《二年律令》中也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国家要收回田宅。如:
田宅当入县官而诈代其户者,令赎城旦,没入田宅。(户律319)
罪人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田宅。(收律174)
第一条律文规定如果发现有人冒称自己是户主从而占有某些应当归还官府的田宅,冒名者要判处“赎城旦”刑罚,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田宅。从文中“诈代其户”一语来看,这些“当入县官”的田宅似为绝户田。第二条规定如果有人被判处“完”、“城旦舂”、“鬼薪”以上刑罚,或受腐刑,官府要没收其所得田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将绝户田及一些罪行较重罪犯的田产收归国有的制度早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实行了。
《二年律令》还规定民户也可以主动向政府退还田宅:“田不可垦而欲归,毋受偿者,许之。”(田律244)律文规定如果被授土地过于贫瘠,没有垦殖价值,可以退还给官府,但不能要求另外补偿。说明田不但可以由国家收回,而且受田者也可以主动退还给国家,这大约与赋税制度有关。
4.“名田宅”制度的实施
《二年律令》公布以后,朱绍侯、高敏、臧知非、杨振红、于振波、王彦辉、张金光等学者纷纷著文,从不同角度对战国秦汉时期“名田宅”制度的实施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取得不少共识。其中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一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认为:“名田宅”这套制度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确立的,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为其后的秦帝国和西汉王朝所继承。国家通过爵位减级继承制控制田宅长期积聚在少部分人手中,并使手中不断有收回的土地,它们和犯罪罚没的土地以及户绝土地一起构成国家授田宅的来源,授予田宅不足的民户。文帝时期由于国家不再为土地占有立限,使这套制度走向名存实亡,“名田制”仅仅作为土地登记的手段而存在。此后,脱控的土地兼并掀起狂潮,并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危机,西汉末年哀帝和王莽曾力图恢复限田,但无奈这套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以失败告终。东汉政府则基本上放弃了对土地占有加以控制的努力,听之任之。
二.赋税制度
1.刍槀税
刍槀为马牛饲料。为了满足军队及邮驿系统官有马牛饲料的需要,中国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一直向民户征收刍槀税。《国语·鲁语下》:“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这是春秋时期已有刍槀税的明证。文献中有关秦代征收刍槀税的记载有二:《淮南子·氾论训》:“秦之时,……发谪戍,入刍、稿。”高诱注:“入刍稿之税,以供国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二世时,以“度用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但其税额如何确定,史籍不甚明了。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则有载:“入顷刍槀,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顷入刍三石、槀二石。”(田律9)律文显示秦代以民户受田的顷数来确定刍槀税的标准,无论民户所受土地是否耕种,每顷土地均须缴纳刍三石、槀二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也有类似规定:“入顷刍槀,顷入刍三石;上郡地恶,顷入二石;槀皆二石。令各入其岁所有,毋入陈,不从令者罚黄金四两。收入刍槀,县各度一岁用刍槀,足其县用,其余令顷入五十五钱以当刍槀。刍一石当十五钱,槀一石当五钱。”(田律241)律文所见西汉初期刍槀税的缴纳标准与秦代基本一致,即每顷纳刍三石、槀二石。但在某些方面有较大变化:其一,规定上郡等土地较为贫瘠地区的刍税为每顷二石,减轻了当地民户的刍税负担;其二,对刍槀的质量有了明确要求,即不能缴纳存放一年以上的陈刍、陈槀,否则罚黄金四两;其三,以县为单位计算当年所需刍槀,足用之外,令民户按每顷五十五钱的标准纳钱代物,其换算标准为刍一石折合十五钱,槀一石折合五钱。说明汉初刍槀税主要用于地方需要,当与汉初承平日久,没有大的战争有关。但刍槀的价格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纳时刍槀税价格较高,则有另外的折算办法:“刍槀节(即)贵于律,以入刍槀时平贾(价)入钱。”(田律242)律文显示若刍槀价格较高,超出前述刍一石折合十五钱,槀一石折合五钱的标准,则按纳税时的刍槀平价折算,反映出汉初商品经济有所发展。
《二年律令》还显示卿以上高爵位者可免除刍槀税及田租,反映了他们的阶级特权:“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槀。”(户律317)而卿以下低爵位者、无爵位者及司寇、隐官等罪犯,除了需要缴纳按田亩征稽的刍槀税之外,还需要缴纳按户征稽的刍税:“卿以下,五月户出赋十六钱,十月户出刍一石,足其县用,余以《入顷刍律》入钱。”(田律255)律文显示卿以下者每年十月还要按户缴纳刍税,其标准为每户一石。征足县级所用之外,其余刍税均按《入顷刍律》的标准折算为现钱缴纳。江陵凤凰山汉牍中有“平里”及“稿上”二里的刍税征稽记录,其文为:“平里户刍廿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稿上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其中刍税分为“户刍”及“田刍”两类,前者明显是按户收取,而后者或是按田亩收取的。牍文中也有“(其)二斗为钱、一石当稿”的记录,说明当时确实实行过以现钱折算刍税的制度,而牍文中以槀折算刍的方式在《二年律令》中并未出现,大概是地方政府出于某种需要而作的变通之计。
2.盐铁税
盐铁等工矿业税收是春秋至两汉时期除了田赋及人头税之外的有一大财政收入来源。著名改革家管子曾计算过:如果每升盐增加二钱,则一个万乘之国每月可以获得六千万钱的税收,相当于该国一月应得人头税的两倍;如果每个铁犁铧加价十钱,则三个铁犁铧所得税收就与一个成年人的人头税相当。他还指出如果国家增加人头税势必会招致百姓的反对,但增加盐铁税则可以成功地规避这一风险。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管子盐铁财政的奥妙所在。另一改革家商鞅也十分重视盐铁之利,所谓“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论·非鞅篇》)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实行盐铁专营政策,设盐官三十六个、铁官四十八个,专管盐铁专营事务,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力,有力地支持了对匈奴的战争。汉昭帝时又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已为大家所熟知。检视春秋至两汉盐铁政策,唯西汉早期情况不甚清楚。《二年律令》则弥补了这一重要缺环,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盐铁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诸私为卤盐煮济汉,及有私盐井煮者,税之,县官取一,主取五。采银,租之,县官给橐,□十三斗为一石,□石县官税□□三斤。其□也,牢橐,石三钱。租其出金,税二钱。租卖穴者,十钱税一。采铁者,五税一,其鼓销以为成器,有(又)五税一。采铅者十税一。采金者,租之,人日十五分铢二。民私采丹者,租之,男子月六斤九两,女子四斤六两。”(金布律436~438)律文对盐、铁等五种私营工矿业税收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人贩卖北方卤盐到汉水流域及开采井盐者按照“县官取一,主取五”的比例征收;开采银矿者视官府提供的鼓风工具橐及自备橐两种不同情况而定,冶炼出成品银者每金税二钱,出卖银矿穴者十税一;开采铁矿者五税一的比例征收铁税,矿主又将铁矿石冶炼、加工为器物,再按“五税一”比例征收;开采铅矿者十税一;开采金矿者按雇佣人工每人每日十五分铢二的标准定额收税;开采朱砂矿者按男子每月六斤九两、女子每月四斤六两的标准定额收税。
这些情况说明西汉初期国家对煮盐、冶铁等经济领域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允许民间私营,官收其税,这对促进当时工矿业的开发、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等有着积极作用。而“文、景时期,‘弛山泽之禁’、‘纵民冶铁、煮盐’对山林川泽资源进一步开放经营,当是汉初工矿业政策的沿袭和拓展。”
3.市税
市税在战国时即已有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载:“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钜于长安。”西汉初年,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商品交易日益频繁。但此时市税如何征收,未见文献记录,而《二年律令》在这方面却有一些规定:
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贾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诸诈绐人以有取,及有贩卖贸买而诈绐人,皆坐臧(赃)与盗同法,罪耐以下,有(又)迁之。有能捕若诇吏,捕得一人,为除戍二岁;欲除它人者,许之。(市律260~262)
上引律文大意为:商贩必须如实向官府申报市税,如果隐瞒不交,就按偷盗相应数量的财物的罪行论处,官府没收其所贩卖的货物及货款,并剥夺其在“列市”的经营权。列长、伍人对市贩隐瞒市税不予告发者,分别罚金一斤。负责收税的啬夫、吏主失职,分别罚金二两。市贩在买卖过程中,凡以欺诈他人而不当得利者,与盗同法,判处“耐”以下刑罚,还要流放外地。若能捕获或告发逃避市税者,捕获一人,免除兵役二年,若立功者希望免除其他人的兵役也可以。
上文虽未明言市税的具体税率,但从律文中近乎严酷的规定中我们不难看出其税率是相当高的。这在传世典籍中可以找到证据,《汉书·食货志》载:“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正是商贩们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
第二节尹湾汉简所见上计制度
上计制度是我国古代中央政府考述地方治绩的一项重要制度,起源颇早。《周礼·天官》载:“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以知民财、器械之数,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数,以知山林川泽之数,以遂群吏之征令。”又载:“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王安石注:“受其会者,受其一岁功事财用之计。”可见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由朝廷主持的定期上计制度,以便了解国家财用情况。战国时期,上计制度进一步推广。《吕氏春秋·知度篇》载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于(赵)襄子。”《韩非子·外储说》载魏文候时西门豹为邺令,“期年上计”《新序·杂事篇》又载魏文候时“东阳上计,钱布十倍。”以上情况说明战国时赵、魏等国都曾普遍推行上计制度。
一.尹湾汉牍所见汉代上计制度及其政策导向
秦汉时期,上计制度进一步完善。其主要做法是:每年秋冬季节,各县将其所辖区域的人口、土地、财务的增减变动情况后上报至郡,各郡再将其所辖县级行政区域的情况汇总后上报朝廷,接受相关吏员的审计。朝廷亦借此以考核县、郡各级官吏的政绩,决定对他们的奖惩,并了解全国人口、土地及社会财富的变化情况动。
《续汉书·百官志》载:县、邑、道每年“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刘昭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可见“集簿”乃是上计制度的最重要文件。这是史籍所见有关汉代上计项目的最完整材料,惜乎其文过于简略,后人无法得知上计文书究竟如何编制,有哪些具体内容。1993年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一件木牍使我们有机会一睹汉代上计文书的实物。该木牍正背面均有字,正面自题“集簿”二字。这一“集簿”在看似平实的各种统计数据中有几处竭力突出了郡守政绩,以期获得朝廷的褒奖,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一制度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某些导向。
“集簿”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郡所辖户籍数及其变动: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十九。其户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有卅十九万七千三百卌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
【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八升,率口八斗八升有奇。
《汉书·宣帝纪》载,地节二年冬十月诏曰:“流民归还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对那些招揽流民有功的地方官员,中央还给子奖励。如宣帝地节二年春二月诏曰:“今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其秩成中一千石,赐爵关内侯。”上文中“获流”即郡级政府安辑流民,重新登记户口的数量。“集簿”中东海郡特意汇报“获流”一千六百余户,四万二千余口,反映了西汉政府对流民问题的重视。文中“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显然包括“获流”户在内,而“用谷”若干升则可能与安置这些流民过程中的贷种、贷食有关。
2.耕地与播种面积及其变动:
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人,如前。【侯】国、邑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万百卅十三,万九千□□□长生。□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八】十□顷,种宿麦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
春种树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四亩,多前四万六千三百廿亩。
文中“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是当年东海郡耕地总面积。将耕地面积作为上计制度的一个重要项目,反映了西汉政府将农业作为天下根本一贯政策。文中还特意提到种宿麦若干顷,“多前”(较上一年增长)若干顷,“春种树”(此处“种树”系泛指播种农作物而言,非特指植树),“多前”若干亩。说明春秋两季播种面积的增加是地方各级官员最值得夸耀的成绩。
3.人口数量及其性别与年龄构成:
【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十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十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万六千四百五十九。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
由于连年战争,汉初人口锐减,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汉代统治者就竭力鼓励增殖人口。早在惠帝时,就立法促使女子早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提倡女子结婚,甚至早婚,是为了“繁息”人口。因此人口状况如何,也是评定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方面。例如《汉书·循史传》中的六位循史,就有三位有“户口岁增”、“户口增倍”之类的评语。在这种情况下,东海郡太守不能不注意本郡男女人口的比例问题。有学者指出“《集簿》特意说明东海郡女子人口已在逐年增多,即考虑到了该郡日后人口增长的问题。”从文帝时期开始,西汉政府在养老方面为八十岁以上老人制定了不少优待措施。《汉书·贾山传》又载当时“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是为免除高龄者算赋。《汉书·贡禹传》载元帝时“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开始直到汉末,一直免除七岁以下儿童的口赋。“集簿”中特意汇总了八十岁以上及七岁以下人口数量,可能就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
4.钱谷等财务收支情况:
一岁诸钱入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一岁诸钱出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一。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率升出卌一万二千五八十一石四斗□□升。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某年东海郡钱、谷两种主要财政收入情况与支出情况相比均有较多盈余。
尹湾汉简《集簿》是郡级上计文书,而2004年安徽省天长市安乐镇纪庄村所出汉代木牍中又出现了县级上计文书。纪庄一号木牍正面自题“户口簿”,分别记载了西汉临淮郡东阳县户与口的总计数字和所属六个乡户与口的分计数字,各乡户口的分计数字相加与县的户口总数完全相同,说明这项统计是严密的。其中“户凡九千一百六十九,少前;口四万九百七十,少前”等用语与尹湾汉牍十分类似,说的是此年东阳县的户、口数皆较前有所减少。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尹湾木牍《集簿》中的数据可能存在地方官为了争取褒奖而夸大政绩的问题,而此件文书明确记载户、口增长“少前”,或可部分纠正我们对汉代上计文书准确性的看法。
二.其它秦汉简牍所见秦汉上计制度的运行
除了前述尹湾汉牍“集簿”及纪庄汉牍“户口簿”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它简牍材料中了解到一些有关秦汉上计制度的运行细节。
1.内史在上计制度中的作用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载:
入禾稼、刍槀,辄为廥籍,上內史。(仓律28)
至计而上廥籍内史。(效律176)
稻后禾孰(熟),计稻后年。已获上数,别粲、穤、秙、稻。别粲、穤之襄,岁异积之,勿增积,以给客,到十月牒书数,上内史。(仓律36)
内史掌财务。《史记·赵世家》记载徐越主张“节财俭用,察度功德”,赵烈侯任以为内史。由上引三枚简文可知,每年十月,地方官要把禾稼、刍槀等入仓的情况分门别类编成“廥籍”(仓库账簿)送到内史审计。可见有秦一代内史在上计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
2.秦代“计断”时间
仓律36号简称每年十月各县要将粮食入仓的数量上报内史。这与秦代“计断”的时间(即上计数据的截止日期)有关。《秦律十八种》载:“官相输者,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受者以入计之。八月、九月中其有输,计其输所远近,不能逮其输所之计,□□□□□□□移计其后年,计毋相缪。”(金布律71)律文规定官府之间相互输送物品,应以文书通知其出帐的年份,接受者按收到的时间记账。如在八月、九月中输送,估计所运处所的距离,不能赶上所运处所的结账,改计入下一年账内,双方帐目不要矛盾。这是因为九月为秦代“计断”时间。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所谓“计断九月”,即每年度的各项统计数字至九月底截止。因为秦以十月为岁首,九月底也就是岁终。
《秦律十八种》又载:“都官岁上出器求补者数,上会九月内史。”(内史杂律187)律文规定都官须在每年九月向内史上报已出器物及要求补充器物的数量。由此看来,“计断九月”当为秦朝定制。
3.汉代边郡军事系统的审计制度
前引尹湾汉牍“集簿”中提到“都尉一人,丞一人,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五人,凡十二人。”这一统计数据中包括属于军事系统都尉府,可见汉代的上计也涉及到军事系统。我们也在居延汉简中发现了一些侯官与都尉府之间与上计有关的公文:
 □长丞拘校,必得事实。牒别言,与计偕,如律令,敢告卒人。……以来。 □长丞拘校,必得事实。牒别言,与计偕,如律令,敢告卒人。……以来。
掾定、属云、延寿、书佐德(T53.33A、B)
此枚简已残断,从行文口气上来看,似为下行文书。该文书要求下级机构官吏对某种费用进行详细核对,查清事实后与“计(集)簿”一起上报。居延汉简中也有下级机构的上报公文:
阳朔三年九月癸亥朔壬午,甲渠障守候尉顺敢言之。府书:“移《赋钱出入簿》与计偕。”谨移应书一编,敢言之。
尉史昌(35.8A、B)
上录文书属于上行文书中的“应书”,即甲渠障按照都尉府关于“移《赋钱出入簿》与计偕”的文书要求,上报了一组“计(集)簿”之类的文书,同时还要附上《赋钱出入簿》以备都尉府验核。可惜这部简册已经散失,“集簿”无法找到,但《赋钱出入簿》之类的文书在居延汉简中为数不少:
元寿六月受库钱财出入簿(286.28)
甲渠侯官阳朔二年正月尽三月钱出入簿(281.11)
以上两枚简是“簿检”,即文书的标题简。其下内容当是类似于下文的东西:
入秋赋钱千二百元凤三年九月乙卯□ (280.25) (280.25)
入钱九百五十一五月□□□博受尉史徐□ (284.19) (284.19)
出钱三千七月丁巳令史临付士 (300.11) (300.11)
出钱六百其六百付侯长宣八月己巳……侯长王□ (141.8) (141.8)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载:“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仓律37号)太仓为京师府库。该仓律规定各县应于每年送达上计文书时还要向向太仓上报当年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以便都官审计验核,可见秦代上计制度之严格。汉承秦制,居延汉简中大量以侯官(部)为单位的“吏卒廪名籍”、“卒家属廪名籍”等就可能兼有应对都尉府审计的作用。试举例如下:
第廿三部十二月廪名廿二人
第廿三卒李婴第廿三卒苏光第廿三卒郭亥第廿四卒成定第廿四卒张猛第廿四卒石关第廿五卒鲁建第廿五卒韩意第廿五卒张肩第廿六卒寿安第廿六卒韩非人第廿六卒张建第廿七卒张颈第廿七卒石赐第廿八卒羊实第廿八卒马广第廿八卒曾相憙第廿九卒张卷第廿九卒褒赣第廿九卒左漠價第卅卒钟昌第卅卒高关”(24.2号)
上文书于一块长23.9厘米,宽2.3厘米的木牍之上,是甲渠候官所属第廿三部二十二名戍卒某年十二月领取口粮的名籍,其文仅列举廪食人员名单,较为简略。1996年谢桂华复原出一册廪名籍,简册有残缺,但结构大体完整,内容较为详细,抄录如下:
建平五年十二月官吏卒廪名籍
令史田忠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
右史四人用粟十三石三斗三升少
障卒张竟盐三升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障卒李就盐三升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障卒史赐盐三升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障卒□□盐三升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
……
右障卒九人用盐二斗七升用粟卅石
执胡隧卒张平盐三升十二月食……
……[盐]三升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 十一月庚申自取
……
右省卒四人用盐一斗二升用粟十三石三斗三升少
凡吏卒十七人凡用盐三斗九升用粟五十六石六斗六升大”
上录册书是哀帝建平五年十二月某障吏卒廪名籍,其内容可分为五部分:一、簿检(标题);二、吏廪名籍,包括令史田忠等四人;三、障卒廪名籍,包括李就等九人;四、省卒名籍,包括张平等四人;五、用粮食及食盐数量合计。其用途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是吏卒口粮的发放记录,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作为上级审核吏卒口粮的原始记录。
前引仓律37号规定各县应于每年送达上计文书时还要向太仓上报当年除了口粮以外的“它费”(其他费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就有将马牛草料列为上计的项目的条文,明显可归入“它费”。其文为:“官各以二尺牒疏书一岁马、牛它物用槀数,余见刍槀数,上内史,恒会八月望。”(田律256号)律文要求地方官于每年八月十五日向内史上报一年内马牛等牲畜所用草料及剩余草料数量。居延汉简中屡见“茭出入簿”即是此类:
不侵部建昭五年正月余茭出入簿(142.8)
吞远部建平元年正月官茭出入簿(4.10)
《说文·艸部》:“茭,干刍。”许锴系传:“刈取以用曰刍,故曰‘生刍一束’,干之曰茭,故《尚书》曰‘峙乃刍茭’。”上引简文中的“茭”应即刍槀,马牛草料。“茭出入簿”也可能用于审计。
第三节居延汉简所见经济契约与经济纠纷
经济契约起源颇早。西周时期铭文《曶鼎铭》就是一件典型的奴婢买卖契约,曶以“匹马束丝”交换五名奴隶,效父做中介人。西周金文中还有牛马、兵器等商品的买卖契约。可见买卖契约的出现最迟不晚于西周时期。《管子·轻重乙》载:“君直币之轻重以决其数,使无券契之责,则积藏囷窌之粟皆归于君矣。”《墨子·号令》载:“收粟米、布帛、钱金,出内畜产,皆为平直其贾,与主券人书之。事已,皆各以其贾倍偿之。”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契约一类文书已经广泛运用于各种经济活动中。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契约所涉及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其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也更趋规范。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中有许多买卖契约,为我们了解当时的贳买、贳卖等经济活动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
一.券书的订立
西北边塞戍卒的衣物大体上是由戍卒原籍的地方政府配给的,不足时由戍卒家属供给。而军官因享有俸禄,衣物是需要自理的。但由于边塞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物产也不丰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便成了紧俏的物品。我们从居延汉简及敦煌汉简中可以看到当时戍卒之间、戍卒与军吏之间、戍卒与百姓之间买卖衣物、布料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若买方一时无法付款,则需要订立券书(契约)。举例如下:
建昭二年闰月丙戌,甲渠令史董子方贳买鄣卒□威裘一领,直七百五十,约至春钱毕已。旁人杜君隽。”(26.1)
《说文·贝部》:“贳,贷也。”这一券书内容为建昭二年闰月丙戌日,甲渠令史董子方赊买戍卒□威裘衣一件,价钱为七百五十,约定在春前支付完毕,有杜君隽作中人。这件契约文书左侧有三道刻痕(下文所列券书多数可见刻画痕迹),是汉简“券书”的典型形式,“券书”有“左券”、“右券”之别,通常是出物者执左券,受入者执右券。
七月十日,鄣卒张中功贳买皁布章单衣一领,直三百五十三,堠史张君长所,钱约至十二月尽毕已。旁人临桐史解子房知券□。(262.29)
这一券书内容为某年七月十日,戍卒张中功在堠史张君长处所赊买某人黑色单衣一件,价钱为三百五十,约定在十二月底支付完毕,临桐史解子房作中人。文中没有说明张中功所买单衣的原主人为谁,但这件券书的持有者毫无疑问就是此人。
元康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壬寅,居延临仁里耐长卿贳买上党潞县直里常寿字长孙青復绔一两,直五百五十,约至春钱毕已。姚子方 (EPT57。72) (EPT57。72)
这一券书内容为元康二年十一月壬寅日,居延临仁里居民耐长卿赊买上党璐县直里常寿(字长孙,可能是来居延的戍卒)青色夹裤一条,价钱为五百五十,约定在开春前支付完毕。有姚子方作中人。
上引三件券书的构成要素大致为:1,买卖交易时间,2,交易双方身份(籍贯)姓名,但券书持有者的姓名有时可以省略,3,衣物的价格,4,交易地点,有时可省略,5,约定的付款期限,6,中人(知见人)姓名及其身份。以上六大要素已基本具备后世契约的全部内容。
二.债务的清偿
敦煌汉简中有这样一件券书:
元平元年七月庚子,禽寇卒冯时卖橐络六枚杨卿所,约至八月十日与时小麦七石六斗,过月十五日,以日斗计。盖卿任。(1449A)
这一券书内容与前述三件券书大致类似。内容为元平元年七月庚子日,禽寇燧戍卒冯时在杨卿住所出卖橐络(《说文》:“络,絮也”,则橐络或为某种丝织品)六枚给某人,价钱为小麦七石六斗,定于八月十日前交付,若超过当月十五日未付,按超出一日加一斗小麦作为违约金。担保人为盖卿(任,担保。《说文·人部》:“符也。”段玉裁注:“如今言保举是也。”《汉书·赵充国传》:“臣任其计必可用也。”颜师古注:“任,保也。”)。这一契约中首次出现了违约赔偿的概念,令人瞩目。但是违约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这枚简的背面,还有如下三字:
麹小麦(1449B)
我们认为这是买家给付小麦的记录,表明货款已按照契约中的约定按时交付。类似的情况在敦煌汉简中还有一例:
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广汉县廾郑里男子节宽 卖布袍一陵胡隧长张仲孙所,贾钱千三百,约至正月□□任者□□□□□□□(1708A) 卖布袍一陵胡隧长张仲孙所,贾钱千三百,约至正月□□任者□□□□□□□(1708A)
这一券书内容为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广汉县廾郑里男子节宽在陵胡隧长张仲孙住所“ 卖”(未详何义)给某人布袍一件,价钱为一千三百钱,定于正月前交付。有□□为担保人姓名(漫漶不清)。其背面还有一行字: 卖”(未详何义)给某人布袍一件,价钱为一千三百钱,定于正月前交付。有□□为担保人姓名(漫漶不清)。其背面还有一行字:
正月责付□□十时在旁,侯史长子仲、戍卒杜忠知券□,沽旁二斗。(1708B)
上文漫漶不清之处虽多,但其中“正月责付”为买家在正月按其付款的含义还是很明显的。付款时也有担保人侯史长子仲、戍卒杜忠在场作为见证,买家还沽酒二斗相谢。至此债务已清偿,交易结束。由此我们知道债务清偿后在原契约背面写上清偿字据可能是当时通行的做法,还可知道汉代就有诂酒酬谢担保人的风俗。
三.债务纠纷的出现及其解决机制
(1)申诉
如果赊欠方没有履行合约,一般由卖主向主管官吏提出申诉。这样的法律文书在居延汉简中较为常见。如:
灭虏燧戍卒梁国蒙东阳里公乘左咸年卅六,自言责故乐哉燧长张中实皂练一匹,直千二百。今中实见为甲渠令史。”(35.6)
吞远燧卒夏收自言责代胡燧长张赦之,赦之买收缣一丈,直钱三百六十。”(217.15+217.19)
司马令史腾谭自言责甲渠燧长鲍小叔负谭食粟三石,今见为甲渠燧长。”(EPT51:70)
□既自言五月中行道贳卖皂复袍一领,直千八百;□卖缣长袍一领,直二千;皂绔一两,直千一百;皂□,直七百五十。凡直六千四百。居延平里男子唐子平所。”(206.28)
第廿五燧卒唐憙自言贳卖白紬襦一领,直千五百,交钱五百。凡并直二千。”(EPT51:302)
上引五条简文均为“自言书”(自诉状),是“爰书”(法律文书)的一种,均有残缺。文中的“责”字为“索取”之意,五位原告各自向官府告发债务产生的原因及债务数量,并提供被告身份信息,要求被告偿还。可见此类纠纷产生以后多数债权人还是选择通过法律渠道加以解决。
(2)验问
有关吏员在接到这样的自诉状之后,要及时报告上级。这在居延汉简的一些行政文书中有所反映:
甘露二年五月己丑朔戊戌,候长寿敢言之:谨移“戍卒自言贳卖财物吏民所”,定一编。敢言之。(EPT53:25)
 □丑朔甲寅,居延库守丞庆敢言之:缮治“车卒甯朝自言贳卖衣财物客民、卒所”,各如牒。律……□辞(首唯?)官移书人在所在所以,次唯府令甲渠收责,得钱与朝。敢言之。 □丑朔甲寅,居延库守丞庆敢言之:缮治“车卒甯朝自言贳卖衣财物客民、卒所”,各如牒。律……□辞(首唯?)官移书人在所在所以,次唯府令甲渠收责,得钱与朝。敢言之。
掾破胡、佐护充光(EPT58:45AB)
甘露三年十一月辛巳朔己酉,临木候长福敢言之:谨移“戍卒吕异众等行道贳卖衣财物直钱”如牒。唯官移书令觻得泺涫收责。敢言之。(EPT53:186)
元康四年六月丁巳朔庚申,左前候长禹敢言之:谨移“戍卒贳卖衣财物爰书名籍”一编,敢言之。(10.34A)
上引第一条简文为侯长寿收到戍卒自诉状后向上级呈报的文件;第二条简文为代理居延库丞庆上级在收到戍卒甯朝自诉状后向都尉府呈报的文件,请求都尉府发文承债人所在机构,追回甯朝应得欠款;第三条为临木候长福收到戍卒吕异众自诉状后向侯官呈报的文件,请求侯官追回吕异众应得欠款;第四条为左前候长禹收到戍卒自诉状后向上级呈报的文件,背面记有“印曰蔺禹,六月壬戌金关卒延寿以来。候史充国”,为侯官收文记录。四个文件中都将自诉状作为附件。
上级机关收到上引文件之后会要求被告所在机构传唤被告人验问,验问后下级机构还要上报相应的法律文书。见下例:
神爵二年六月乙亥朔丙申,令史□敢言之:谨移“吏负卒赀自证已毕爰书”一编。敢言之。(EPT56:275)
所谓“自证已毕爰书”就是相关机构验问当事人后所作的证言材料。当如下例:
“贷甲渠候史张广德钱二千,责不可得,书到验问,审如猛言,为收责。”言:谨验问广德,对曰:“迺元康四年四月中,广德从西河虎猛都里赵武取谷钱千九百五十,约至秋予。”(EPT59:8)
简文所见一名为“猛”的人自诉借给甲渠候史张广德二千钱,无法要回。上级机关要求相关机构验问张广德,若情况符实,则要帮助猛讨还债务。相关机构依法验问,张广德交代他在元康四年四月从西河郡虎猛都里赵武处借得谷钱一千九百五十,约定于当年秋天偿还给赵武。此案较为复杂,按照张广德的说法,他本来是欠赵武谷钱一千九百五十,但为何猛成为债权人?欠款也变成二千?因上下文缺失,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我们推测这有可能是“三角债”。居延汉简中还有一条类似的材料。
“责不可得,书到验问,审负知君钱,白报。”谨验问,当辞曰:“乃十一月中从知君”(EPT59:13)
此条材料也无上下文,但其案情大致可知:一名为“知君”的人要求一名为“当”的人归还欠款,上级机关要求查清是否确实,相关机构依法验问,“当”交代了债务产生的缘由。
(3)清偿
事实清楚之后,相关机构就可依法判决。但在很多情况下,基层机构在验问后即可协调解决此类纠纷。试看下例:
“ 自言责士吏孙猛脂钱百廿”。谨验问,士吏孙猛辞服负。已收得猛钱百廿。(EPT52:21) 自言责士吏孙猛脂钱百廿”。谨验问,士吏孙猛辞服负。已收得猛钱百廿。(EPT52:21)
简文为某人要求讨还士吏孙猛欠他的脂钱一百二十钱,上级机关要求查清事实,基层机构依法验问,孙猛供认不讳,并很快交上欠款,再由基层机构转交给某人。还有二例:
临之燧长王君房负季子六百六十。六百已入,少六十。(220.16)
 徐充国十二月……积三月奉钱千八百。出钱三百一十偿第卅燧卒王弘;出钱千一十,偿第卅三燧卒陈第宗钱;出钱八,就十月尽十二月,月二钱七分。凡出钱千三百廿八,今余钱四百七十二。(EPT51:214) 徐充国十二月……积三月奉钱千八百。出钱三百一十偿第卅燧卒王弘;出钱千一十,偿第卅三燧卒陈第宗钱;出钱八,就十月尽十二月,月二钱七分。凡出钱千三百廿八,今余钱四百七十二。(EPT51:214)
上引材料均为“簿籍”类文书,类似于现在的会计账目。第一条大意为:临之燧长王君房欠季子六百六十钱,其中六百钱已入账,还有六十钱未还。第二条大意为:徐充国从某年十二月开始的三个月应得俸禄共一千八百钱,在偿还王弘三百一十钱、陈第宗一千零一十钱、就(僦)钱八钱等三笔债务后还剩余四百七十二钱。”
如果承债人一时无法凑齐还款数目,还可以从俸禄中扣除。见下例:
阳朔元年七月戊午,当曲燧长谭敢言之:负故止害燧长宁常交钱六百,愿以七月奉钱六百偿常,以印为信,敢言之。(EPT52:88A)
上引材料类似于现在的“还款保证书”。大意为:阳朔元年七月戊午日,当曲燧长谭向上级保证他愿意从七月奉钱中偿还所欠原止害燧长宁常交钱六百钱,并以私印为信。依据这样的保证书,基层机构就可以从承债人的俸禄中扣除欠款。
如果一些经济纠纷基层机构无法调节,则由上级机关审理。审理之后,交由基层机构执行。见以下二例:
第廿三候长赵倗责居延骑士常池马钱九千五百,移居延收责。重。一事一封。十一月壬申,令史同奏封。(35.4)
不侵守候长成赦之责广地燧长□丰钱八百,移广地候官。一事一封。八月壬子,尉史并封。(58.11)
上文所见上级机关在审理完两起债务案件之后,分别交给居延、广地等基层机构执行。这种情况下相关机构还要编制“戍卒贳卖衣财物名籍”(EPT59:47)、“卒贳卖名籍”(EPT56:263)”之类的文件,通过基层机构从债务人俸禄中扣除欠款。可参下例:
当欲隧卒宾德成卖布一匹,直钱三百五十,临要隧长当责,尽四月奉;察適隧卒王未央卖絣一匹,三百七十,当责察適隧长,尽四月奉;恿敢卒狐卖练一匹,贾钱四百九十,又布钱百卅四,凡直六百廿四,当责造史诛子病□尽四月。(838A)
上引文书记录了当欲隧卒宾德成、察適隧卒王未央、恿敢卒狐分别卖出布帛若干,价值若干,“当责”者(即承债人。《字汇·田部》:“当,承也”;责,通“债”。《正字通·贝部》:“责,逋财也,俗作债。”)分别是临要隧长、察適隧长、造史某某,各以四月前俸禄偿还。说明这些债务是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解决的,由隧以上机构直接从承债人的俸禄中扣除,交给债权人。
债务清偿之后,相关机构还要上报相应的文书证明承债人已经还债。如:
 □二年二月丁酉朔丁卯,甲渠鄣候护敢言之:府书曰:“治渠卒贾……□自言责燧长孙宗等衣物钱”凡八牒,直钱五千一百,谨收得。(EPT52:110) □二年二月丁酉朔丁卯,甲渠鄣候护敢言之:府书曰:“治渠卒贾……□自言责燧长孙宗等衣物钱”凡八牒,直钱五千一百,谨收得。(EPT52:110)
察微燧长卑赦之,负夏幸钱五百卅、负吕昌氏钱二百、负吞北卒□□□□五百五十,皆□□,皆已入毕。前所移籍当去。(EPT51:77)
上引第一条为都尉府要求甲渠鄣帮助治渠卒贾讨回燧长孙宗所欠衣物钱等八起经济纠纷事件后,给上级部门所作的汇报,简文显示这些欠款已经追回。第二条为某机构已追回察微燧长卑赦之所欠债务,故要求先前呈报的“自证爰书”、“卒贳卖名籍”等不再执行。
(4)无法清偿债务的刑事责任
以上所述可见当时边塞屯戍系统在处理债务等经济纠纷方面有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但这一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债务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承债人不履行或者无法履行合约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居延新简中有一条材料:
临之隧卒魏郡内黄宜民里尹宗责故临之隧长薛忘得铁斗一,直九十、尺二寸刀一,直卅、缇绩一,直廿五,凡直百卌五。同隧卒魏郡内黄城南里吴故责故临之隧长薛忘得三石布囊一、曼索一具,皆?忘得,不可得。忘得见为复作。(EPT59:7)
上文中的薛忘得曾任临之隧长,他贳买戍卒尹宗价值一百四十钱的物品,又借用了戍卒吴故的一些物品,尚未归还,因而受到了这两个戍卒的指控。但薛忘得正在服刑,看来债务的清偿存在一定麻烦。
居延汉简中还有承债人因贫困无力偿还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事例:
 年六月己已朔丁丑,甲渠候破胡以私印行事敢言之:谨移“戍卒朱宽等五人贳卖候史郑武所,贫毋以偿,坐诈□□名籍”一编,敢言之。(EPT51:199) 年六月己已朔丁丑,甲渠候破胡以私印行事敢言之:谨移“戍卒朱宽等五人贳卖候史郑武所,贫毋以偿,坐诈□□名籍”一编,敢言之。(EPT51:199)
上文显示戍卒朱宽等五人在候史郑武处贳卖物品后,因为贫困无法偿还而涉嫌欺诈。这样的事例在边郡地区可能屡有发生。
四.官府禁止高价贳卖活动
前文所见贳买贳卖活动是受到官府保护的,但官方对于高价贳卖活动则持有不同态度。见下例:
二月戊寅张掖太守福、库丞承熹兼行丞事敢告张掖农都尉、护田校尉府卒人:谓县律曰:“臧它物非钱者以十月平贾计。”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吏不禁止,浸益多,又不以时验问。”(4.1)
上引材料是张掖太守和库丞(兼行丞事)向张掖农都尉、护田校尉发出的下行文书,文书认为戍田卒将即官府发给的衣物高价贳卖给当地贫困居民,而基层官吏不加以禁止,又不按时过问这样的事情,以致这种现象愈演愈烈。文书要求对有关贳卖物品按十月份平贾进行估算,若高出十月平价则不允许。下文就是一条例证:
第五隧卒马赦贳卖□□袍,县絮装,直千二百五十,第六隧长王常利所。今比平,予赦钱六百。(EPT56:17)
上文显示戍卒马赦在王常利住所以一千二百五十钱的价钱贳卖给某人衣物,但按照十月平价来看,这一价格偏高,所以最后只给马赦六百钱了事。
其它汉简所见契约文书还有很多,著名的有江陵凤凰山10号汉牍“中舨(贩)共侍约”(为合伙经商契约)、居延汉简“乐奴买地契约”(577·4)、尹湾汉简“师君兄贷师子夏”借贷契约等,而居延汉简《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则涉及到因雇佣契约而引起的债务纠纷,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
第四节居延汉简中的物价
物价问题是秦汉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一向受到学界关注。1928年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一书将传世典籍中有关西汉一朝的物价史料汇集起来,列举了食粮、金、银等11类商品的价格情况。其后,陈啸江、马非百、瞿宣颖等人也对文献所载的秦汉物价资料作过进一步梳理,但收获有限。居延汉简的发现则为研究汉代物价提供了大量可靠资料。1934年劳榦《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一文对居延汉简所涉及的西汉中晚期的物价资料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研究。其后,陈直《汉代的米谷价及内郡边郡物价情况》、《居延的物价》等文进一步考察了居延汉简中的物价,并以之与内地的物价相比较。1980年代以后,利用汉简资料进行物价问题研究的成果更是层出不穷,其中以丁邦友、徐扬杰、刘金华等人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下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两汉河西地区的物价状况做一大致梳理。
一.地价
两汉的土地价格因时代先后、肥瘠不同,差距很大。《汉书·东方朔传》载:“酆鄗之间,号为土膏,其价亩一金。”《后汉书·杜笃传》载:“厥土之膏,亩价一金。”其中亩价高达一金,这是内郡膏腴之地的市价。传世汉代地券《汉樊利家买地铅券》载:“田五亩,亩三千,并直万五千。”《汉王未卿买地券》载:“亩价钱三千一百,并直九千三百。”其中亩价均在三千钱左右。《汉书·李广传》载汉武帝时,丞相李蔡“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其中亩价在一千三百钱左右。以上是内郡中等土地的价格。著名的“礼忠简”(37·35)及“徐宗简”(24·1AB)均为汉宣帝时期的遗物,其中有觻得县及居延县(均属张掖郡)地价资料,前者载侯长礼忠有“田五顷,五万。”后者载燧长徐宗有“田五十亩,直五千。”其中亩价均为一百钱,十分低廉,这与边塞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有很大关系。
两汉时期的宅价也因地域差异、建筑物大小好坏等因素而有很大不同。东汉后期的《郑子真宅舍残碑》所载宅价格大致在一万至七万以之间,最贵者达到百万。四川郫县出土的东汉残碑所载宅价在五千至十七万之间。敦煌汉简668载:“买宅三万在里究贾明不私欲戴副阳□□□□□ ”此简已残,但“买宅三万”清晰可断,其价格与内郡相当。而前述“礼忠简”及“徐宗简”中宅价分别为一万及三千钱,相对内郡来讲较为低廉。 ”此简已残,但“买宅三万”清晰可断,其价格与内郡相当。而前述“礼忠简”及“徐宗简”中宅价分别为一万及三千钱,相对内郡来讲较为低廉。
二.粮价
居延汉简所见粟价大致在每石一百钱至一百五十钱左右。EPT51:105载:“粱粟二石,直二百,一百钱一石。”EPT5:87载:“出粟二石七斗,直钱二百八十。”其中每石折合约一百零四钱。214·4载:“出钱一百一十,籴黍粟一石,石百五。”与前述价格相近。167·2载:“粟一石,直百一十。”EPT51:71载:“出钱百一十,黍粟一石,第九吏孙卿籴。今五斗,直五十五。”EPT56:104载:“粱粟二石,直二百廿。”以上三例所见粟价均为每石一百一十钱。EPT52:327载:“出钱百卌,□□籴粟一石。”36·7载:“黍米二斗,直钱卅。”折合每石一百五十钱。糜价也大致在这一范围。26·9A载:“糜三石,直三百六十。”即糜一石值一百二十钱。EPT57:69A载:“眉一石,直百五十。”疑其中“眉”即糜。
低于上述价格区间的有:303·3载:“董次入谷六十六石,直钱二千三百一十。”每石折合三十五钱,这是居延汉简中粮价最低记录。19·26载::“入谷六十石六斗六升大,直二千一百廿三。”其价约四十钱一石,比前条所记稍高。EPT5:134载:“出粟二石二斗,直钱百七十 ;出粟二石四斗,直钱百九十 ;出粟二石四斗,直钱百九十 。”其中每石折合不到八十钱。敦煌汉简361载:“入粟三石三斗,直泉二百六十四。”其中每石折合八十钱。276·15载:“出钱四千三百卅五,籴得粟五十一石,石八十五。” 。”其中每石折合不到八十钱。敦煌汉简361载:“入粟三石三斗,直泉二百六十四。”其中每石折合八十钱。276·15载:“出钱四千三百卅五,籴得粟五十一石,石八十五。”
高于上述价格区间的有:26·9A载:“胜之已得粟二石,直三百九十。”折合每石一百九十五钱。EPT51:223载:“出百六十八,籴米七斗。”折合每石二百四十钱。332·11载:“麦五斗,凡直百九十二。”折合每石三百八十四钱。EPP22:325A载:“天子将兵在天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今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石千二百。”价格畸高。
以上所述粮价的波动当与不同时期经济及军事形势有关。但从某一特定时期来看,各种粮食之间的比价并无明显差异。214·4载:“出钱二百廿,粱粟二石,石百一十;出钱二百一十,黍粟二石,石百五;出钱百一十,大麦一石,石百一十。”其中粱粟、黍粟、大麦三种粮食比价接近。王莽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簿册载:“粱米八斗,直百六十;即米三石,直四百五十。”其中梁米价折合每石二百钱,即米价每石折合一百五十钱,疑“即米”或为原米,故价格略低。
三.肉价
居延汉简所见肉价大致在每斤三钱至七钱之间。173·8A载:“肉十斤,直卅。”折合每斤三钱。EPT51:235A载:“肉卅斤,直百廿。”折合每斤四钱。286·19A载:“凡肉五百卌一斤,直二千一百六十四。”折合每斤四钱。悬泉汉简0213②:106载:“出钱六十,买肉十斤,斤六钱。”折合每斤六钱。EPS4T2:15载“母纫中君肉十五斤,钱百”,“徐长卿肉十五斤,钱百”,“张子游肉十五斤,钱百。”折合每斤约六点七钱。乙附29A载:“肉百斤,直七百。”折合每斤七钱。
居延汉简中肉价也有以谷物折算的。EPT40:76A《宜农辟取肉名》记录尚子春等二十人各自取肉“十斤,直二斛”,并多有“清黍”(即以黍偿付)等记录,说明其中肉价为每斤值黍二斗。该名籍还记录了其他人各自取头、脾、肠、脯、肝、项、应肋等,价格在一斛至五斛之间。相同情况见于EPT43:33AB及EPT43:37AB,其中肉价也为每斤值谷二斗。EPE22:457A载:“肉五十斤,直七石五斗。”则每斤值谷一点五斗。敦煌汉简309载:“肉亖十斤,直二石亖斗八升。”敦煌汉简310载:“肉二十斤,直一石二斗亖升。”折合每斤值谷六斗二升。以上所见“肉”不详为何种肉,但从《宜农辟取肉名》所记“凡肉百二十斤”的情况来看,当是一头猪的重量。
悬泉汉简所见传马死后,其骨肉可卖钱,其价格差异很大。0116②69载:建昭二年十月“出悬泉马五匹,病死,卖骨肉,直钱二千七百卌。”知此时一匹马骨肉价平均为五百四十八钱。II0114③:468A载“騩,乘,齿十八岁……病柳张,立死,卖骨肉临乐里孙安所,贾千四百。”这匹马骨肉所卖价钱达到一千四百钱。
悬泉汉简《元康四年鸡出入簿》载:“所置自买鸡三双,直钱二百卌,率双八十。”知当时鸡价平均为四十钱。又载:“正月尽十一月丁卯,置自买鸡十五双一枚,直钱千二百一十五。”则该年度所购三十一只鸡平均价格为三十九钱略多。EPT51:223:“出百八十,买鸡五只。”知鸡价每只三十六钱。以上所见鸡价波动不大。
居延汉简所见鱼价较为便宜。274·26A载:“出鱼卅枚,直百□。”“直百”后尚有缺字,依理推测30枚鱼所值当在100—200钱,因此这枚简所记鱼价当在1枚3.3—6.7钱之间。EPT65:33载:“并负掾鱼卅头,直谷三斗。”是一头鱼平均值谷一升。前文已指出居延地区谷价一般在一百至一百五十钱之间,则此处鱼价当在每头1—1.5钱之间。
居延汉简所见王莽时期的羊价波动较大。413·6A记:“出羊一头,大母,子程从君巨买,贾泉九百;出羊一头,大母,子程从君巨买,贾泉九百桼十五;出羊一头,大母,勒君兄买,贾泉千;出羊一头,大母,君巨去时与巨相用□伯通今子程买,贾泉千。”从简文中以“泉”代“钱”、以“桼”代“七”等特殊用字来看,上文所述当在王莽时期,其中羊价在九百钱至一千钱之间。但王莽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又载:“羊二,直五百。”折合一只羊价为二百五十钱,或是小羊。又EPT51:223载:“出二百五十,买羊一。”与前述价格一致。
四.马牛价
居延汉简所见马价多在在一匹四千钱至一万五千钱之间。前引“礼忠简”载:“用马五匹,直二万。”其中马价平均为四千钱。居延汉简229·1及229·2载汉成帝永始二年,甲渠收虏隧长赵宣借乘大昌里张宗雌性胡马追逐野橐驼,归途中胡马死亡,赵宣企图以所捕获野橐驼抵债,张宗不接受,最后有关部门责令赵宣赔付七千钱了事。敦煌汉简2011载:“律曰:‘畜产相贼杀,参分偿和。’令少仲出钱三千及死马骨肉付循,请平。”则这匹马的价格为四千五百钱或九千钱。悬泉汉简I0205②8:“传马死二匹,负一匹,直万五千,长、丞、掾、啬夫负二,佐负一。”其中规定若传马死亡相关吏员要担负各自的赔偿责任,传马死二匹,赔偿一匹,折价一万五千钱。206·10载:“马钱五千三百,己入千二百,付隧卒丽,定少四千一百。”35·4载:“第廿三候长赵傰责居延骑士常池马钱九千五百。”143·19载:“甲渠候长李长赣马钱五千五百。”可能都是一匹马的价格。
居延汉简所见牛价较马价为贱。“礼忠简”载:“服牛二,六千。”其中牛价三千钱一头,但同一简所载马价则为四千钱一匹。“徐宗简”载:“用牛二,直五千”其中牛价为二千五百钱一头,较前条所记价钱还低。EPT53:73:“□买肩水尉丞程卿牛一,直钱三千五百。”即牛一头价三千五百钱,也较马价便宜。
五.衣物价
两汉边塞吏卒常用衣物有袍(长衫)、襦(短上衣)、袴(裤子)等三类,袍类又有袍、袭(左衽袍)、裘(皮袍)、襌衣(单层袍)、襜褕(直裾单衣)等不同类型。
居延汉简中袍价一领值一千一百钱以上的情况较为多见。EPT59:31载:“买卒冯自为袍一领,直千一百。”EPT51:122载:“七月中贳卖缥复袍一领,直钱千一百。”EPT16:11载:“官袍一领,直钱千二百。”EPT59:555:“陈袭一领,直千二百五十。”EPT52:91B载:“袍,直千三百。”《居延汉简补编》C22载:“官袍一领,直千四百五十。”157·5A载:“责殄北石隧长王子恩官袍一领,直千五百。”206·28载:“贳卖皁复袍一领,直千八百;缣长袍一领,直二千。”EPT51:314载:“卖皁袍一领,直千九百。”69·1载:“贳买皁练复袍一领,贾钱二千五百。”居延汉简中也有袍价较贱的记录。49·10载:“买布复袍一领,直四百。”EPT56:152载:“布袍,钱四百五十。”EPT59:374载:“故官布袍,直四百五十。”257·17载:“官袍,直五百。”
居延汉简中襦价在每领二百九十钱至一千五百钱之间,价格悬殊。见以下四例:EPT52:188载:“绛单襦一领,直二百九十。”EPT52:189载:“复襦一领,直六百。”EPT59:645载:“练襦一领,直八百三十。”EPT51:302载:“贳卖白袖襦一领,直千五百。”
居延汉简中袴价在每两八十钱至九百钱之间,价格相差十几倍。见以下七例:91.1载:“楼里陈长子卖官袴柘里黄子公,贾八十。”EPT52:493B载:“一匹,直六百,韦袴钱少百,并直七百。”EPT52:493A载:“皮袴,直三百。”EPT52:91B载:“韦袴,直三百。”EPT57:3A:“袴一两,直四百。”EPT57:72载:“复库(袴)一两,直五百五十。”EPT57:56载:“卖皁复袴一两,直七百。”EPS4T1:21:“贳买皁袴一两,直九百。”
以上所见各种衣物面料有布、丝、皮之分,薄厚有单、复之分,来源有官、私之分,更有时代先后之别,要理清其中价格的变动情况是很困难的。
六.布帛价
居延汉简所见布料有以“布”统名者,也有细分为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者。其价格在每匹二百二十七钱至七百五十钱之间,大致稳定。90·56载:“出广汉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廿。”折合每匹二百二十七钱,是为布价最贱者。311·20载:“贳卖八稯布八匹,匹直二百卅。”287·13载:“贳卖八稯布一匹,直二百九十。”EPT56:72A《胡中文布计》载:“尹圣卿二匹直六百,孙赣二匹直六百……”凡八人,共买布十四批,价格为每匹三百钱。282·5载:“贳卖九稯曲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EPT56:10载:“戍卒东郡聊成昌国里何齐贳卖七稯布三匹,直千五十。”即七稯布一匹值三百五十钱。EPT59:660载:“乃受直布一匹,直四百。”308·7载:“入布一匹,直四百。”EPT53:52载:“布一匹,直五百。”2000ES9SP4:22载:“布一匹,贾钱五百。”EPT59:64载:“布一匹,直七百五十。”EPT59:70载:“布二匹,直千五百。”折合每匹值七百五十钱,是为布价最贵者。
居延汉简中所见丝织品有帛、练、缣、素、皁、鹑缕、缥、絣等不同类别,其中帛最为常见。当时戍边吏卒各月俸禄常有以帛供给者,存放在府库,价格在三百二十五钱至八百钱之间,较为稳定。509·15载:“帛千九十匹二尺五寸大半寸,直钱卅五万四千二百。”帛四丈为一匹,折合每匹帛价约三百二十五钱。303·5载:“出河内廿两帛八匹一丈三尺四寸大半寸,直二千九百七十八,给佐史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九月积八月少半日奉。”折合每匹帛价三百五十七钱。509·8载:“受六月余河内廿两帛卅六匹二丈二尺二寸半寸,直万三千五十八。”折价与前条所记相同。187·22载:“已得五月廿日奉一匹三丈三尺三寸,直七百 。”折合每匹帛价至少三百八十二钱。89·12载:“候史靳望正月奉帛二匹,直九百。”折合每匹帛价四百五十钱。210·27载:“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二人,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折合每匹帛价八百钱。 。”折合每匹帛价至少三百八十二钱。89·12载:“候史靳望正月奉帛二匹,直九百。”折合每匹帛价四百五十钱。210·27载:“右庶士士吏、候长十二人,禄用帛十八匹二尺少半寸,直万四千四百四十三。”折合每匹帛价八百钱。
而居延汉简所见各类帛市场价格差异较大。284·36载:“缥一匹,直八百;代素丈六尺,直三百六十八;白练二匹,直千四百;皁二丈五尺,直五百;练一匹,直千。”其中各类帛价均不同:缥价匹值八百钱,代素价匹值九百二十钱,白练匹值一千二百钱,皁匹值八百钱,练匹值一千钱,平均价格在一千钱左右,较前述俸帛价为高。与这一均价相近的有112·27载:“贳卖鹑缕一匹,直千。”214·26载:“买白素一丈,直二百五十。”折价每匹值一千钱。35·6载:“皁练一匹,直千二百。”低于这一均价的有168·13载:“二千八百六十二赵丹所买帛六匹直。”折价每匹值四百七十七钱。EPT59:345载:“今余帛一匹直四百七十七”,帛价与上文一致。EPT59:163载:“缣素上贾一匹直小泉七百枚。”84·5载:“皁四尺,钱七十七。”折价每匹值七百七十钱。高于这一均价的有217·15载:“赦之买收缣一丈,直钱三百六十。”折价每匹值一千四百四十钱。156·34载:“帛一丈六尺,直千九百 。”折价每匹值四千七百五十钱以上。 。”折价每匹值四千七百五十钱以上。
思考题:
1.试述张家山汉简汉简中的“名田宅”制度。
2.试述尹湾汉简中的上计制度。
3.试论居延汉简所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4.试论居延汉简中的物价。
延伸阅读:
1.杨振红:《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社会出版社,1999年。
3.王子今:《汉代丝路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论“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简帛研究汇刊》第1辑,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发行,2003年。
4.丁邦友:《汉代物价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黄今言《从张家山竹简看汉初的赋税征课制度》,《史学集刊》2007年第2期。
高恒《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
谢桂华《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和册书复原》,《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第238—264页。
原释文此处漏释“亖”字,今据图版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