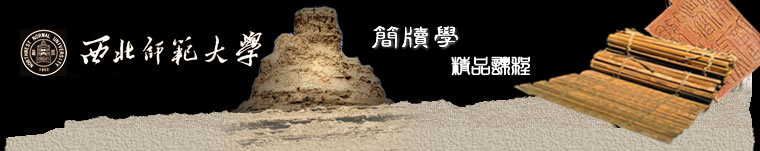第六章 简牍中的军事活动
简牍中的军事活动,历来为学界所重视,早期的简牍研究,从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劳榦的《居延汉简考释》,到陈梦家的《汉简缀述》,均重视于此。迄今仍为简牍学研究之大宗。
军事简牍数量众多,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中原地区人类活动频繁,地层耕作或建筑频繁,古代简牍难以相对完好地保留至今,而边疆地区人类活动相对较少,一些屯戍区废弃后即长期无人问津,大批简牍得以存续。边疆多军事活动,军队档案关乎国家大事,当时人们即已刻意保存。如居延汉简和楼兰魏晋简牍,发现时几乎仍维持当年屯戍部队匆忙撤离时之原状。另一方面,中原人口密度大,开展发掘不易;边疆则如居延古塞与楼兰古城,“地热,多沙,冬大寒”,千百年来无人居住,开掘不致影响人类生活。随着简牍发掘的科学进展,相信中原地区也将陆续出土大量简牍。
简牍中的军事记录,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军事的第一手资料。传世典籍对边疆屯戍语焉不详,20世纪以来大量出土的简牍文书,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居延、敦煌等西北汉简记录了大量屯戍活动,使我们对当时边郡防御、候望系统、屯田生产乃至戍卒生活、随军家属等情况有了较明晰的认识。
本章拟以出土简牍中军事文书之大宗居延汉简和楼兰魏晋文书为代表,对简牍中反映的军事活动作一扼要阐述。
第一节 居延汉简中的军事活动
居延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燧遗址。汉武帝前属匈奴,故有人说居延为匈奴语,与祁连、贺兰、皋兰同音异译,都是“天”意。1930-1931年,中瑞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瑞典人贝格曼(F.Bergman)在中方团员黄文弼发现数枚汉简的今额济纳河流域古居延塞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汉代烽燧遗址展开大规模发掘,出土简牍14000余枚,其中较完整的编号有10200枚,震惊国内外学坛,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和明清大内档案并列为近代中国四大文献考古奇观,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居延汉简”。
1931年5月,这批汉简运抵北京,由刘半农、马衡、傅振伦、傅明德整理研究;1935年后由向达、劳干、贺昌群、余逊等协助。1937年抗战爆发,工作中断,在上海的简牍照片毁于战火,简牍由天津海运至香港大学图书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简牍照片第二次毁于战火,简牍运至美国国会图书馆封存。1943年,劳干依据照片副本,在四川南溪整理出版了石印本《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次年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限于条件,当时均未附照片图版。1957年,劳干于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收录了居延汉简全部图版及释文。1987年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谢桂华、李均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纠正了原来的不少错误。但随技术及研究深入,释文仍可望继续精确化。
1972-1976年,甲渠候官、甲渠第四燧、肩水金关等址又获近2万枚,被称为“居延新简”。
1999-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此地发现5百余枚,命名为“额济纳汉简”。
居延出土年代最早简为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最晚的一枚则是西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九月七日简,也可能是后世扰入。居延屯戍时限主要是汉武帝至汉光武帝间。大规模屯戍则在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后。东汉尤其是光武帝时行保守决策,安内而不攘外,《光武帝纪》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诏罢诸边郡亭候吏卒”。居延屯戍亦止。
一、居延屯戍组织系统
《流沙坠简》已对汉边郡体系作了阐述。在《屯戍丛残考释》中,列举太守府下有诸曹、属国都尉、农都尉、都尉府四个平行职务官署。其中都尉府下又有:1、丞、千人、司马。2、掾、卒史、书佐。3、塞候。塞候下有丞、掾,令史、士吏、尉史。塞候下设部,僚属有候长、士吏、候史。部下有燧,设燧长;燧长领燧卒。随着出土简牍数量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这一系统尚可探讨。还有一些属临时性设置,74EPT50:207:“令使者张君当为居延将军。”汉代常因事命官,如贰师将军、因杅将军、祁连将军等,居延将军当亦然。
汉居延设有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有丞担任都尉府的值班官员。都尉府下设候官(汉代的官,往往指官署而非长官本人,候官之“官”,义近都尉府之“府”,甲渠候官,即甲渠候长官署。),候官居鄣,故亦称鄣候。候官既是部、燧的上级,又是都尉的下级,起着承上启下之作用,故业务最为繁忙,组织也较为复杂。候官的长官称候,下有丞、掾、令史、尉史。还有尉史。候秩六百石,与内郡县令相当,但管辖人口与权限远不及之。《史记·酷吏列传》汉武帝令博士狄山莅官,依次为郡、县、鄣,可为佐证。
候下设部,部下设燧,部、燧为直接进行戍防之军事单位。
部的长官称候长,有候史辅助处理事务。《候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檄》反映候史有定期巡视所部之责。
燧为最下一级防御单位。每燧设燧长,下辖戍卒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当与地理冲僻、军务闲剧有关。
二、居延戍卒来源及身分
居延屯戍者来源相当复杂。汉制男丁自23至56岁均有服兵役的义务,除任正卒、戍卒各一年后,还须每年服徭役一月。戍卒、田卒、骑士属义务军役,此外还有大量应征的良家子、应募士、谪卒,以及随军家属、私从者等。骑士多来自当地;而戍卒则大部为内郡人,田卒、河渠卒亦然。
汉简记载戍卒来自内地的资料甚多,悬泉汉简Ⅰ0309③:237:“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十一月癸未,丞相史李尊,送护神爵六年戍卒河东、南阳、颍川、上党、东郡、济阴、魏郡、淮阳国,诣敦煌郡、酒泉郡。因迎罢卒送致河东、南阳、颍川、上党、东郡、济阴、魏郡、淮阳国。并督死卒传槥。”这条简文较明晰地交代了戍卒更代之程序,内地戍卒至边地,边地役满的罢卒返原籍,死者也要运尸还故乡。
应募士:《汉书·赵充国传》留屯者有“应募”,居延屯府也在当地招募吏卒,居延汉简137.3西汉哀帝建平五年(公元前2年)简,“谨募□戍卒”。290.12:“出茭食马三匹,给尉卿募卒吏,四月十六日食。吏一人马一匹,卒一人马一匹。”
谪卒:《汉书·郦食其传》颜注:“谪卒谓卒之有罪谪者,即所谓谪戍。”秦汉皆有“七科谪”而对象稍异。居延汉简61.3,194.12:“万岁候长田宗,坐发省治大司农茭卒不以时遣,吏将诣官失期,適为驿马载三□茭五石致止害。”185.32:“坐移正月尽三月四时吏名籍误十事,谪□里。”188.17:“马□□善,令病死,谪为卅井南界载。”194.17和214.50有“却谪隧卒”。
三、汉河西屯田生产者
汉代河西屯田生产者,主要有以下几类:
1.田卒。这是屯田简单的基本力量,从汉简记载来看,其构成主要为内郡戍卒。田卒原由边郡戍卒中抽取,故亦称“戍田卒”,也备有武器,平时生产,战时参战。
2.河渠卒。居延还有专职水利官吏。居延新简74EPT65:35:“将军仁恩忧劳百姓元元,遣守、千人,迎水部掾三人。”负责水利的戍卒则称“河渠卒”,居延汉简140.15:“河渠卒:河东皮氏毋忧里公乘杜建,年廿五。”居延新简52:110:“二年二月丁酉朔丁卯,甲渠鄣候护敢言之:府书曰治渠卒”;EPT65:450:“发治渠卒”。
3.弛刑复作。即今日所谓判处徒刑监外执行,《宣帝纪》孟康注:“复音服,谓弛刑徒……复为官作。”据《汉书·赵充国传》“弛刑应募”者为其屯田主要生产者。罪犯自愿应募戍边,政府自然乐于接受。简牍所见弛刑复作数量甚多,居延新简EPT56:185:“当修治凡章,用积徒四万四千。”居延汉简34.9,34.8A:“四月旦,见徒复作三百七十九人……卅八人署厨、传舍狱、城郭官府,六十人付肩水部,部遣吏迎受。”118.17:“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五月癸未,以使都护檄书遣尉丞赦将施刑士五十人送致。”弛刑士与“见徒复作”并见简牍,或两者尚有区别:“见徒”即现行囚徒,弛刑或为缓刑。
4.隧卒、省卒。隧卒、省卒主要任务为戍守,但在军情无患之际,也可参与屯田。居延汉简194.17:“第二隧长景褒不在署,谨验问,褒辞:61.3,194.12:“万岁候长田宗,坐发省治大司农茭卒。”
由于官府允许戍卒携带家属,自然也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不少携家带口的戍卒服役期满后,不愿再回故乡,往往就地安家,从事生产。
四、居延屯戍活动
居延汉简中大量记录了当时烽燧亭障的军事活动。戍卒平时要进行军事训练,守望烽燧;军务之余还要从事生产活动,包括种菜、收茭、伐木、养马等。
天田日迹为每日必记,边塞外沿铺细沙,是谓天田;烽燧吏卒每日巡视,察看敌情,并作记录,即“日迹簿”。两燧结合部还设桩标志,双方巡视至此合符“刻券”,敦煌汉简释文1392酥油土简完整记录了两燧交接:“十二月戊戌朔,博望隧卒旦徼西,与青堆隧卒会界上,刻券;”“十二月戊戌朔,青堆隧卒旦徼东,与博望隧卒会界上。”
戍卒平时负责守望烽燧,举烟火。居延新简EPF16:1-17《塞上烽火品约》,简长38.5厘米,共17枚,是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卅井、殄北三塞联防条例。《品约》规定了匈奴入侵时各种情况下的举烽类别,尤重传递速度和联防配合:“塞上亭燧见匈奴人在塞外,各举部烽如品,毋燔薪。其误,亟下烽灭火。候、尉史以檄驰言府。”古人没有如今日高效的通讯设备,却能维持相当便捷的通讯方式。史载安禄山叛军攻破潼关,距长安仅百余华里,数小时可达,唐玄宗却因“平安火不至”,快速撤离。《塞上烽火品约》为我们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重要佐证。
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691:“昼举亭上烽,夜举离合火。次亭燧合,烦举如品。”据文意此“烽”当指“烽烟”,也就是说,白天燃烟,夜晚举火。其余亭燧依次呼应,遵守《品约》。居延新简E.P.T68:81-92记录了东汉初年十一月辛巳,“日且入时,胡虏入甲渠木中隧,塞天田,攻木中隧”。候长王褒“不以时燔举”,“不如《品约》,不忧事边”,遭劾责,“诣居延狱,以律令从事”。说明《品约》执行严格,违约将受追究。
敦煌汉简2257:
望见虏一人以上入塞,烦(燔)一责新(薪),举二蓬(烽);夜二苣火。见十人以上在塞外,烦举如一人□□
望见虏五百人以上若功(攻)亭障,烦一责新,举三蓬火;夜三苣火。不满二千人以上,烦举如五百人同品。
虏守亭障,烦举:昼举亭上蓬,夜举离合火;次亭遂和,烦举如品。
敌情一至五百人,烽火同品;五百至二千人,烽火亦同。
看来古代通讯有其局限性,不能精确反映实情。
EPT57:108A《候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檄》记候史广德未按时巡察,后经检举,发现各隧防务多阙,“亭不涂,毋马牛矢,毋非常屋,毋沙,毋深目,毋芮薪,烽少二”,“天田不画”等。广德受责。
居延汉简中屯田资料颇多,涉及屯卒身分、田卒生活、屯田组织、生产过程、水利建设、生产工具、屯收分配、仓储管理、剥削形式等。汉武帝反击匈奴获效后,因边费繁重,为巩固成果,戍卒开展屯田。其后徙民建郡,亦有民屯。据薛英群先生统计,居延汉简中的农作物达25种,有不少在今日仍沿袭播植。
汉武帝时赵过创制的代田法,在居延屯区推行。《汉书·食货志》“代田……及居延城”,居延汉简273.24:“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十一月戊戌朔戊戌,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557.5:“第二亭长舒受代田仓……”557.6:“舒受代田……”均反映居延屯田行代田法。这自然促进了西北农耕技术的发展。
居延汉简中的兵器数量众多,最常见的是弩,
五、居延吏卒生活泛览
居延地处边陲,生活本自艰苦。官吏俸禄拨自内地,而内地遥远,加财政或困,时有不至。居延汉简53.19:“元始五年(公元5年)九月,吏奉赋钱不到,迄二年……未得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以来奉。”
戍卒口粮由屯府供给,通常每人每月的口粮是米大石1.2石。居延汉简58.19:“卒张奉子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丁酉自取。”133.7:“令史田忠,十二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一月庚申自取。”257.26:“七月食三石三斗三升少,盐三升,六月癸巳高霸取。”“三石三斗三升少”屡见,可能是一个标配单位。随军家属也有供应,口粮按年龄分级。居延汉简95.20:“王褒妻大女信,年十八,见署用谷×”203.15:“城北部卒家属名籍,凡用谷九十七石八斗。”133.8:“省卒家属名籍,用谷卅石。”衣物布匹,官府所供及戍卒自携,均较丰裕,戍卒用不完还有出售者,4.1:“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311.20:“戍卒魏郡贝丘珂里杨通,贳卖八稯布八匹,匹直二百三,并直千八百。”居延新简EPT57:57:“第卅卒邓耐卖皁復绔一两直七百。”72:“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十一月丙申朔壬寅,居延临仁里耐长卿,贳买上党潞县直里常寿字长孙青复绔一两,直五百五十,约至春钱毕。”与今日军品转民用颇类。
《汉书·王莽传》“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泛指政府)愁苦”,可见一斑。若公给不足,也可携私财。居延汉简10.37“私剑八”,19.1“私马一匹”,看来武器和战马也可私备。
对一些应服正役而又因故无法亲赴者,两汉政府也有变通措施,允许雇人代行。汉代雇佣现象已相当普遍,典型史料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崔实《政论》:“长吏虽欲崇约,犹当有从者一人,假令无奴,当复取客,客庸一月千钱。”这条史料,对我们理解汉简中大量出现的“从者”身分提供了佐证。居延汉简中反映取庸代戍现象多见,雇主出钱,受雇者代戍。各取所需,雇主可在家乡安心生产,受雇者也获经济补偿以贴家用。这种模式,对稳定社会秩序或有一些积极作用。居延汉简224.19:“庸任作者移名,任作不欲为庸。”似反映取庸代戍已获官府认可并加以管理,庸作者身分相当自由,可移名取消庸作。另外,还有一些简文反映官府也作为雇主招募戍卒,居延汉简224.18有“谨募□戍卒”语。
汉屯戍得以长期维持,显然不可能仅靠直接暴力。居延新简EPF22:243:“天子劳,吏士拜。它何疾苦?禄食尽得不?吏得毋侵冤?假贷不赏(常)有?”这是皇帝遣使直接询问居延吏士生活状况的记录。汉简反映戍卒及家属的人身权益得到保障,官吏没有伤害或侮辱他们的权力。EPF22:246:“告吏:谨以文理遇士卒,病致医药,加恩仁恕,务以爱利,省约为首。毋行暴殴击。”有先生认为,汉代屯戍组织中吏卒地位相对平等,戍卒劳动强度可控,享有必需生活品和医疗保障,体现了朴素人道主义。
由《急就篇》和《苍颉篇》可见,汉代对屯边戍卒除保障基本生活需要外,还有扫盲教育。“急就”即“速成”,显属扫盲性质。这一方面不能排除官府之功利:需要戍卒具备起码的书写能力,提交边塞戍防报告;但另一方面,也反映汉政府普及文化知识的积极努力。
六、居延汉简所见窦融治理河西史实
传世典籍中窦融治理河西史缺载,居延汉简则提供了较丰富记录。窦融出守河西达14年,自命河西五郡大将军,在建设河西之同时,继续维持居延屯戍。居延新简中窦融资料甚多,尤以破城子甲渠候官F22遗址最为集中。窦融继承西汉以来各项设施,保障河西稳定,发展经济,调和民族关系,并以大局为重,加强与中原的联系,为中国重新统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窦融是一位相当成熟的政治家,面对中原战乱,他“小心精详”,周旋于各势力间。由于窦氏后来显贵,史传对其评价难免溢美,《后汉书》本传谓“融等遥闻光武即位,而心欲东向”。而出土简牍则给我们提供了更可据信之资料。窦融在河西,先后用过新莽“地皇”、刘玄“更始”、赤眉“建世”和东汉“建武”诸年号,大概是逐鹿群雄此起彼伏令其眼花缭乱,索性在赤眉败亡后的建武二年(公元26年)恢复西汉平帝的年号以求稳健,称“元始二十六年”。直到刘秀已渐次扫平群雄,大局已定的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才“决策东向”,“以投天隙”。EPF22:325A:
●范君上月廿一日过当曲,言:窦昭公到高平还,道不通。
●天子将兵在天水,闻羌胡欲击河以西,今张掖发兵屯诸山谷。麦熟,石千二百;帛万二千。牛有贾(价),马如故。七月中恐急忽忽,吏民未安。
窦昭公,即窦融弟窦友。《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八年(公元32年)闰六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当即此简所记时事。窦融审时度势,不顾河西尚有动乱,“羌胡欲击河以西”,力主与东汉合击隗嚣,终建伟业。
窦融在河西,积极发展经济,为保农耕畜力,建武四年简“部吏毋屠杀马牛”。为防通货膨胀,禁私铸,“部吏毋铸作钱”。禁止铺张浪费,“嫁娶毋过万五千”。又保护生态,“吏民毋得伐树木”。EPF22:43:“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牧、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是说不得役使境内少数民族,保护他们的农牧生产。
《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即窦融颁行的官吏奉禄条例,规定全谷支俸,“以祖(粗)脱谷给”,是应对当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虽数额较西汉减半,实际收入则较新莽大增。它使窦融河西政权官吏能有稳定收入,维持了政局稳定。
前引《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案例,最终以“客民”寇恩胜诉告终,反映窦融河西政权抑止官吏侵民事件的发生。
比较窦融、隗嚣,起初均有摇摆投机。窦融前后屡改年号,可见一斑;但一旦认清东汉将兴,即不再观望,遂获功成名就。隗嚣先附王莽,后降刘玄,再归公孙,又向刘秀频递秋波,但最终未能认清时局,把握时机,终致身败名裂。诚可谓顺逆殊路,功罪异途。
第二节 楼兰简牍中的军事活动
1900年3月28日,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在其第二次中亚探险中,因丢失铁铲,命所雇维吾尔族向导艾尔迪克回去寻找,意外发现了楼兰古城。因事先无充分准备,几乎整整一年后,1901年3月3日,赫定重返,掘得277件汉文简纸文书,这是楼兰简牍的首次发掘。
1903年,赫定发表《中亚与西藏——走向圣城拉萨》,首次公开报导罗布泊沿岸考古经历;两年后,撰成《1899——1902年中亚考察科学成果》,其中第二卷《罗布淖尔》介绍发掘楼兰古城过程。因赫定不谙汉文,委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希姆莱考释,希姆莱认定此地即楼兰,这是楼兰古城湮没千载后首次面世。希姆莱去世后,文书转由另一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孔拉弟继释,1920年发表《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汉文写本及零星物品》,首次系统地向世人公布了这批文书。
1906年12月7日,英籍匈牙利考古学家斯坦因抵楼兰,又获二百余件汉文文书。
1908年6月,日本大谷探险队员橘瑞超在斯坦因编号为LK的古城内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
1930年4月,黄文弼先生在罗布泊北岸发现一处汉代遗址,命名“土垠”,发现汉简71枚,后经考证为史传所载居卢訾仓所在地。
1080年4月,侯灿先生率新疆楼兰考察队对楼兰古城LA再作调查试掘,又发现了一批屯戍文书。
一、楼兰文书中的诸多谜团
《三国志》作者陈寿由蜀降魏,寄人篱下,不得不突出司马氏“功德”,贬抑蜀汉政绩。《史记》、两《汉书》均有《西域传》,《三国志》却代之以《乌丸鲜卑东夷传》,对司马氏平定东夷大加褒赏:“景初中,大兴师旅,诛渊;又潜军浮海,收乐浪、带方之郡。而后海表谧然,东夷屈服。”诛灭公孙渊者,司马懿也;而当时西域在何人之手,陈寿未作交代,留下千古谜团。
传世典籍中不见魏晋西域长史之记载。《晋书·地理志》黄初元年(公元220年)会昌元年(公元841年)置凉州,凉州刺史除管辖河西四郡外,还兼“领戊己校尉,护西域”。但当时河西战乱未息,遑及西域?两年后,河西渐定,鄯善、龟兹、于阗遣使奉献,“是后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魏略·西戎传》言魏晋“戊己校尉所治高昌”。然楼兰文书中屡见相当于西域长史的“督邮”,尤以督邮王业(字彦时)多见。从王彦时文书集中出土的LAⅠ遗址看,时代早于魏晋楼兰屯府LAⅡ“三间房”。而王业又见于《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即景元元年)五月己丑皇太后令,裴注引《世言》曰:“业,武陵人,后为晋中护军。”武陵治今湖南常德,自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吴蜀议和西属。蜀名将廖立即武陵临沅人,而曹魏名宦无一出武陵。《三国志》王业仅见于魏末,或即叛蜀降晋之蜀汉楼兰督邮王彦时。
20世纪初楼兰遗址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学坛。传统以为,两晋亦如两宋,积弱不振。而楼兰文书反映魏晋诸政权均曾有效控制西域,其中西晋泰始年间规模更为宏远。看来干宝《晋纪总论》谓晋武帝“夷吴、蜀之垒垣,通二方之险塞,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民乐其生,百代一时”;及《晋书·武帝纪》尾李世民论:“于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浚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恐怕不为过誉。
二、汉晋楼兰屯戍述略
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伐大宛后,即“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盐泽即罗布泊,说明当时楼兰已有军事活动。黄文弼先生发现的土垠汉简,纪年最早为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最晚为成帝元延五年(公元前8年)
楼兰纪年文书有曹魏嘉平、景元、咸熙等多件。出土于魏晋屯署“三间房”的“景元四年八月八日”简记有“幕下史”、“将”、“录事掾”多种官职;城内灰区所获“咸熙二年四月”简则记与屯田有关的“×种”事宜;另有向官兵支付口粮并有“监仓”押署的廪给简:证明嘉平以后司马氏主政期间曾在这里屯戍。
晋武帝雄才远略,边疆经营成效卓著,楼兰西晋纪年简远过曹魏且大部为泰始年间,即为明证。司马炎对楼兰屯戍之重视,由其对西域长史之任命调遣亦可窥知。东汉于西北持保守决策,中期以降,西域都护有名无职,而以长史代行其部分职能,长史时由敦煌太守遣出,故王国维先生谓“本敦煌郡吏”。然泰始长史则由中央直接任命,楼442:“西域长史承移:今初除,月廿三日当上道,从上邽至天水。”王国维考证为泰始七年以前天水郡治冀城时文书。这位长史来自上邽或内地,断非敦煌郡吏。上邽即今天水市秦城区,冀城在今甘谷县境,从上邽至天水(冀城),正合西行途次。尤可注意者,上邽为魏晋西北重要屯区,曹魏曾徙冀州农丁五千至此屯田,其后邓艾、司马骏均曾继营。这位长史或即由此屯区调任,至少曾在此逗留参观,这也透露出晋初对楼兰屯田的重视及西北屯田的整体联系。
前凉继魏晋续营楼兰,但因孔雀河下游水源枯竭,楼兰生态恶化,屯兵渐割北戍,转营高昌,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建郡立县,此年应即前凉楼兰史之下限。
三、楼兰屯田生产者身分
魏晋楼兰屯田生产者,主要来自征发河西戍卒和招募西域各族民众。河西戍卒中又以敦煌多见,另有酒泉、张掖、西、晋昌、西平郡及姑臧、效谷县等。河东的陇右地区也有少量。内地则未有见。召募西南各族,如:“于尉□南□□×募人。”“尉”缺字,据图版当为“犁”。尉犁为西域胡国,治今新疆焉耆县西南。1980年发现的楼兰简LBT:028“×侯于慰犁”,有学者据此认为魏晋尉犁可能驻有西域长史属下的军侯或曲侯。军侯在尉犁召募屯兵,自当便捷。楼兰文书有“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兵支胡管支”等,当为月支胡族;“兵胡虎”、“兵胡金”、“兵胡秋儿”、“兵胡腾宁”等亦当为胡族。由于他们长于畜牧,在饲养役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兵支胡薄成、兵支胡重寅得,右二人共字驴四岁”,是说两名胡兵养驴达四年之久。
从文书反映的情况看,楼兰屯兵很可能是长期服役,纵有番代之制也未曾实行。反映屯兵思乡情绪的文书不少,如“旷隔险远”,“还未可期”;企盼回家难以实现,“无阶亲省,骞心东望”。因而厌役、逃亡现象屡有发生,“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六月,发讫部兵名,至高昌留屯”,即为一例。
屯戍部兵所受的人身束缚极为强烈。长史、幕下史、帐下将、督战、督田及诸多佐吏,构成严密监管系统。甚至散布各地的牧摄也兼负捕亡之责,楼703:“逐捕不得,使经家而不禽获已,牧摄皆先问所经。”屯府还有牢狱之施,楼361、477记“囚钎”、“囚釿”,当即刑具。
屯戍部兵虽受超经济强制,从事繁重的军事活动及耕牧劳作,但封建政权对其家属也予“复其徭赋,厚加赈恤”。主观上自然是为稳定军心,客观上却也对民众有利。楼170:“华都欲得书与未效谷,属说:□□□华都在此使,厚待遇其门户,莫使有役使。”“未效谷”,楼135作“韦效谷”,文书可能是一位屯戍者写给敦煌郡效谷县韦姓县令的,申诉本人在楼兰服役,故应免除家属徭役。楼35:“超济白:超等在远,弟妹及儿女在家,不能自偕,乃有衣食之乏。今启家恉(诣)南州,彼典计王黑许取五百斛谷给足食用。愿约敕黑,使时付与。伏想笃恤无念,当不须多白。”典计为州县佐吏,自无私许五百斛谷权力,又“约敕”、“使(按)时付与”,都说明有此制度,张超济才自信“笃恤无念”。
四、楼兰屯戍实行供给制
楼兰屯戍自口粮、兵器、生产工具及其他物品均实行供给制。
口粮供给。屯戍部兵按月或计日支廪。楼239:“出穈卌一斛七斗六升,给廪将尹宜部兵胡支鸾十二人,人日食一斗二升,起十月十一日尽十一月十日。”“入糜六斛七斗二升,廪将晋□部兵李平威等二人,人日食一斗二升,起十月十日尽十一月十日”。“出黑粟三斛六斗,廪督战车成辅一人,日食一斗二升,起二月一日尽卅日”。此为月廪,当按月支取。楼538:“(前略)李卑等五人,日食八升,起六月十一日尽十七日。”此为计日支廪。
文书反映口粮标准差异很大,最高人日食12升,最低5升。原因大致有二:一、不同时期的变化,与屯收丰歉有关。楼兰既曾有过“丰粮经月”的温饱,也有“糊口恒有不足”的饥俭。歉收时屯府“权复减省督将吏兵所食”,“权复”反映这种措施较为频繁。同一时期的变化,当与劳动强度有关。这里有一条很典型的材料:“出穈四斛四升(斗)廪兵孙定、吴仁二人,起九月一日尽十日,日食六升。×尽月廿日,人日八升,行书入郡。”二人前十日日食六升,计12斗;后二十日人日8升,计32斗。前后共44斗即四斛四斗,正合总支廪数。后二十日之所以增廪,是“行书入郡”即奔波于路途之故。
兵器供给。楼211背面:“青旃一领、弓一张、箭十枚,沃耆所取。”楼435:“铠曹谨条所领器仗及亡失簿。”领取、亡失均须登记。也有亡失专门报告:楼293正面:“刘得秋失大戟一枚、盾一枚、皮丰兜鍪一枚。”背面:“胡支得失皮铠一领、皮兜鍪一枚、角弓一张、箭卅枚、木桐一枚,高昌物故。”看来兵器管理很严格,士兵死(物故)后仍要追究。
生产工具尤可注意。楼324“犁教”;楼514:“因主簿奉,谨遣遗大侯究犁与牛,诣营下受试。”这是两枚引起学界广泛重视的简牍。西晋政府曾赐西域各国贵族“亲晋大侯”,此简可能记录了中原王朝赐其所封的鄯善王究犁、牛,并在西域长史营教其使用。这是中原与西域生产技术交流的珍贵资料。此外还有“大钻三枚”、“斧八枚”等,反映工具供给种类全面。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为减省运费,有些工具就地取材,就地制作。楼276“胡向犁”、楼455“胡犁”、楼348“胡臿”、楼371·楼561“胡铁小锯”、楼418“胡铁大锯”,工具名前均冠以“胡”字,并有“胡铁”,应即就地冶铸,由屯府“削工”打制。
其他物品则较复杂。戍卒来时有些随身私财物,新简80LBT:051:“奉前郡来时,各有私饷,验官录□藏。”虽由官府代为保管,但所有权仍归戍卒,并可用于交换所需物品,楼553:“兵胡腾宁市青旃一领,广四尺六寸,长丈一尺;故黄旃褶一领:贾(价)彩三匹。”当然,“私饷”也可能是戍卒离家出发时政府发给的财物,《魏书·薛虎子传》“州镇戍兵,资绢自随”,虎子曾集资绢市牛兴屯,若纯系私财,似难实行。另外,楼兰设有织府,上引楼211正面:
五、楼兰屯田组织单位及生产活动
魏晋楼兰屯田以“部”为单位进行,典型资料如楼479:
正面:
大麦二顷已截(栽)廿亩,下穈九十亩溉七十亩
将张佥部见兵廿一人 小麦卅七亩已截(栽)廿九亩
禾一顷八十五亩溉廿亩莇九十亩
背面:
大麦六十六亩已截(栽)五十亩,下穈八十亩溉七十亩
将梁襄部见兵廿六人 小麦六十二亩溉五十亩
禾一顷七十亩莇五十亩溉五十亩
这份文书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楼兰屯田的基本情况。其屯作以“部”为单位,集体耕垦,下种、灌溉、锄草、收获等,都要一一记录。
每部人数有多至“百一人”的,也有如上引“见兵廿一人”、“廿六人”及“部卅二人”,见兵即现有部兵,言外之意是有缺额,则每部兵员当高于此,“估计每将部兵约百人左右”。汉代农亭在魏晋已不见记载。
每部顷亩差异较大,将张佥部21人共耕512亩,人均约24亩;将梁襄部26人共耕378亩,人均约14亩。两部人均相差10亩,或因候望任务闲剧及自然条件互异。而平均值则与《汉书·赵充国传》“人二十亩”相近。
水利也以部为单位维护。楼549正面:“将敕:□□兵张远、马始,今当上堤。敕到,具粮食、作物,诣部会。被敕时不得稽留谷斛。”背面:“五月三日未时起。”此敕精确到时,在农耕生产中未见;当因楼兰水情多变,既有“水大波深必泛”之患,又有“来水少许”之虞,故须及时应对。楼468记“东空决六所,并乘堤,已至大决”,而仅有“五百(伍伯)一人作”,要求“增兵”。
畜牧也以部为单位。楼39记“将朱游私使×羌驴”,影响田作,被责令“还楼兰”推问。楼439:“驴十二头,驼他二匹,将朱游部。”两件文书均记“将朱游”且均与牲畜有关,当即专职畜牧部。
思考题:
1.居延屯戍组织系统是怎样的?
2.谈谈居延戍卒来源与身分。
3.楼兰简牍中的军事活动有哪些?
延伸阅读:
1.薛英群《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3.侯灿《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
居延汉简502.15A,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页。
索麦斯特罗姆《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报告》,斯德哥尔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
《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魏书·蠕蠕传》“敦煌北西海郡即汉晋旧障”,似西晋亦屯防居延,然尚未见确切遗址的发掘报告。
李宝通《东汉经营西北的保守决策述评》,西北师院学报增刊《历史教学与研究》1988年总第10期。
《盐铁论》作“扇水都尉”,显因形近而讹。
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页\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45页。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墨子·号令》:“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光。”
《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60页。
李振宏《汉代屯戍生活中的古典人道精神》,《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初师宾、任步云《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例略考》,《敦煌学辑刊》第3辑。
楼兰古城废弃年代尚有争议。多数学者定在公元330年以后。李宝通认为,西晋泰始年间楼兰生态已趋恶,屯田部兵渐割北戍,前凉短期经略后便转营高昌,至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建郡立县,此应即楼兰古城废弃年。学界属之前凉的“建兴十八年”简应系蜀汉,反映诸葛亮“西和诸戎”史实。参见李宝通:《试论魏晋南北朝高昌屯田的渊源流变》,《蜀汉经略楼兰史脉索隐》。
本节引用楼兰文书,编号据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图版参看侯灿《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版。
《三国志》卷2《魏书·文帝纪》。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89页。
《观堂集林》卷17《敦煌所出汉简蹖》1。
同上《罗布淖尔东北古城所出晋简跋》。
李宝通《蜀汉经略楼兰史脉索隐》,《简牍学研究》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侯灿《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第216页。
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年7期。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32页第25号,第39页第63号,第69页第469号。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57页。
新简80LBT:051、050缀合,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年7期。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53页第237号。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57页第302号。
孟凡人《楼兰新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69页。
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第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