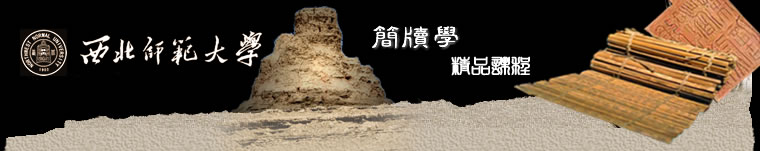|
第九章 简牍中的社会生活
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2)[①]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80年代后渐趋热烈。由于秦汉魏晋社会生活研究缺少后代那种可以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笔记、文集、方志史料,所以作为时人生活记录的简牍材料无疑就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衣食住行
探讨历史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简牍材料可以发现,战国秦汉魏晋,距今时代久远,时人的服饰、饮食风俗,居住及行旅习惯,与后世相比有较大差异。
一、衣食
穿衣、吃饭,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各种性质的出土文献都会对当时的饮食、服饰情况有所涉及,这方面最集中的材料,无疑是以记载随葬品种类、数量为主要内容的遣策类简牍。[②]中国传统丧葬文化强调“事死如事生”,战国秦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无论是贵族还是经济条件稍好的平民,墓葬中一般会有随葬物品,而衣物和食物则是其中的大宗。遣策类简牍对这些物品予以登记,成为今天研究当时服饰风俗、饮食习惯的重要史料。下面就以遣策为主,结合其它简牍材料,对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服饰类别、饮食结构和烹饪技术予以简述。
20世纪以来,遣策类简牍多次出土,战国时期的遣策主要出自湖南、湖北等楚国故地。其中长沙仰天湖楚墓、望山2号楚墓、包山2号楚墓出土遣策,涉及衣物的内容较多。由于这些墓葬埋葬的主要是高级贵族,所以遣策中所记衣物以精美的丝织品为主。仰天湖遣策中记有双层的“紡衣”、画有饰纹的“ 衣”。望山遣策中不但有衣、袴,还有大冠、丝屦,以及组缨、革带等装饰品。包山2号墓的遣策共分四组,置于西墓室葬器之下的那部分所记内容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不少冠饰和衣物。 衣”。望山遣策中不但有衣、袴,还有大冠、丝屦,以及组缨、革带等装饰品。包山2号墓的遣策共分四组,置于西墓室葬器之下的那部分所记内容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其中包括不少冠饰和衣物。
秦汉时期的遣策类简牍数量和出土地域范围都远远超过了战国简牍,所记有关衣物的内容大体可分为衣裤、冠饰、鞋袜、杂服等类型。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遣策保存完整,里面除了有越闰锦衣、熏衣等丝绸衣物外,还有不少关于丝履、素履、绪巾、麻巾、熏囊等鞋袜、杂物的记载,仅手套就有沙绮 、 、 绮 绮 、素信期绣尉等多种名目,反映了当时南方高级贵族的服饰风尚。凤凰山8号汉墓、张家山247号汉墓、海州西汉侍其繇墓、尹湾汉墓等墓葬出土遣策类简牍也有不少与衣物相关的内容。凤凰山8号汉墓遣策中有複襦、襌衣、袍、袭、绔、複裙、履、袜等多种衣物,其中襌衣6件、袍9件。张家山247号汉墓遣策有绀袍、锦裙、素绔、漆履等衣物。尹湾6号汉墓《君兄衣物疏》中有单衣、复衣、复襦、大绔、小绔、襜褕,2号汉墓《衣物疏》有单复衣9领、繻6领、直领2领、诸于3领、絪单襦5领、裙10、绔4、巨巾4、履3、手衣3具。这些衣物种类众多,原料包括丝绸及布匹、葛麻,反映了当时民间服饰的多样性。 、素信期绣尉等多种名目,反映了当时南方高级贵族的服饰风尚。凤凰山8号汉墓、张家山247号汉墓、海州西汉侍其繇墓、尹湾汉墓等墓葬出土遣策类简牍也有不少与衣物相关的内容。凤凰山8号汉墓遣策中有複襦、襌衣、袍、袭、绔、複裙、履、袜等多种衣物,其中襌衣6件、袍9件。张家山247号汉墓遣策有绀袍、锦裙、素绔、漆履等衣物。尹湾6号汉墓《君兄衣物疏》中有单衣、复衣、复襦、大绔、小绔、襜褕,2号汉墓《衣物疏》有单复衣9领、繻6领、直领2领、诸于3领、絪单襦5领、裙10、绔4、巨巾4、履3、手衣3具。这些衣物种类众多,原料包括丝绸及布匹、葛麻,反映了当时民间服饰的多样性。
魏晋时期的遣策类简牍数量无法与秦汉相比,但也时有出土,南昌东吴高荣墓和武威旱滩坡19号晋墓衣物疏是其中的代表。前者主要记有褖、褠、裙、两裆、绔、裳、缚、单衣等衣物,后者除了有袍、衫、襦、练褕、单衣、裙、袴、两当等衣裤外,还有袜、履、巾帻、面衣等鞋袜、杂服。从总体上看,与秦汉时期的服饰风尚差别不大。
上述遣策对于了解古人的服饰风尚有重要价值,而2010年北京大学所收藏的秦简中则有名为《折(制)衣》的文献,为研究当时的服装制造工艺提供了直接史料。简文详细记录了各种服装的形制、尺寸和剪裁、制作方法,种类包括大襦、小襦、大衣、中衣、小衣、袴等,对古代服饰史的研究意义重大。[③]
出土遣策类简牍中关于衣物的内容虽不算少,但如果与其中关于饮食的内容相比,则不免相形见绌。包山2号楚墓,马王堆1号汉墓,张家山247号汉墓,凤凰山8、9、10、167号汉墓出土遣策类简牍中都有不少关于饮食的材料。此外,马王堆1号汉墓、邗江胡场5号汉墓等墓葬中出土有标明随葬食物数量、名称的楬,悬泉汉简中有招待来往宾客的费用簿,居延、敦煌汉简有关于汉代西北地区戍卒饮食情况的记录,这些材料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饮食风尚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据出土简牍,战国秦汉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饮食习俗上有一定差异,但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食物的丰富、精细程度,以及个别地域特色上。从整体来说,在基本的饮食结构方面,差别不大。当时人们的饮食已比较丰富,主要由粮食、蔬菜、瓜果、鱼肉禽蛋、调味品、饮料等构成。粟、大麦、小麦、黍和水稻是当时的主要粮食作物,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中有黄秶、白秶、稻白鲜米,凤凰山8号汉墓遣策有秶秫米、稻秫米、秶米、稻米、白稻米,凤凰山167号汉墓遣策有秶秫、稻糯米、稻稗、秶粺米。其中秶属于粟类,稻白鲜米应是籼米。由这些粮食作物做成的饭即是主食,从出土遣策来看,有黄秶食、白秶食、麦食、稻食和作为干饭的糒等多种称呼。当时的蔬菜以根叶类蔬菜和葱蒜类蔬菜为主,品种较多,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有芋、葵、笋、禺(藕)、葱、赖、襄荷,新旧居延汉简则有葵、韭、菁、葱、大荠等品种。除了蔬菜外,马王堆1号汉墓和凤凰山汉墓遣策里还有不少关于棘(枣)、梨、梅、瓜、李等瓜果的记载。
王公贵族等社会上层分子是鱼肉禽蛋等肉类食品的消费主力军。以马王堆1号汉墓为例,其遣策上所涉及的食物绝大部分属于肉类食品,除了鱼、猪、牛、羊、狗、兔、鸡等常见肉类外,还有鹿、雉、鹄、鹑、爵(雀)、炙姑(鹧鸪)等野味。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鱼肉禽蛋不普遍,但也并非遥不可及。国家虽对民间的牛马食用有一定限制,如东汉初年就有“毋得屠杀马牛”的诏令,[④]但这并不影响死后的马、牛作为食物使用。猪、狗、鸡、鱼是当时较普遍的肉类食品。悬泉汉简有《元康四年鸡出入簿》,反映了即使在边疆地区,鸡也是最主要的待客肉食品。羊的食用在西北边地较内地为多,悬泉汉简《过长罗侯费用簿》中曾提到用羊五头招待“长罗侯军长吏”。秦汉时期的人有爱食包括肝、胃、肾、肠在内的动物下水的习惯,新旧居延汉简频见此类简文,如E.P.T51:235A号简记载的肉食中即有“胃肾十二斤”、“肝一”、“肠一”、“胃八斤”等内脏食品。[⑤]不仅普通平民,就是锦衣玉食的贵族对动物下水也有特殊偏好,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里有大量动物内脏类食物,如“犬肝炙一器”、“朊脯一笥”、“弦脯一笥”、“牛濯胃一器”、“牛濯脾含心肺各一器”等。
作为正常饮食调节品的点心,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和邗江胡场5号汉墓木楬中都有关于“居女”的记载,“居女”即“粔籹”,是战国秦汉时期流行于南方的一种以蜜、秫为原料的点心。
从出土简牍来看,战国秦汉时期的人们对食物的味道已有较高要求,调味品种类复杂。盐是当时最主要的调味品,西北汉简中有“戎盐”、“善盐”等称谓,簿籍中有“盐出入簿”、“廪盐名籍”,在一些特定时段,盐甚至成了官吏的俸禄,居延154·10号简中即有“三月禄用盐十九斛五斗”的记载。糖在当时也已作为调味品使用,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中有“唐一笥”、“唐枎于頪一笥”的记载。凤凰山8号汉墓、张家山247号汉墓遣策和居延汉简中的“薑(姜)”,是时人常用的辛辣味调味品。而用豆、面等原料调盐形成的豉、酱,更是汉人非常喜爱的调料。《急就篇》颜师古注曰:“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⑥]对酱在食物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参之简牍,可知颜说不谬。居延、敦煌、悬泉、张家山汉简中都有关于“豉”、“酱”的记载,肩水金关汉简《劳边使者过界中费》载:“盐豉各一斗,直三十;酱将薑,直五”,盐豉和酱薑是招待劳边使者的重要调料。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中除了有 (豉)、酱外,更有肉酱、爵(雀)酱、马酱等经过深加工的酱类食品,反映了贵族阶层在调味品使用上的精益求精。 (豉)、酱外,更有肉酱、爵(雀)酱、马酱等经过深加工的酱类食品,反映了贵族阶层在调味品使用上的精益求精。
战国秦汉时期饮酒之风盛行,这一点在简牍材料中也有体现。居延、敦煌等西北汉简中关于酒的记载层出不穷,甚至有低级军官因醉酒伤人而叛逃出塞的极端事例。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中有白酒、温酒、助酒、米酒。悬泉汉简《过长罗侯费用簿》中有关酒的消费相当庞大,从简文可知,为了招待长罗侯的随从军吏,悬泉置用酒20石,其中2石由县里配给,18石“置所自治”。
秦汉时期不仅饮食结构完善,烹饪技术、方法也丰富多彩。仅从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中关于肉制品的制作来看,就有烧烤、煎熬、清蒸、菹醢、腊、脯、做羹等多种烹调手法。其中烧烤类食品有牛炙、牛乘炙、犬肝炙、豕炙、鹿炙、炙鸡等,煎熬类食品有熬豚、熬兔、熬鹄、熬凫、熬雁、熬雉、熬炙姑(鹧鸪)、熬阴鹑、熬鸡、熬爵(雀)等,清蒸类食品有烝秋(蒸鳅),以腌制为主的菹醢类食品有鱼 、肉 、肉 ,将肉风干的腊制品有羊昔(腊)、昔(腊)兔,将肉拌上调料然后晒干的脯制品有牛脯、鹿脯、朊脯等。而种类繁多、最受欢迎的无疑是肉羹,具体来说肉羹又包括不调五味不和菜蔬的 ,将肉风干的腊制品有羊昔(腊)、昔(腊)兔,将肉拌上调料然后晒干的脯制品有牛脯、鹿脯、朊脯等。而种类繁多、最受欢迎的无疑是肉羹,具体来说肉羹又包括不调五味不和菜蔬的 羹(又称大羹),掺和稻米的白羹,加有芹菜或苦堇的巾羹,拌有葑菜的逢羹,加了苦菜的苦羹等种类。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中,有牛首 羹(又称大羹),掺和稻米的白羹,加有芹菜或苦堇的巾羹,拌有葑菜的逢羹,加了苦菜的苦羹等种类。马王堆1号汉墓遣策中,有牛首 羹、鸡白羹、狗巾羹、豕逢羹等几十种肉羹。其中“鹿肉鲍鱼笋白羹”、“鲜鱯禺鲍白羹”等食品,仅从名字就能想象出其用料和做工的讲究。1999年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约300枚是有关烹调的内容,整理者将其定名《美食方》。《美食方》中关于植物性食品制作的有7条,关于动物性食品制作的有148条。其详细介绍了每道菜的烹制程序,是研究汉代饮食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羹、鸡白羹、狗巾羹、豕逢羹等几十种肉羹。其中“鹿肉鲍鱼笋白羹”、“鲜鱯禺鲍白羹”等食品,仅从名字就能想象出其用料和做工的讲究。1999年湖南沅陵虎溪山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约300枚是有关烹调的内容,整理者将其定名《美食方》。《美食方》中关于植物性食品制作的有7条,关于动物性食品制作的有148条。其详细介绍了每道菜的烹制程序,是研究汉代饮食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住
安居才能乐业。历史时期居民的居住环境、建筑禁忌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课题之一。探讨战国秦汉时期民居的基本结构和装饰布置情况,主要须依靠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但也不可忽视出土简牍中的相关内容。
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的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主要的居住形式是聚居,每里中的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社区里,“居处相察,出入相司”。里有里门,平时由田典“挟里门龠”,按照规定的时刻开闭。《户律》还规定了不同爵位、身份的人分别应该占有的住宅面积,一宅“大方卅步”,彻侯可占105宅,关内侯可占95宅,大庶长90宅……至上造可占2宅,公士一宅半,没爵位的庶人1宅,司寇、隐官等曾具有刑徒身份的人仅半宅,这种对住宅面积的限定充分体现了封建国家的身份性特征。当时,国家对私人购买房产也有限制,《户律》中就有“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的规定。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中对当时普通居民的居住条件有所涉及,《封守》章载:“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甲的房屋有一个堂屋、两间卧室,与《汉书》中晁错曾提到的“一堂二内”的住宅结构相似。房屋上有瓦盖,屋里的主体由木构成,屋外种着10株桑树,与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居住观念也相符合。《封诊式·穴盗》对当时某些民居的描述更详细,
房内在其大内东,比大内,南乡(向)有户。内后有小堂……内北有垣,垣高七尺,垣北即巷殹(也)。垣北去小堂北唇丈,垣东去内五步。
“大内”是主人的卧室,其东边有个开有南门的侧房“房内”,侧房后面是个小堂,整座住宅坐北朝南,在一个临街的院子里。睡虎地秦简《日书》[⑦]甲种中也有关于民居建筑的信息,其载一座完整的民居会包括猪圈、粮仓、水井、池塘、排水沟等辅助设施,可以说已相当完善。
关于当时住宅的室内陈设和布置情况,可以参考遣策类简牍。以马王堆1号汉墓为例,其遣策中家具有长五尺高三尺的木五菜画并风(屏风)、漆画木变机(几)、熏卢(炉)、布漆检(奁)、九子曾(层)检、五子检、布缯(层)检等;卧具有席子多种,如涓度席、滑 (篾)席、莞席等。除了“莞席”,遣策中还有“坐莞席”,其以“坐”为名应是坐具,与前述作为卧具的席子有别。除了马王堆汉墓遣策,其它遣策类简牍中也有不少关于室内陈设用品的记载,如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从器志》中就有博具、梠机、坐絪、簟席、簟长席、张(帐)帷、张(帐)帷柱及丁(钉)、大方籨(奁)等用品。 (篾)席、莞席等。除了“莞席”,遣策中还有“坐莞席”,其以“坐”为名应是坐具,与前述作为卧具的席子有别。除了马王堆汉墓遣策,其它遣策类简牍中也有不少关于室内陈设用品的记载,如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从器志》中就有博具、梠机、坐絪、簟席、簟长席、张(帐)帷、张(帐)帷柱及丁(钉)、大方籨(奁)等用品。
战国秦汉时人在住宅兴建的地点和时间选择方面有一定禁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啻》篇、《室忌》篇、《土忌》篇、《门》篇、乙种《室忌》篇主要就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室忌》篇和《门》篇分别列出了一些“勿以筑室”和“不可初穿门、为户牖、伐木、坏垣、起垣、彻屋”的具体日子,供人们在建筑择日时使用。《啻》篇则依据当时流行的五行观念将建筑时间和房屋朝向的禁忌结合起来,
春三月,毋起东乡(向)室。夏三月,毋起南乡(向)室。秋三月,毋起西乡(向)室。冬三月,毋起北乡(向)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
除此之外,《啻》篇还强调了“啻为室日”这样一个概念,“啻”即“帝”,“啻为室日”就是上帝盖房子的日子。在这一天,人们绝不能建屋,不然会有可怕后果。具体来说,如果这一天建主卧室,家长会死;建右宅,大儿媳妇会死;建左宅,中子的媳妇会死;建外墙,孙子会死;建北墙,牛羊会死。
除了建筑时间外,战国秦汉时期的人还相信住宅的结构及周围环境对居住者的命运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相宅术流行,九店楚简《日书》载:“北方高、三方下,居之安寿,宜人民,土田聚(骤) (得)。”房屋建在“北方高、三方下”的环境,有种种吉利,显然是良宅。 (得)。”房屋建在“北方高、三方下”的环境,有种种吉利,显然是良宅。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也有相关内容。其《梦》篇之后附有一大段关于相宅的内容,一般被称为“相宅篇”或“宅居篇”,分别对住宅在城中地理位置的高低、结构布局、朝向与居住者命运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剖析。“凡宇最邦之高,贵贫。宇最邦之下,富而 (癃)”条即是说,住宅如果建在全城最高处,主人政治地位会高但家庭贫困,如果住在全城最低处,主人生活富裕但身体会有残疾。“为池西南,富。为池正北,不利其母”条即是说,在住宅西南方向挖池塘,家庭就会富足,在正北方向挖,就会不利于主人的母亲。这种相宅书无疑是了解当时居住风俗的重要史料,值得关注。 (癃)”条即是说,住宅如果建在全城最高处,主人政治地位会高但家庭贫困,如果住在全城最低处,主人生活富裕但身体会有残疾。“为池西南,富。为池正北,不利其母”条即是说,在住宅西南方向挖池塘,家庭就会富足,在正北方向挖,就会不利于主人的母亲。这种相宅书无疑是了解当时居住风俗的重要史料,值得关注。
三、行
秦汉大一统的形成与长期维持,和交通事业的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国家对交通的重视,为人们的出行、交往也提供了便利。出行是社会生活方式之一,借助简牍材料对秦汉时人的出行条件、行旅风尚进行探索,是简牍学的研究任务。
道路的修建与维护是出行的前提条件,秦汉统治者对其尤为重视。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就将“除陛甬道”和“千(阡)佰(陌)津桥”作为地方官吏的基本职责。青川秦牍所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更修的《为田律》中有关于田间道路修整维护的内容,
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隄,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在9月和10月农闲期间集中修整道路、桥梁等交通设施。如果道路在“非除道之时”损坏,也须及时修补。相关法律汉代予以继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载,
恒以秋七月除千(阡)佰(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梁。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乡部主邑中道,田主田道。道有陷败不可行者,罚其啬夫、吏主者黄金各二两。
明确规定邑中道和田道由相关吏员负责维护,如果道路“陷败”,主者将承担法律责任。悬泉汉简V13094:40号简有县廷要求属下“缮治道桥”的记载。居延新简中也有关于道路维修及养护的内容。E.P.T65:173号简载“开通道路毋有章处”,应是边塞地区行政或屯戍机构对于道路兴建的要求,其中“章处”即“障处”。而E.P.T65:230号简 “车马中央未合廿步溜漉不可”的记载,也反映了当地政府机关对道路状况的重视。“溜漉不可”与“陷败不可行”相似,是由于雨水导致的路基破坏或路面翻浆,[⑧]简文中对此情况的说明可能与追查相关责任人及展开道路养护活动有关。除了陆路交通,当时的水上交通也较普遍。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关于“行水”、“船行”的记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规定:“诸漕上下河中者,皆发传”,可见在汉代以河运为主的漕运已相当发达。
秦汉时期交通畅通,在辽阔的疆域内已基本形成了以直道、驰道为中心的较为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由于年代久远,以往我们对当时交通运输路线的研究只能借助于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梳理,错误在所难免。而20世纪以来相关简牍材料的出土,使我们获得了大量有关当时交通网络的第一手资料,准确性和全面性都有极大的提高。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中有三枚地名里程木牍,分别涉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交通情况,记录了秦代由北而南三段重要的驿道。[⑨]以1652号简第二栏的记载为例,
鄢到销百八十四里
销到江陵二百四十六里
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
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
索到临沅六十里
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简文非常清楚的揭示了秦代从鄢到迁陵的路线走向及具体里程。由于简中的地点大都临近汉水、长江及洞庭水道,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此驿路应是水陆并用,反映了水运在当时南方地区的交通系统中已占据重要地位。[⑩]而1652号简驿路“凡四千四百四十四里”,1714号简驿路“泰凡七千七百廿二里”的记载更直接反映了秦代驿路交通的庞大规模。2010年北京大学收藏的秦简中也有类似的交通里程书,其关于“某地到某地”里程的记录甚至详细到“步”。简中的交通路线既有陆路,也有水路,涉及的地名以“安陆”、“江陵”为多,主要反映了战国晚期至秦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交通网络。
这种邮置里程简牍在汉简中也多有发现,居延新简E.P.T59:582号简,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
茂陵至茯置卅五里 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茯置至好止七十五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
好止至义置七十五里 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 ……
(以上为第一栏)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里
居延置至 里九十里 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 里九十里 日勒至钧著置五十里
 里至 里至 次九十里 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 次九十里 钧著置至屋兰五十里
 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屋兰至 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屋兰至 池五十里 池五十里
(以上为第二栏)
是由长安西行至居延地区之间邮置里程的记录。通过此简,我们对此交通线的准确走向、途径、里程,甚至邮置设置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无独有偶,类似的简牍在悬泉汉简中也有发现,Ⅱ02141:130号简,
仓松去 鸟六十五里 鸟六十五里  池去觻得五十四里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池去觻得五十四里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
 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
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其反映了汉代河西地区的邮置道里等交通情况,恰与前述居延里程简相衔接,构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从长安出发到河西敦煌地区的里程表,对于研究两汉时期东丝绸之路的交通情况有重要意义。[11]此外,邗江胡场5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宣帝时期的记事木牍也反映了当时东方沿海地区陆上交通的便利情况。[12]
战国秦汉时期的主要交通道路上,一般设有关卡,对人民的出行予以限制、管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就是汉初关于关禁制度的规定,其中明确规定普通百姓通过关津,必须使用符、传。《释名·释书契》称:“传,转也,转移所在执以为信也,亦曰过所,过所到关津以示之也。”作为时人出入关口通行证的传(或称过所),在出土简牍中多有发现,居延汉简15·19号简,
永始五年闰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自言为家私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敢言之。
闰月丙子觻得丞彭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书到,如律令。掾晏、令史建。
即是汉成帝时期的一件通过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的过所,记录了将要出关者的姓名、籍贯、出关缘由等事项,并注明其没有欠税和司法问题。
学界对秦汉时期的交通工具有所研究。从出土简牍来看,陆路交通工具主要有车、马,水路交通工具则主要是船。车在载人、载物方面作用突出,而马在长途远行、驿传交通中不可替代。汉简所见的车有轺车、方相车、传车、牛车、大车、轻车、橐佗龟车、兰车等等。居延新简《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简册载,居延农民寇恩曾以自己的车载5000头鱼至觻得为甲渠候粟君贩卖,可见当时车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悬泉汉简有《传马名籍》等关于传马管理的详细记录。而居延新简《驹罢劳病死册书》则是一件围绕马驹累死展开的诉讼,最终塞尉放因此事被劾以“以县官马擅自假借,坐赃为盗”的罪名,由此可见汉代官府对马的重视。“船”在秦汉简牍中也较常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均输律》称:“船车有输”,明确指出在交通运输上船与车有着几乎同样重要的作用。凤凰山8号汉墓遣策中有“船一艘”,及有关“大奴某擢(棹)”的6枚简牍,参之同墓所出木船模型,可以想见当时湖北地区船运的普遍。此外,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中舨舨长张伯”等人相与为“舨约”的内容,反映了汉初江陵地区利用舟船往返贸易的情况。[13]对于船的使用,不仅局限于长江流域,甚至在被认为干旱的西北边郡,也存在造船生产,居延简载,
□□□为□□五百石治舩 109·3
 □处益储茭谷万岁豫缮治 □处益储茭谷万岁豫缮治 毋令 E·P·T59:658 毋令 E·P·T59:658
其中的舩、 即是船字的异写。 即是船字的异写。
秦汉时期,商人、戍卒、官员等群体出行频繁。据统计,居延和敦煌的戍卒大量来自于关东地区,其中不乏远如魏郡、渔阳、丹阳等郡者。[14]戍卒的出行充满艰辛,居延汉简中就有“行道辟姚(遥)”、“戍卒行道物故”的记录。官员的出行条件则较为优越,国家在道路沿线设置有传舍、驿置等机构,为过往官员提供食宿及传马服务。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都有《传食律》,详细规定了不同身份的官员在传舍可享受的食宿、车马待遇。以张家山汉简为例,
丞相、御史及诸二千石官使人,若遣吏、新为官及属尉、佐以上徵若迁徙者,及军吏、县道有尤急言变事,皆得为传食。车大夫粺米半斗,参食,从者 米,皆给草具。车大夫酱四分升一,盐及从者人各廿二分升一。食马如律,禾之比乘传者马。 米,皆给草具。车大夫酱四分升一,盐及从者人各廿二分升一。食马如律,禾之比乘传者马。
“车大夫”及其从者,在传舍等机构中有米、酱、盐等物品的供应。悬泉汉简出土后,学界对汉代邮置的食宿供给作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据《过长罗侯费用簿》可知,邮置对过往高级官员的供给十分丰盛,除了粮食和酒外,仅副食品就有羊、鱼、鸡、牛肉、酱、豉等物。
与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一样,秦汉人对于出行也有很多禁忌,涉及出行时间、形式、方向等各个方面。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迁徙》、《行》、《归行》、《到室》、《禹须臾》,乙种《诸行日》、《行》,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择行日》等篇都以出行为主要占卜对象。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除》篇也有关于出行的内容,
外害日,不可以行作。之四方野外,必耦(遇)寇盗,见兵。
外阴日,利以祭祀。作事,入材,皆吉。不可以之野外。
夬光日,利以登高、饮食、猎四方野外。居有食,行有得。
在所谓的“外害日”、“外阴日”不适合出行野外,而“夬光日”则是出行的吉日。除了出行的日子有禁忌外,返家的日子也有禁忌,须慎重选择,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行者”题下即载:“远行者毋以壬戌、癸亥到室。”有时出行日期的选择与出行方向有密切关系,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归行》篇载,
凡春三月己丑不可东,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百中大凶,二百里外必死。
其中“百中”是百里之内的意思。时人关于出行的禁忌很多,据统计,秦简《日书》所列行忌凡14种,除去重复后,全年行忌日尚有165日,占全年日数的45.2%以上,禁忌的苛繁严密可见一斑。[15]
除了行忌日,当时还存在一些出行行为上的禁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行》篇载,
凡民将行,出其门,毋(无)敢 (顾),毋止。直述(术)吉,从道右吉,从左吝。少(小) (顾),毋止。直述(术)吉,从道右吉,从左吝。少(小) (顾)是胃(谓)少(小)楮,吝;大 (顾)是胃(谓)少(小)楮,吝;大 (顾)是胃(谓)大楮,兇(凶)。 (顾)是胃(谓)大楮,兇(凶)。
出门时不能停步,更要避免回头,如果稍稍回头看,会受耻辱,如果大转身回头看,则会有大灾难。走在路的中央或右边吉利,如果走在路的左边,就会蒙受耻辱。
出行禁忌的广泛存在,与时人忌惮鬼怪的心理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战国秦汉人普遍相信鬼神对人类生活的干预,而这种假想的干预在野外出行中更被无限放大。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中有教人在出行时利用巫术对付鬼怪的方法,
鬼恒从人游,不可以辞,取女笔以拓之,则不来矣。
人过于丘虚,女<母>鼠抱子逐人,张伞以乡(向)之,则已矣。
人行而鬼当道以立,解发奋以过之,则已矣。
在这里,女笔、伞、头发都成为了对付影响出行的鬼怪的武器。
由于出行的过程充满艰辛和不可预知的危险,所以出行前进行祠祀在先秦秦汉时期有着特殊意义。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不少关于“祠行”的内容,乙种《行行祠》条:
行祠,东行南〈南行〉,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其謞(号)曰大常行,合三土皇,耐为四席。席叕(餟)其后,亦席三叕(餟)。其祝曰:“毋(无)王事,唯福是司,勉饮食,多投福。”
详细记载了祠行的仪式规则,东南行时祠大常行和三土皇四神于道左,西北行则祠于道右,祠行时需要酹酒并作祝辞。
在传世文献中,先秦秦汉时期最受重视的行神无过于“祖”神,而祠祀“祖神”的仪式,直接导致了当时出行前“祖道”风习的盛行。《汉书·疏广传》载,汉宣帝时太傅疏广衣锦还乡,“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祖道”已从单纯的祠祀行神的活动发展为一种表达离别之情的交际方式。这种交际方式在汉代颇为盛行,居延汉简载,
候史褒予万岁候长祖道钱 出钱十付第十七候长祖道钱
 道钱 出钱十付第廿三候长祖道钱 道钱 出钱十付第廿三候长祖道钱
 道钱 出钱十 道钱 出钱十
出钱 104·9,145·14 104·9,145·14
简中明确提到了“祖道钱”的概念,丰富了我们对汉代出行风尚的认识。
第二节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其文化意蕴丰富,是我们了解时代风尚的重要参考。浩如烟海的传世文献对古代社会的人际交往,有较多关注,但其形式、内容过于单调。而近年出土的一些简牍材料则是古人交往的鲜活记录,恰可补文献之缺。古人在交往中留下的记录有许多种,如赠钱名籍、名刺、谒、书信等等都是古人在不同交际领域中所留下的印迹。
一、 赠钱名籍
亲朋之间互相以礼物、钱财祝贺或资助对方家庭一些重大事件的行为,长期以来是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其在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已成为一种风俗习惯,并绵延至今。古人家中有喜事、丧事或其它花费较多的事件,邻里亲朋往往会向当事人赠送一定数量的钱财、物品,要么用来庆贺,要么用于资助。记录赠送钱款情况的清单就叫“赠钱名籍”,一般包括赠钱者的姓名和钱财数目。通过一些残存至今的“赠钱名籍”,可以了解古人在婚姻、出行、丧葬之际的交往情况,对认识当时的社会风尚有重要价值。
传世文献中有不少关于赠钱这种社会交往形式的记录,仅《史记》中就记载了与刘邦有关的两次赠钱活动。一次是迁居贺钱,吕后的父亲初迁沛地,当地豪绅都前往致贺,萧何负责赋敛礼钱,刘邦擅为大言,自称“贺钱万”而受到吕公的注意。另一次是出行赠钱,刘邦早年曾以吏的身份“徭咸阳”,当时沛县的其他小吏纷纷向刘邦赠钱,一般是“奉钱三”,而萧何“独以五”。除了出行、迁居外,婚姻、丧葬等活动中也往往有赠钱的举动。尤其在丧礼中,以赠钱为主要形式的赙賵活动更是被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称:“賵者何?丧事有賵。賵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賵,货财曰赙,衣被曰襚。”《史记正义》称:“衣被曰襚,货财曰赙,皆助生送死之礼。”史书记载表明,先秦秦汉时期赙賵之礼非常盛行,如果一些人能辞拒数额巨大的赙賵,甚至会被视为“高志凌云”。
根据《仪礼·既夕礼》“知死者赠,知生者赙。书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的记载和郑玄“书賵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的注解,可知当时有将赠钱物者的名字和所送钱物登记于木牍之上的习惯。以前我们对此的认识,多限于文献记载。而20世纪以来,这种性质的木牍屡有出土,为研究这种社会交往方式的具体情况提供了便利。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曾出土汉初简牍170余枚,其中一块木牍载:
载翁仲七十 王翁季五十 杨公子卌
庄伯五十 胡兄五十 靳悍卌
□小伯五十 袁兄五十 张父卌
□翁仲五十 氾氏五十
陶仲五十 姚季五十
王它五十张母卌
张苍卌
(以上为正面)
不予者 陈黑 宋则齐 (以上为背面)
此牍所记内容为人名和数字,且出土于墓葬之中,与郑玄“书賵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的记述相符。其记录了墓主人死后亲朋为之赙賵的情况,当是一种有关赙賵的赠钱名籍。[16]其中除了记载赠钱者的名字和赠钱数量外,在牍的背面还有“不予者”的名字,与今天的风尚似有不同。
1993年出土的尹湾汉简中,编号为M6D7、M6D8的两块木牍,分别在正反两面记录了一些人名和钱数,也是“赠钱名籍”类简牍的实物遗存,其中M6D7上还有“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明确纪年。这两块木牍所记赠钱之事不止一次,牍中除了记载人名、钱数外,还有“外大母”、“季母”、“之长安”等文字说明,可能“指受钱原因或受钱者”。[17]两牍所记赠钱数额多为二百、三百、五百,最多的有千钱,少的有百钱。M6D8中且有22人合凑500钱作为赠礼的情况,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交际风尚提供了直观材料。
二、名刺、谒
古人登门造访等交际行为往往需要通报,而名刺和谒即是当时用作通报的媒介,是上层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交际物品,时人谓之“通达谒刺”。睡虎地秦简和放马滩秦简《日书》中有占卜某日适合请谒与否的材料,睡虎地秦简《日书》载,
开日,亡者,不得。请谒,得。 甲种24正二
六月:酉(柳),百事吉·以【生】子,肥。可始寇<冠>,可请谒,可田猎。 乙种91一
能不能请谒和请谒是否能达到目的,显然是古人在社会交往中关心的问题。今天发现的简牍材料中,有不少古代名刺、谒的实物。这些刺谒的形制、内容,对于了解古人的交际行为有重要参考价值。
刺是用于禀报的实录文书,《文心雕龙·书记》称:“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中也称:“刺谓书之于刺板也。”今天能见到的简牍材料中,有记录到行政机构办事人员的“入官刺”,有按月记录廪食情况的“食月别刺”,有记录俸禄发放情况的“出俸刺”,有记录邮书传递过程的“邮书刺”,有记录烽火信号通过辖界情况的“表火出入界刺”等等。[18]而本节要着重介绍的,则是用于通报自己身份、姓名的名刺。
东汉刘熙《释名·释书契》中说:“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者也。下官刺曰长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名刺这种通报媒介,多见于东汉之后,《太平御览》卷606载汉末名士郭泰成名后“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其中的“刺”即是“士”用以表明身份的名刺。名刺一般是本人持用,事先按照常套写好问候语和本人的名姓爵里,一式多份,以备使用。这种名刺的实物在魏晋时期的墓葬中时有发现。1974年南昌永外正街1号晋墓中出土木刺5枚,1979年南昌东吴高荣墓中出土木刺21枚,1980年湖北鄂城水泥厂1号吴墓中出土木刺6枚。[19]此外,近年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和东牌楼东汉简中也都有木刺。这些名刺的格式基本相同,以高荣墓出土木刺为例:
弟子高荣再拜 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绶
其书写格式正是“长书中央一行而下”,先写致问人的姓名“弟子高荣”,接着是问候语“再拜问起居”,然后说明籍贯沛国相县,形式与《释名》所载完全一致。同墓出土内容、形制完全一样的木刺21枚,也说明名刺确是提前做好,一式多份。
其实在西汉之前,名刺并不多见,当时用作通报、致问的主要是与名刺既相似又略有区别的“谒”。《释名·释书契》称:“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史记·郦食其列传》载,郦食其“踵军门上谒”,拜见刘邦。谒是表明身份、通报致问的媒介,但其与名刺在使用上尚有一定差别。一般认为,谒常常是为某次进谒临时写就,正规的格式是分行书写各项内容,即受谒者的官职和称呼,进谒的目的和进谒者的官职姓名。与名刺往往是本人亲自使用不同,谒的持用者不仅可以是本人,也可以是代表本人的被差遣的下人。[20]《后汉书·孔融列传》载,何进迁为大将军,孔融受大司徒杨赐差遣奉谒向何进庆贺,由于未及时被何进家人通报,孔融一怒之下“夺谒还府”。孔融受杨赐之命奉谒拜见何进,正是差下人奉谒拜问的实例。关于实物“谒”,以1993年尹湾6号汉墓出土的最具代表性。尹湾汉墓共出土木谒10枚,其使用都与墓主人东海郡功曹史师饶(字君兄)有关。除22号木牍仅在反面书写外,其余都是正反两面书写,行文基本格式一致。一般是正面为受谒者的官职和姓氏尊称,反面第一行写致谒者的官职、姓名以及恭语“再拜”,第二行写问候语如“请”、“谒”、“问”等,第三行写进谒的目的及致谒者的姓名乡里。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为他人遣吏来谒所持,如牍15,
进东海大守功曹
师卿 D15正
沛郡太守长熹遣吏奉谒再拜
问
君兄起居 南阳谢长平 D15反
即是沛郡太守遣吏拜谒师饶所用。一为师饶遣吏往谒所持,如牍23,
进长安令
兒君 D23正
东海大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
请
威卿足下 师君兄 D23反
即是师饶遣吏致问长安令兒君所用。
尹湾汉墓所出土的木谒,价值巨大,通过对它们的考察,我们可以对西汉晚期一个地方郡功曹在官场中的交往圈子有简单的了解,可以真切的知道当时官场中的人际交际情况。师饶不但接受本郡长官的派遣、礼遇,还与沛郡、琅邪、楚等其它地方的太守、县令长,及容丘侯、良成侯等封君有密切关系。这些木谒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当时的官场网络,是反映秦汉时期人际交往的重要史料。
不仅中原地区,甚至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西域地区,也流行着作为社交媒介的刺谒类简牍。尼雅遗址出土汉文简牍中,就有西域王公贵族之间送礼、致问的记录,如
王母谨以琅玕一致问(正) 王(背)
臣承德叩头谨以玫瑰一再拜致问(正) 大王(背)
君华谨以琅玕一致问(正) 且末夫人(背)
苏且谨以琅玕一致问(正) 春君(背)
奉谨以琅玕一致问(正) 春君幸毋相忘(背)[21]
尼雅遗址是汉代精绝国所在,这些简牍反映了精绝贵族间以琅玕、玫瑰等礼物通谒致问的交际形态,而王母以琅玕向王致问的简牍更是当地王族内部家庭交际的直接史料,价值不菲。
三、书信
书信是人际交往最直接的体现之一,其内容丰富、信息含量较大,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起着沟通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秦汉魏晋传世文献中,收录有一些历史人物的书信,著名者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窦融的《致隗嚣书》、冯衍的《与妇弟任武达书》等。这些书信的史料价值毋庸置疑,但遗憾的是它们都经过史籍编撰者的改编,已非原貌。并且史籍中所录书信往往来往于高官名士之间,对了解当时基层社会的人际交往用处有限。20世纪以来,随着简牍文献的不断问世,我们得以接触到一些秦汉魏晋时期私人书信的原件,为了解当时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的人际交往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出土简牍中与私人书信有关的内容不少,但相当一部分是残简,较完整的主要有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两封书信、天长19号汉墓出土的与“孟”有关的书信、东牌楼7号井中出土的书信,以及新旧居延、敦煌汉简和楼兰、尼雅汉晋文书中的一些书信材料。从内容上来说,大体可以分为家书、朋友书信、请托询问书信和社会上一些应酬往来的书信。
家书以睡虎地4号墓出土书信最具代表性。睡虎地4号墓出土木牍两方,分别是两封家书。第一封是从军在外的黑夫、惊兄弟二人写给家中兄弟中的信。黑夫和惊是安陆人,公元前223年正在淮阳秦军中参加灭楚战争。其信中有对家乡亲人的问候和对战况的简单描述,但核心内容是黑夫通过中向母亲要钱、要衣,并说如果安陆“丝布贵”,就不要寄衣了,把钱送来他可以在淮阳置办,信中嘱咐母亲寄的钱一定不要太少。而惊在信的最后单独问候了自己的妻子,并勉励她孝敬公婆。第二封信写于第一封信之后不久,由惊寄给衷(即第一封信中的“中”),信中问候了亲属,对家中的事有所嘱托,核心内容与第一封信相似,希望母亲快点给自己送来钱和做衣服用的布料。惊在信里强调了处境的窘迫,称家里再不及时送钱,自己就没有活路。信中连用三个“急”字表达对家中经济资助的迫切,十分生动。
朋友之间的书信在出土简牍中也较常见,居延汉简《宣与幼孙少妇书》(10·16A、B)是比较完整且研究较充分的一例。幼孙和少妇是夫妻二人,这封信是宣寄给他们夫妇的。[22]从简文看,宣和幼孙都是边塞的低级军官,两人关系密切。信中交待了一些边塞工作情况,其中涉及较高级官吏长史的动向。在信的最后,宣向幼孙透露了巡视边塞工作的“行兵使者”将要到达的消息,希望幼孙提前做好准备,不要在各部的评比中落后。这封信字里行间显示了宣对幼孙的袒护之情,是两人友谊的见证。
居延汉简《曹宣与董房、冯孝卿书》(502·14,505·38、43)也是一封朋友之间的来往书信。曹宣任职于驩喜隧,董房、冯孝卿任职于都仓,相距40余里。在信中,曹宣表达了由于职事繁忙不能经常去都仓与两位好友相见的遗憾之情。接着他又说,由于有人可以经常为自己捎来董房、冯孝卿的书信,使好友之间能“相问音声”,所以自己也能得到安慰,“意中快也”。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出董宣对友情的珍视。与《曹宣与董房、冯孝卿书》相似,东牌楼汉简《侈致督邮某书信》反映的也是朋友间的思念之情。侈自称“客贱子”,可能是一介布衣,他的朋友则是督邮,他们已很长时间没有相见。在信中,侈表达了自己“欲相从谈欢”的迫切心情,但同时表示由于自己生活贫困,“财自空乏”,所以“无缘自前”,并对此表示遗憾。这封东汉后期的书信,较有文采,侈用“别亭易迈、忽尔[至]今,轴磨年朔,不复相见”的语言表达了与朋友分别之痛,令人感动。此外,敦煌汉简《时致翁糸书》(1448号简)也应是一封朋友间的书信,写信人名时,收信人名翁糸,通篇内容是希望对方保重身体之类的客套用语,最后提醒对方有机会了别忘给自己写信。
事务性的请托、询问书信在出土简牍中占较大比例。居延汉简《给使隧长仁致范掾书》(157·10)是较完整的一例,写信人是第卅五隧长周仁,他曾经托候官范掾为自己“移自言书居延”。由于居延迟迟没有回复,他非常着急,所以再次致信范掾,让他为自己探听消息,并希望居延的回复文书下来后,范掾能催促候官负责人将其尽快传达给自己。敦煌汉简《兒尚致杨掾书》(244A、B)也是一封请托书信,兒尚在边塞服役已超期,盼望早日能回到故乡,所以致信候官杨掾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居延汉简《萧晏白李子真书》(35·20A、B)记述了萧晏通过书信向李子真求麴五斗的事件。而居延新简《敞致子惠书》(E.P.T51:23A、B)则是一封敞请求子惠帮助自己解决衣绔破烂问题的书信,解决方法是借子惠绔一二日,可能还希望子惠能借给自己一些钱财。
出土的事务性请托询问书信中包括一些经济生活材料。居延汉简《受致子丽书》(142·28A、B),是关于一桩木材买卖的书信,写信人是受,收信人名子丽。子丽曾经许诺帮助受做成一桩木材生意,现在到了木材价格高涨的时候,受写信催促子丽快点做成这桩生意,“必为急卖之”。从信的内容来看,作为中间人的子丽,如果生意做成是可以得到一笔经济报酬的。[23]
应酬往来的书信在出土简牍中也较常见。天长19号汉墓的墓主人谢孟,是西汉前期临淮郡东阳县一个较有权势的人,在其墓中出土有8封书信,内容主要是各地官民与他的应酬往来。与其交往的官员有东郡守丞贲且、东阳县丞莞横,普通人有丙充国、方被、幼功等。书信的内容主要是问病、致谢等应酬活动。以《方被致谢孟书》为例,方被在信中慰问了谢孟的病情,说自己本应该迅速到谢孟家探视,只是自己恰也染病在身,所以不能成行。他在寄信的同时,还让人捎去了一石米和一只鸡,并在信中嘱托谢孟一定要收下。居延、敦煌汉简中,也有不少这种本人不能前往而以书面形式问病、问安的信件,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居延新简中的一封宴请信,
戎具少酒:
谨请邑大夫官,仄中功、仄君都、谢敖等三人同食,五大夫幸临
戎,戎叩头幸甚幸甚。第七三大夫、第六三大夫、第五三大夫、第四三大夫、
第三三大夫谨会月廿四日日中,毋忽。 何君刑褚、刑房 E.P.T51:224B
“具少酒”是略备薄酒的意思,戎备酒宴请仄中功、仄君都、谢敖三人,希望第七三大夫等五个大夫也能到场陪客。这封信即是写给五位大夫的信,让他们在廿四日日中到达。信末尾的何君刑褚、刑房则是送信人的名字。
书信反映的人际交往很全面,有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也有朋友之间的交往,有工作上的交往,也有经济生活领域的交往,是我们了解古人社会交往的重要资料。
第三节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简牍材料,探索战国秦汉时人认识和应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方法,是简牍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 、婚姻和育子禁忌
客观来说,出土简牍中关于婚育的资料,并不是非常全面。但出土《日书》中有不少嫁娶、育子择日禁忌方面的材料,对我们了解时人在婚育方面的思想宗教观念,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作为人伦之始的婚姻和生育,在战国秦汉人眼中具有神圣地位,当时盛行的择日、占卜术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围绕着婚育展开。仅以篇名记,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生子》、《取妻》篇,乙种有《生》篇,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乙种有《生子》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汉简《日书》有《取妻出女》篇等。此外,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星》、乙种《官》等篇中也有相当多的婚育禁忌材料。
1.婚姻禁忌
请期是古代婚姻六礼之一。通过占卜等方式选择吉日成婚对秦汉人来说具有预定未来生活幸福与否的重大意义。据睡虎地秦简《日书》,在吉日成婚可以保障婚后夫妻生活的幸福美满;反之,在凶日成婚,则会有离异、贫困、夫亡、妻死等不好的后果。以甲种《取妻》篇为例,
取妻龙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戌亥。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
“龙日”即是“忌日”,显然不适合娶妻。从简文来看,时人在判断吉日时有经验主义倾向,将发生婚姻悲剧的牵牛织女成亲之日定为婚姻忌日,显然具有民俗学价值。除了《取妻》篇,《日书》甲种中还有很多内容与婚姻择日有密切关系,如
春三月季庚申,夏三月季壬癸,秋三月季甲乙,冬三月季丙丁,此大败日,取妻,不终。
凡取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娄吉。以奎,夫妻爱;以娄,妻爱夫。
戌兴<与>亥是谓分离日,不可取妻。取妻,不终,死若弃。
甲寅之旬,不可取妻,毋(无)子。虽有,毋(无)男。
“大败日”在数术系统中有很大影响,是不利百事的日子,婚姻也不例外。分离日以“分离”为名,显然不是结婚的良日。古人将60甲子按天干甲的出现分为十旬,甲寅是其中之一,在此时成亲无子、无男,显然与婚姻繁衍种族、延续后代的使命相悖。“奎”、“娄”,都是星宿名,在这里作为一种记日手段出现。据简文,在“奎”、“娄”日成亲,有助于夫妻恩爱。
时人不仅在婚姻上有择日禁忌,甚至在性爱上有时也须避开忌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曾提到每月上旬有一天“赤帝临日”,据说是赤帝开临下民并降殃之日,在这一天夫妻不能同房,如果违禁妄行,“其央(殃)不出岁中,小大必至”,如果行事时又“禺(遇)雨”,灾殃就会加速到来,“不出三月,必有死亡之志至”。行房,除了须考虑忌日外,秦汉时期还注意从养生的角度对其予以限制。张家山汉简《引书》记载,春夏时行房应在“从昏到夜大半”时进行,秋天应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冬天则“从昏到夜半”时进行,一定不能过劳伤气。不过,限制房事过劳并不意味着时人对行房有所排斥,相反,“秦汉时期两性之间欢娱的快乐感和合理性得到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一致认可”。[24]马王堆汉简《天下至道谈》强调:“先戏两乐,交欲为之,曰智(知)时”,并认为夫妻之间房事的和谐在促进家庭和睦方面有重要作用。
2.育子禁忌
和婚姻一样,战国秦汉时期的人们在生子日期上也有禁忌,这在传世文献如《史记》、《论衡》、《风俗通义》等著作中都有体现。如不举五月五日子的习俗,在战国时就已形成。[25]此外,还有“讳举正月、五月子”、[26]“不举父同月子”[27]等。参之出土简牍,可知当时关于生子的忌日还有更多。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生》篇说:“凡己巳生,勿举,不利父母,男子为人臣,女子为人妾。庚子生,不出三日必死”,明确指出己巳生子勿举,即使生下来,男子以后会成为奴隶,女子以后会成妾婢,于己于父母都不好。
当然,一方面由于生子后再“不举”从人情上来说并不容易做到,另一方面秦汉法律对于“擅杀子”有非常严厉的处罚规定。[28]所以《日书》中关于生子时日的内容更多是作为占卜此子未来的依据使用,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生子》篇“癸丑生子,好水,少疾,必为吏”的记载,即是对此子人生较长时间段各种情况的预测。秦汉时期的人相信不同时间生的子女拥有不同的未来。彭卫、杨振红先生曾概括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生子》篇,认为:“生子时日所决定后代的未来涉及从抽象的吉或不吉到具体的生活走向、从生理到能力、从性格到工作、从迁徙到人生终结等极为丰富的内容。”[29]
不仅从子女出生的时间可以判断吉凶,从新生儿的出生方位或分娩时的头向也可以,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有相关内容:
生东乡(向)者贵,南乡(向)者富,西乡(向)寿,北乡(向)者贱,西北乡(向)者被刑。
凡生子北首西乡(向),必为上卿,女子为邦君妻。
出土《日书》关于生子吉凶的占卜材料,对父母的未来关注不多,主要是围绕着子女展开,子女能否“为吏”、“有爵”、“富”、“美”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当时人对子女的未来非常关注,希望子女能够长寿、美丽、成才、富贵、做官。这些简牍虽是迷信的产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与期望。
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也有《生子》篇,但其内容与前述《日书》有别,主要是对从平旦到鸡鸣不同时辰产子是男是女的占卜。对子女性别的占卜反映了时人在产子之前对子女性别的重视和对某种性别的期待。结合传世文献,可能当时在某些人群中已经存在类似于后来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
二、养老
尊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精神贯穿于国家政策与民众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之中,至少在周代已成为当时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王朝由于尚首功、好战斗而“俗日败”,一度被认为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敬老、尊老的传统相悖,是中国尊老习俗的断裂带。然而通过近些年出土的秦代简牍可以发现,尽管民间尊老习俗在当时社会变革的冲击下曾发生过扭曲,以致有“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30]的讥议,但当时的国家法令和社会主流舆论并未放弃尊老,相反是对养老、敬老精神的珍视。[31]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明确写道:“孤寡穷困,老弱独传,均徭赏罚,傲悍 (戮)暴”,鼓吹“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殹(也)”,《法律答问》中也有“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的法律条文。并且秦律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子女则不得向官府告发父母的罪状,这无不反映了秦统治者对于孝道和尊老的重视。 (戮)暴”,鼓吹“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殹(也)”,《法律答问》中也有“殴大父母,黥为城旦舂”的法律条文。并且秦律明确规定父母对子女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而子女则不得向官府告发父母的罪状,这无不反映了秦统治者对于孝道和尊老的重视。
汉王朝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天下”,对尊老、养老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有清晰地认识,并不遗余力的通过政治和教化手段予以推行。两汉四百年间,在国家政策和儒家伦理观念的双重作用下,尊老、敬老观念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养老法令也一再被统治者颁布推行,社会上的养老、尊老风尚大为盛行。早在楚汉战争尚在紧锣密鼓进行中的公元前205年,刘邦就曾继承秦制设置有一定参政资格和政治权力的县、乡三老,其中县三老有“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的优待。之后,西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也都有根据年龄授王杖、赐酒肉、赐米帛、减刑等一系列制度上对老年人的优待,《汉书》中就收录有文景武宣时期的一些养老诏书。东汉对养老更为重视,《续汉书·礼仪志》载:“仲秋之月,县道各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国都南郊老人庙。”
近代之前,学界对两汉时期养老风尚的认识,主要得自对上述史料的理解。20世纪之后,大量当时尊老的实物见证——王杖[32]和不少包括一些皇帝养老诏令实物在内的反映汉代尊老、养老情况的简牍的出土,大大补充了我们对汉代养老政策和社会敬老风气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59年、1981年、1989年三次在甘肃武威的发现。1959年武威磨咀子18号汉墓出土一王杖和木简10枚。10枚木简属于一件册书,内容是西汉宣帝、成帝时期关于“年七十受王杖”的两份诏书和受杖老人受辱之后裁决犯罪者的案例,后被称为“王杖十简”。1981年在该地又征集到26枚木简,内容是有关尊老敬老、高年赐杖、处决殴辱受杖者的五份诏书,末简署“王杖诏书令”。1989年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残简17枚,内容都是东汉前期实用的律令条文,其中也有关于优抚老年人的内容。武威“王杖”简的发现,意义重大,不但印证了正史的记载,更提供了有关汉代养老风俗的第一手资料。“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提到了西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元延三年(前10年)的赐杖、养老诏书,并明确指出“哀怜耆老”、尊老养老是自高皇帝以来的政治传统。诏书称:“年七十以上,人所尊敬也”,规定了对受王杖者的敬养、保护条例以及对违令者的处罚原则。王杖“比于节”,受杖者享受相当于六百石官吏的政治待遇,经商可以免税,犯法可以宽免,“吏民有敢骂殴詈辱者”,以“逆不道”论处。除了受王杖者,诏书对其他60或70岁以上老年人的政治、经济优待也有提及,例如男女60岁以上无子男者即可享受“田毋租,市毋赋”的待遇,与归义的少数民族相同。不仅直接优遇高年耆老,政府还倡导全社会的敬老、养老之风,百姓有热心赡养孤寡老人的,也给予减免赋役的优待。“王杖十简”载:“高年受王杖……有旁人养谨者常养扶持,复除之”,“王杖诏书令”规定:“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鲲(鳏),女子年六十以上毋子男为寡。贾市毋租,比山东复。复人有养谨者扶持”,这些都是着眼于在全社会形成养老之风而出台的鼓励政策。[33]
除了武威王杖简外,其它汉代简牍材料中也有关于当时敬老、养老的记录。居延汉简有三老征收租税、协同地方长吏处理行政事务的事例,验证了《汉书》中关于县三老可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的记载。简中还提及当时张掖郡觻得县有“敬老里”,里以“敬老”为名更直接反映了当时尊老、养老的社会风尚。
江苏连云港尹湾6号汉墓的墓主师饶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其墓中有不少与当时地方行政相关的记录,其中一块木牍标题“集簿”,所记为西汉晚期东海郡的行政建置、吏员设置、户口、垦田和钱谷出入等方面的年度统计数字,研究者认为其应该是东海郡上计所用集簿的底稿或副本。牍中关于东海郡户口情况的记录中有与“王杖”相关的内容:
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九。
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十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
一个郡中受杖者多达2823人,充分反映了高年受杖、养老尊老政策在汉代严格执行,且受众庞大的情况。但这则材料同时也告诉我们在汉代并非年七十以上者皆可受杖,毕竟2823这个数字与东海郡七十岁以上者的数量还相差甚远。由此可知,汉代高年受王杖除了年龄须达到70岁以外,还当有其它条件。这些其它条件是什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张家山汉简汉律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线索。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中有汉初对于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老年人予以赐米、授杖、免除徭役等优待的法律条文,是我们研究汉初养老政策的重要资料。其中对高年受杖的规定如下:
大夫以上年七十,不更七十一,簪袅七十二,上造七十三,公士七十四,公卒、士五(伍)七十五,皆受仗(杖)
根据此律文可知,年龄不是受王杖的唯一资格,在考虑受王杖者的年龄时,须与其爵位联系起来,爵位越低,受王杖的年龄标准就越高,文献中“年七十以上受王杖”的话并非针对所有人。[34]这个认识的得来完全依赖于尹湾汉简和张家山汉简的出土。由此可见,简牍材料对于我们深入了解王杖制度,乃至汉代的养老风俗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三、医疗养生
延续生命长度,提高生命质量,是大多数人追求的目标。在上古时期,卜筮祷祠是古人用以消除病患的主要手段。春秋之后,随着科学及唯物思想的萌发,时人在继续重视卜筮祈禳的同时,开始注意到医学手段对治疗疾病、维护健康的重要意义,“巫”、“医”开始分离。此后,人们又逐渐认识到导引、房中等方技对养生的作用。到战国秦汉时期,医疗、养生无疑已是时人,尤其是贵族阶层关注的大问题,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书·艺文志》继承了西汉著名学者刘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方法,“总其书”而分为“七略”。其中以“论病”、“原诊”为主的“方技”书赫然与“六艺”、“诸子”、“诗赋”等并列,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36家868卷,蔚为大观,反映了当时医疗、养生活动的盛行。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的许多书志今天已成佚籍,流传下来的医书仅有《黄帝内经》等寥寥几种,较集中的医学史料也仅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汉书·方术列传》等几篇。幸运的是,随着近代考古材料,尤其是简帛材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对战国秦汉三国时期医疗卫生、养生保健的认识逐渐加深。1972年武威旱滩坡出土的载有30多个方剂的汉代医简,1973年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包含有大量医经、方剂、房中术的竹简帛书,1983年江陵张家山出土的竹简《脉书》、《引书》,是其中较为集中的发现。此外,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简牍中也有不少反映疾病、医药的材料,对探究医疗、疾病与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从疾病、医疗和养生几个方面,来谈谈简牍材料对认识古代医疗养生问题的重要意义。
1.疾病
疾病的感染,除了与患者本人的体质密切相关外,与患者的食宿习惯、社会交往和所处外部环境无疑也有紧密联系。探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域内居民的患病情况,对了解这一时期、这一地域居民社会生活的基本情况,有重要意义。传世文献中关于疾病的记载很少,而近代出土的简牍中有不少关于疾病名目和病征的内容,补充了这方面的材料。
早在1914年,罗振玉根据英籍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简牍而作的《流沙坠简》一书中,就曾关注过“医方简”,有“治久欬逆匈痺痿痺止泄心腹久积伤寒方”的记载。
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前期墓中出土了92枚医简,内容是作者长期临床实践记录的总结。其中完整方剂30多个,保存有对疾病症状、病名、病因的详细描述。其包括久咳上气、气逆、喉中如百虫鸣、声音嘶哑、鼻不利、懑、头痛、胁痛、腹胀、臃肿、便血、小便难、金创出脓血、胫寒、橐下痒、不仁等各种症状。涉及内、外、妇、五官等临床科,属内科的疾病有伤寒、七伤、大风、痹症、伏梁、久泄、肠辟、痉、心腹大积等;属外科的有五癃、金创、痈、狗噬人等;属妇科的有乳余;属五官科的有目痛、喉痹、嗌痛、齿痛、耳聋、(鼻)息肉等。[35]有的医方对某些疾病的症状描述相当详细,如“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治心腹大积上下行如虫状大痛方”等,反映了时人对疾病诊治的审慎;有的医方对疾病的划分则相当细密,如同是“金创方”,当时即有“治金创止痛令创中温方”、“治金创内漏血不出方”、“治金创止痛方”、“治金(创)肠出方”的区别,反映了时人在疾病认识方面的进步。而对于男子的“内伤”病,医简“白水侯方”更是根据具体病征将其分为“七疾”、“七伤”,分别予以辨正治疗,在疾病划分与症状描述方面尤其详尽。武威汉代医简充实了学界对秦汉时期居民常患疾病和治病方法的认识,有重要史料价值。
20世纪出土的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主要内容是关于汉代西北地区屯戍生活的,其中也包含有不少戍边士卒的患病信息,对我们了解汉代,尤其是西北边陲的疾病情况有所帮助。汉代西北边塞的行政文书中有作为病假报告的“病书”和伤病人员名单的“病名籍”,其中涉及病名和症状的记录,如居延汉简:
第廿四隧卒高自当以四月七日病头恿四节不举 鉼庭隧卒周良四月三日病苦
第二隧卒江谭以四月六日病苦心服丈满
第卅一队卒王章以四月一日病苦伤寒 第一隧卒孟庆以四月五日病苦伤寒 4·4A
第卅七隧卒苏赏三月旦病两胠葥急少愈
第卅三隧卒公孫谭三月廿日病两胠葥急未愈
第卅一隧卒尚武四月八日病头恿寒炅饮药五齐未愈 4·4B
即是一则“病名籍”。居延和敦煌简中也有一些散见的病历及医方,对研究疾病的种类、特点,同样有参考价值。仅以居延汉简计,其所涉及的病症,至少就有伤寒、头痛、四节不举、病心腹、痈种(臃肿)、肠辟、带下等内、外、妇科疾病20余种。[36]西北汉简除了有对疾病本身的记载,还有不少关于屯戍地区医疗管理制度的内容,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边塞地区的医药卫生情况及医疗保健制度。
武威和居延、敦煌汉简主要反映了汉代西北地区的医学实践,而关于中原及南方地区居民的疾患情况,则可以参考张家山汉简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相关记载。张家山汉简《引书》和《脉书》是汉初的医学文献,《引书》记载了40余种疾病,《脉书》依从头至足的顺序排列了60余种疾病,涉及内科、外科、五官科、妇科、小儿科等。走马楼吴简主要反映了汉末吴初长沙郡的社会生活、经济关系,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疾病信息。从简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长沙郡吏民主要受“腹心病”、“肿足”、“盲目”等病患的威胁。此外,2009年北京大学所收藏的西汉竹简中,有700余枚医书简,其内容涵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多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价值巨大。
2.医疗
出土简牍不仅提供了大量疾病信息,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两千多年前古人征服、治疗疾病的手段。其中既有理论性的医经,如论述人体经脉走向及所主病症的张家山汉简《脉书》,也有实践性较强的治疗方法。据出土简牍,战国秦汉时期治疗疾病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针灸治疗、导引治疗和神秘主义手段等。
药物是当时主要的医疗手段,出土简牍中涉及药方的主要有关沮周家台秦简、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和汉简、武威医简、张家界古人堤遗址木牍、西安未央宫遗址汉简、悬泉汉简,及居延、敦煌简等。周家台秦简中有去黑子方、已龋方、治痿病方、治病心方。古人堤遗址出土两块医方木牍,较完整的1块是“治赤谷方”,研究者通过对所记药物的分析,认为其应是治疗外感风寒、食谷不化、便溏泄泻的药方。居延汉简有以贝母、桔梗入药的“治除热方”,敦煌汉简有以人参、昌蒲、姜桂、蜀椒、细辛、乌喙等入药的“治久欬逆匈(胸)痹痿痹止泄心腹久积伤寒方”。北京大学所藏汉简内容类似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含有“秦氏方”、“翁壹方”等珍贵药方,对药物的炮制和服用方法有较多介绍。武威医简的药方材料非常丰富,有“治百病方”和“白水侯方”等,涉及药物有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计100多味,并对药物的炮制,用药的时间、剂量、方法、禁忌有详细说明,是关于汉代药物学的重要资料。从出土简牍来看,汉代的药物制剂既有用于口服的丸药、散剂、汤剂,也有用于外敷的“千金膏药方”、“百病膏药方”,以药物治疗疾病的方法已比较完善。
针灸治疗是传统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秦汉时期已比较流行。武威医简19至21号简治腹胀病的材料即是一则以针灸治疗疾病的实例,其强调在用针灸治疗由于寒气在胃莞(脘)而导致的腹胀时,应先刺三里穴,再刺肺输穴,对针刺深度、留针时间都有明确规定。简文对针灸的疗效也有记述,“后三日病愈平复”,说明了针灸在治疗这种腹胀病时奏效快捷。医简还提到了针灸时的禁忌,对小儿和老年人的针灸部位有详细规定。除了武威医简,居延简中也有关于针灸治病的零星记载,如“□□久胫刺廿针”(159·9A),“左足癃□刺”(E.P.T56:339)等。
导引是通过呼吸吐纳、屈伸俯仰、活动关节而健身、养生的方法,类似于今天的气功。秦汉时期的人们已认识到合理的运动在身体保健、疾病治疗方面的作用,张家山汉简《引书》即是一部专门讲述导引的著作。《引书》记载了利用导引术治疗内瘅、项痛、病肠、踝痛、膝痛、北(背)甬(痛)、要(腰)甬(痛)、心痛、腹张(胀)、目痛、龋等44种疾病的方法,对动作的解说相当细致。导引对一些疾病的治疗,与今天的医学理论有相似之处,反映了当时医疗技术的先进,如对龋齿的治疗,《引书》载:“学(觉)以涿(啄)齿,令人不龋。其龋也,益涿(啄)之。”这种睡觉醒来叩击上下牙齿以预防龋齿的方法,两千多年前的先民已经掌握,确实值得称道。和导引类似的治疗手段还有推拿按摩,武威医简对“膏摩”法有所介绍,其先用千金膏药外涂肌肤的一定部位,然后再施以按摩,结合了“涂药”和“按摩”两种治疗手段,是当时医疗技术进步的体现。
战国秦汉时期,占卜、祷祠等神秘主义的治疗方法,在社会上仍有一定市场,这与时人对疾病的认识有关。从出土的战国秦汉《日书》来看,当时的人仍部分具有疾病来自于鬼神作祟的观念。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病》篇载:“庚辛有疾,外鬼伤(殇)死为祟”,即是说庚日、辛日得病是由于外死之鬼和殇死之鬼作祟。《诘》篇载:
人毋(无)故一室人皆疫,或死或病,丈夫女子隋(坠)须(鬚)羸发黄目,是宲宲人生为鬼。
人得了能致死或掉头发胡须、黄眼睛的病,是由于化作小孩的疫鬼作祟。既然得病来自于鬼,那么治病的手段显然也要与解除鬼的影响有关。从出土简牍来看,主要有祷祠祭祀和驱鬼等办法。
以卜筮祷祠的方式治疗疾病在春秋战国时期相当普遍,《左传》中即有相关内容。在出土简牍里,以望山1号墓、包山2号墓和新蔡平夜君成墓出土楚简最具代表性。这三座墓的墓主都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高级贵族,墓中都有以询问、治疗疾病为主要内容的占卜、祷祠竹简。以望山楚简为例,墓主 固有心病及足骨病、胸疾、首疾等病患,不能饮食。其卜筮的内容主要与占问疾病吉凶有关,祭祷简则记述了 固有心病及足骨病、胸疾、首疾等病患,不能饮食。其卜筮的内容主要与占问疾病吉凶有关,祭祷简则记述了 固用佩玉、酒食、猪马牛羊等物祭祀楚国的先王及后土、司命、大水、山川等神灵,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治病驱祟。秦简也有通过祷祠、祭祀的手段驱除疾病的记载,睡虎地秦简日书《病》篇所载的治病方式主要就是先通过占卜确定是某一鬼神作祟,然后用“酢”即报祭的方式禳除病患。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也有以占卜治病的内容,被称为“占病”、“占疾”或“卜来问病”,其祭祷的对象主要有天、社、人鬼、司命等。到汉代,虽然以药物等科学方法治疗疾病已成为主流,但民间社会仍存在祷祠的治病手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汉代简牍中有纪年为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序宁简”,记载“皇母”因守丧致病,“皇男皇妇皇子”等人即通过向炊、造(灶)君、社、郭贵人、殇君、水上、祠命君等神灵祷祠的方式祈求病愈。 固用佩玉、酒食、猪马牛羊等物祭祀楚国的先王及后土、司命、大水、山川等神灵,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自己治病驱祟。秦简也有通过祷祠、祭祀的手段驱除疾病的记载,睡虎地秦简日书《病》篇所载的治病方式主要就是先通过占卜确定是某一鬼神作祟,然后用“酢”即报祭的方式禳除病患。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也有以占卜治病的内容,被称为“占病”、“占疾”或“卜来问病”,其祭祷的对象主要有天、社、人鬼、司命等。到汉代,虽然以药物等科学方法治疗疾病已成为主流,但民间社会仍存在祷祠的治病手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汉代简牍中有纪年为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的“序宁简”,记载“皇母”因守丧致病,“皇男皇妇皇子”等人即通过向炊、造(灶)君、社、郭贵人、殇君、水上、祠命君等神灵祷祠的方式祈求病愈。
对于因鬼神作祟所患之病,除了通过祭祷的方式治疗外,还有采取强硬手段驱除、攻击甚至屠杀恶鬼的治病方式。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中有不少相关记载,如:
(1)一室人皆养(痒)体,疠鬼居之,燔生桐其室中,则已矣。
(2)一室中卧者眯也,不可以居,是□鬼居之,取桃枱〈棓〉椯(段)四隅中央,以牡棘刀刊其宫蘠(墙),謼(呼)之曰:“复疾,趣(趋)出。今日不出,以牡刀皮而衣。”则毋(无)央(殃)矣。
第一例中疠鬼使人身体瘙痒,对付疠鬼、去除病患的办法是在室中燔烧桐木。第二例对付“□鬼”的方法较为复杂,使用了桃木、牡棘刀等工具,采取了祝由术等恐吓鬼的办法。这种利用巫术、祝由治病的方式,在汉代还很盛行,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有不少相似内容,可参看。
3.养生保健
马王堆汉简《十问》称:“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这段对话借尧舜之口表达了战国秦汉时期人们对长生、健康的追求。如果说生病后予以治疗是消极的养生之道,那么在疾病来临之前,通过各种方式避免疾病、延长生命无疑是更积极的养生手段。战国秦汉时期已有不少关于养生保健的著作,从出土文献来看,长沙马王堆汉墓、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简牍、帛书及张家山汉简《引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下面我们即利用相关简牍材料,对当时流行的养生保健手段予以简单介绍:
第一,良好的生活习惯。张家山汉简《引书》开篇首先阐述了一年四季的养生之道,强调人的饮食起居和性生活需要适应自然界“春产、夏长、秋收、冬臧(藏)”的运行规律,并将之视为可以延年益寿的“彭祖”之道。《引书》所载应予以遵守的生活习惯,很多符合今天的保健常识。如春夏应早起,起床后小便、洗漱,在室前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喝一杯水;夏天要多洗头,少洗澡,多吃蔬菜;秋天应多洗澡洗头,饮食和房事应以身体适宜为限;冬天应晚起,要注意脚和身体的保暖,而手和脸则可以适当保持寒冷等等。
第二,类似于气功和仿生运动的导引术。张家山汉简《引书》以导引为主要内容,除了介绍导引在疾病治疗上的功用外,更多是将导引作为一种养生保健手段。据高大伦先生研究,《引书》中有导引术式65个,包括徒手导引、器械导引、仿生导引、两人合作进行的导引和呼吸导引五大类型。马王堆汉简《十问》“黄帝问于容成”章和阜阳双古堆汉简《行气》篇主要讲“行气”的功能与方法,属于呼吸导引的范畴。其强调人们应根据天地阴阳气候昼夜的变化规律“吐故纳新”,晚上吐出对身体不利的“宿气”,早上吸取新鲜、利于养生的“新气”,从而使九窍通达、六腑健康。
第三,服食药饵。以服药的手段追求益寿延年,甚至长生,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上层社会中并不鲜见,著名者如秦始皇。阜阳双古堆汉简《万物》中包含此类内容,其记述了通过服食乌喙、蜘蛛、牛胆等物,可以使人具备疾行善趋、明目登高、潜水行水、控制寒热等功能。
第四,房中术。《汉书·艺文志》载:“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作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可见秦汉时期,人们已注意到两性之间的交合对生命保健的重要意义。当时出现了一些对两性之间性生活予以指导以使之能促成养生保健的书籍,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就有8家186卷。马王堆汉墓出土简帛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其中竹简主要有《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四种。《十问》是关于“养阳”的方法,其中包括在行房时应注意的服食、行气、导引、按摩之术,如“黄帝问于曹熬”章主要是讲一种叫“玉闭”的固精法,其认为在性交时如果能长期做到闭精勿泄,即可达到“虚者可使充盈,壮者可使久荣,老者可使长生”的效果。《合阴阳》和《天下至道谈》是关于性交技巧的著作,也涉及不少有关房中的养生之道。《杂禁方》主要是关于巫诅禁咒的内容,但其中半数文字涉及房中,尤其对妇人“媚道”介绍较详。
四、先令券书——古代的遗嘱
老、病的最终结果是死亡。濒亡者在临终之际嘱咐身后事务的话或文书就是遗嘱。遗嘱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而秦汉时期的遗嘱一般被称为“先令”。《汉书·景十三王传》载,赵缪王刘元“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颜师古注曰:“先令者,预为遗令也。”秦汉时期,重视孝道,临终者合乎法律规定的意愿一般能得到国家和子女的重视,“先令”在丧事安排、财产分割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载:“民欲先令相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有争者,以券书从事;毋券书,勿听。所分田宅,不为户,得有之,至八月书户,留难先令,弗为券书,罚金一两”,制作先令券书须有乡部啬夫在场,其在分割遗产上具有权威性,不得留难。
传世文献中,对汉代的遗嘱有一些记载,如文帝临终前的薄葬遗诏、杨王孙的裸葬先令等。但传世文献仅记先令的内容,对于先令的制作形式语焉不详。1984年江苏仪征胥浦101号汉墓出土了一份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的先令券书的抄件,极大充实了学界关于汉代先令券书的认识。此先令记述了制定者朱凌在临终之际向6位同母异父子女交待生父,并分配田产的情况。先令由“县乡三老,都乡有秩、佐,里师田谭”等各级行政部门的官员根据朱凌的意志制定,有“里师、伍人谭等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在现场担任见证人,符合“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的法律规定,“可以从事”。对比张家山汉简《户律》的规定和胥浦券书的内容,可以发现从汉初到西汉后期,政府对“先令”这种反映临终者意志的文书的支持和规范几乎没有改变。
五、丧葬风俗
作为一个重视伦理、强调孝道的社会,战国秦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为了给父母办一个体面的丧礼,人们不惜“糜破积世之财”,以致当时就有“财力尽于坟土”的说法。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丧葬习俗自然向繁琐化、奢侈化发展。关于汉代的丧葬风俗,传世文献有较多记载。简牍中虽有涉及丧葬习俗的内容,但并不全面,本节拟从择日、遣策、告地策等角度简述出土材料对秦汉时期丧葬习俗研究的意义。
人死后需要埋葬,而在葬日的选择上,秦汉时期有一定禁忌,《论衡·讥日》引《葬历》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刚柔,月之奇耦”,可见《葬历》即是流传于汉代的一种选择葬日的文献。1990年至1992年发掘的悬泉汉简中有部分《日书》残简,其中有以《葬历》为篇目者,内容确是关于葬日选择。在较完整的出土材料中,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都有丧葬择日的内容,《日书》甲种载:“葬日,子卯巳酉戌,是胃(谓)男日;午未申丑亥辰,是胃(谓)女日。女日死,女日葬,必复之。男子亦然。凡丁丑不可以葬,葬必参。”丧葬时间与死亡时间密切相关,如果死者死于午未申丑亥辰等女日,而又在女日下葬,家中就会再次发生死亡事件;反之,死于男日的死者在男日下葬也会再次导致家中死亡事件的发生。至于丁丑日更是不可以下葬的凶日,如果在这天下葬,就会三次发生死亡。
战国秦汉时期,厚葬盛行,墓中往往有很多包括亲友赠送物品和死者生前使用物品在内的随葬品,用来记载这些随葬物品的清单被称为“遣策”。目前所见遣策,战国楚简和汉简中较多,以仰天湖楚墓、长台关1号楚墓、望山2号楚墓、包山2号楚墓、曾侯乙墓、谢家桥1号汉墓、马王堆1号和3号汉墓、凤凰山汉墓出土的最具代表性。出土遣策的秦代墓葬较少,主要有江陵杨家山135号秦墓。遣策内容丰富,是探讨古代丧葬风俗的重要史料。从其记载可以看出钱财、食物、服装、乐器、器具等生活用品,以及偶人、车马是战国秦汉时期的主要随葬物品。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遣策竹简312枚,3号汉墓出土410枚,仅从遣策简的数目,即可想象当时贵族墓葬中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有些贵族墓葬墓室众多,而遣策简有时也分别出于不同的墓室之中。如包山2号楚墓的遣策即分为四组,分别放置在东室、南室、西室等处,其记载与各室中的随葬品基本相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相关遣策的研究,探讨各个墓室在整个墓葬中的作用,进而促进有关古代墓葬制度的研究。古代丧葬中有较严格的用车制度,曾侯乙墓遣策内容主要即是关于车马和兵器的,其记载了用于葬仪的车马以及车上配件、武器、甲胄和驾车官吏,对丧葬用车制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相信地下世界存在的思想观念在秦汉时期仍较普遍,出土简牍中有种叫“告地策”的文书反映了时人在丧葬时对人间与阴间的沟通。告地策,又称告地书、告地状,书写于木牍或竹牍之上,埋葬在墓葬里,主要是死者家属或死者申请将死者户籍以及奴婢、车马等随葬物迁移到地府的报告。从出土实物来看,其行文格式类似于“过所”等官文书,一般由地方基层官员转呈给地下丞、地下主、土主等虚拟的地府官吏。以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出土的告地书为例:
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乡燕、佐戎敢言之:库啬夫辟与奴宜马、取、宜之、益众,婢益夫、末众,车一乘,马三匹。
正月壬子,桃侯国丞万移地下丞,受数毋报。定手
此例死者为库啬夫辟,先由乡级官员将其户籍及奴婢、车马报告给县级官员,然后由县级的桃侯国丞转呈地下丞,完成了库啬夫辟户籍、物品由阳间向阴间的交接。出土告地策中也有少量由死者本人亲自向地府官员呈报的情况,如凤凰山10号汉墓所载,
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伥(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祭)具器物。各会令以律令从事。
虽然向地下官吏呈报户籍、葬物是告地策主要内容,但也有个别以为死者解除狱事为目的告地策,如江苏邗江胡场5号汉墓竹简载,
卌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广陵宫司空长前、丞□敢告土主:广陵石里男子王奉世有狱事,事已,复故郡乡里,遣自致,移栺穴。卌八年狱计,承书从事,如律令。
广陵宫司空是负责刑徒管理的官员,在王奉世死后,其向地府土主说明狱事已了,应含有希望死者在阴间能过上正常人生活的意思。
目前所见告地策文书将近10件,大部分发现于西汉初年的江陵附近地区,[37]以高台18号汉墓、凤凰山168号汉墓、谢家桥1号汉墓、随州孔家坡8号汉墓所出最为典型。它们对研究古人的鬼神观念和宗教意识有重要作用,值得重视。
第四节 民间信仰
一般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包括官方宗教和民间信仰两大部分,其中民间信仰与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密切相关。简牍作为主要书写材料的先秦秦汉时期,恰是中国古代民间宗教从萌发到盛行的时代,当时民间社会流行着大量的神秘主义信仰和鬼神、术数之道。这些信仰以文字形式保存于出土简牍之中,为探讨当时的民间鬼神观念和术数方技提供了珍贵资料。
一、鬼神世界
出土简牍中有不少属于“卜筮祷祠”和《日书》的内容,它们勾勒出了战国秦汉时人所信奉的鬼神世界以及祭祀、祷祠手段。
传统认为,楚人信巫鬼、好淫祀,通过包山楚简、望山楚简、天星观楚简、葛陵楚简中关于“卜筮祷祠”的记载以及九店楚简《日书》,可看出其说有据。卜筮祷祠简主要是墓主贞问吉凶祸福,并通过祷祠鬼神以求禳除灾祸的记录。从其卜筮的对象,可以看出楚人信仰中鬼神世界的构成。葛陵楚简将当时信奉的神祇统称“上下内外鬼神”,大概包括天神、地祇和人鬼,人鬼根据与墓主有无血缘关系,又可分为内鬼和外鬼。大体来说天神、地祇主要有“太”,诸司神,司地的后土、社、地主、宫后土,作为“五祀”的行、大门、户、灶、室,大水,五山,高丘,以及方位之神等。“太”即文献中的“太一”,是诸神之首。诸司神包括司命、司祸、司录、司折、司祲、司差、司佗、司救等,它们的执掌与人们的生老病死有关,属于职能神范畴。人鬼中的内鬼是楚国贵族祷祠的主要对象。包山楚墓、望山楚墓、葛陵楚墓的墓主都是与楚王有血缘关系的公族,他们祭祀的内鬼包括“楚先”、“荆王”、“文王以就”、“五世王父”、“三世之殇”等。“楚先”又称“三楚先”,是楚人的三位先祖,包括老僮、祝融、鬻熊。“荆王”是从熊丽到楚武王的楚国早期国君。“文王以就”指从楚文王到卜筮前最后去世的一位楚王。“五世王父”是卜筮者父辈以上的五代先人。“三世之殇”则指卜筮者三代以内夭死的亲属。[38]《左传·僖公十年》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这一祭祀原则在楚简中也有体现,天星观1号楚墓的墓主是邸阳君番乘,其祷祠“番先”,祭祀自己的先人章公、惠公,而不提“楚先”,也不提“荆王”及文王以后的任何一位楚君。对内鬼的祭祀,反映了当时盛行的祖先崇拜。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载:“祠父母良日,乙丑、乙亥、丁丑亥、辛丑、癸亥,不出三月有大得”,专门指出了祭祀父母的良日,可见其在当时的流行。
今天所见的“卜筮祷祠”简多是楚国上层贵族所用,而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日书》则更多反映了当时秦、楚基层社会的宗教、鬼神信仰。《日书》作为择日书籍,有很多选择祠祀、祭祀良日的记载,反映了时人对于祭祀的重视。睡虎地秦简《日书》神鬼系统与楚墓“卜筮祷祠”简相似,神祇有帝、上下群神、田亳主、杜主、雨师、田大人,及包括灶、行、门、户、室中在内的“五祀”等。人鬼既有“外鬼殇死”,也有包括故去的父母、祖父母在内的内鬼,以及死去的前贤如女果(女娲)、史先等。[39]放马滩秦简《日书》中有天、社、巫帝、五音、六律、阴雨公、天兽、大水、司命、人鬼、大父及殇等上下内外神祇。其《墓主记》还有“司命史”,应是模仿人间的官职体系为“司命”创造的属吏。
除了受人尊敬的神祇外,当时民间信仰中还盛行各色鬼怪,《日书》对它们有较多介绍,尤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为代表。《诘》篇生动描述了40多种鬼怪的活动形态。其中既有凶残、暴虐的刺鬼、棘鬼、凶鬼、暴鬼、疠鬼,也有较为可怜的哀鬼、饿鬼、衣乳之鬼、遽鬼。既有与动物有关的类似后世物怪性质的神狗、会虫、女<母>鼠,也有具有灵性能加害人的自然现象如雷、云气、野火、寒风、票风等。这些鬼怪的行为、性情与人颇有相似之处,有的鬼有穿衣、吃饭、居住、性生活等生理需要,有的鬼有游玩、交友、爱情等精神需要,甚至还有爱与人开玩笑、戏弄人的 鬼。丘鬼喜欢践踏人的房屋,阳鬼会使人煮不熟饭,暴鬼喜欢责怪人,而作为无家之鬼的哀鬼则喜欢与人交往,对人纠缠不休。夭鬼常无故对人馈赠,饿鬼和鬼婴儿则常向人乞讨, 鬼。丘鬼喜欢践踏人的房屋,阳鬼会使人煮不熟饭,暴鬼喜欢责怪人,而作为无家之鬼的哀鬼则喜欢与人交往,对人纠缠不休。夭鬼常无故对人馈赠,饿鬼和鬼婴儿则常向人乞讨,
凡鬼恒执匴以入人室,曰:“气(饩)我食”云,是是饿鬼。
鬼婴儿恒为人号曰:“鼠(予)我食。”是衣乳之鬼。
这些鬼怪的行为,显然具有较强的世俗化倾向。
大部分鬼怪会凭借其神通给人带来种种危害,至少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1)导致瘟疫或死亡;(2)导致疾病;(3)使人无缘无故失踪;(4)使人做恶梦;(5)骚扰、戏弄人;(6)使人行为失常;(7)抢走或破坏人的财产。[40]当然,人在这些世俗化的鬼怪面前也并非束手无策,可以通过祭祀、驱逐、攻击、药物等方式消除其影响,甚至可以将一些物怪屠杀并吃掉,《诘》篇载:
狼恒呼人门曰:“启吾。”非鬼也。杀而享(烹)食之,有美味。
一室人皆毋(无)气以息,不能童(动)作,是状神在其室,屈(掘)遝泉,有赤豕,马尾犬首,亨(烹)而食之,美气。
《诘》篇的目的本来就是教授普通人一些驱鬼辟邪的方法,其内容反映了时人在对付鬼怪方面的主观能动作用。
秦汉时期人们的鬼神观念与战国时期差别不大,里耶秦简中有祭祀先农、穴、隄等神灵的记载,居延简中有“祠社稷”的记载。这些祭祀已多由地方行政机构主持,可能与秦汉政权打击私人淫祀有关,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就有“擅兴奇祠,赀二甲”的法律规定。当然,这些祭祀虽属于官方宗教的范畴,但其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的信仰风俗。邗江胡场5号汉墓出土有记录神灵名的木牍,反映了汉宣帝时期江淮地区的鬼神信仰情况,其中主要有仓天、天公、上蒲神君、神魂、石里神杜(社)、石里里主、水上、江君、淮河、吴王、大王、荆主、高邮君大王、满君、中外王父母等。牍中既有仓天、神社等天神地祇,也有江君、淮河等山川神灵,还有吴王、大王、中外王父母等内外人鬼,其神鬼体系与战国时期的一致性非常明显。
二、数术
数术是中国古代研究“天道”的学问,其以各种方术观察自然现象,进而推测人和国家的命运,与民间信仰有密切关系。作为民间社会的实用之术,数术类文献数量庞大,《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收录著作190家2528卷,蔚为大观。近代以来出土的简牍材料中,此类内容也占有较大比例,尤以九店楚简、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关沮周家台秦简、银雀山汉简、阜阳双古堆汉简、随县孔家坡汉简、尹湾汉简、永昌水泉子汉简的材料较为集中。
数术的内容包罗万象,对时人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产生过较大影响。现以卜筮、择日、占梦、相术为例,根据出土简牍内容择要简述如下:
1.卜筮
龟卜和筮占是中国古代盛行的占卜之术,前者通过观察龟甲及动物骨骼被灼后的裂纹判断吉凶,后者是以蓍草为占具的卜术。它们来源于用“动物之灵”或“植物之灵”作媒介沟通天人的原始崇拜习俗,从考古材料看,至少可以追溯至夏商时代。[41]卜筮在商周时期极为盛行,据商代甲骨可见,当时举凡祭祀、战争、田猎、捕亡、行旅等事必以龟卜。而相传文王演《周易》,也说明了筮占的影响之广。东周之后,随着科技知识的进步,以星占、式占为代表的占卜方法流行,卜筮的地位受到一定影响,但仍是当时数术领域的重要流派,可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42]《史记》有《龟策列传》,说明其地位至汉不衰。
从出土文献来看,包山、望山、葛陵、秦家咀、天星观等楚简中的“卜筮祷祠”简,很多就包含龟卜、筮占的记录,其内容、形式与商周时代的卜筮有明显一致性。这些竹简一般是卜、筮并用,占卜频率很高,有连日占卜者,也有一天内连续占卜者。它们不但记录龟卜、筮策的名称,有时还记有卦画,对我们了解战国时期民间的占卜数术有重要价值。以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54枚卜筮祷祠简为例,其内容与贞问吉凶祸福有关,占卜之事主要有何时获得爵位、疾病能否好转和侍王是否顺利等。包山卜辞有固定格式,其前辞、命辞、占辞,与甲骨卜辞相类,但占辞后一般还有祷辞和第二次占辞,则与甲骨卜辞不同。前辞包括卜筮时间、贞人名、卜筮名称和请求贞问者的姓名。命辞是贞问事由,如“既有病,病心疾,少气,不内飤,尚毋有恙?”即是一则贞问心疾会不会严重的命辞。占辞是根据卜筮结果做出的判断,“恒贞吉,庚辛有间,病速瘥”条说庚辛这一天病会好转并迅速痊愈,就是判断的结果。在占的过程中,用卜或用筮,分别据“兆”或卦象加以判断。如果占辞中含有凶咎,则要有祷辞(或称敚辞),以向鬼神祈祷,请求保佑或解脱忧患。祭祷鬼神之后,再进行第二次占卜,产生第二次占辞。[43]如
东周之客许裎归胙于载郢之岁,远 之月癸卯之日,苛光以长恻为右(左)尹邵 之月癸卯之日,苛光以长恻为右(左)尹邵 贞,病腹疾,以少气,尚毋有咎。占之,贞吉,少未已,以其古(故)敚之。 贞,病腹疾,以少气,尚毋有咎。占之,贞吉,少未已,以其古(故)敚之。 (荐)于野地主一 (荐)于野地主一 (豭),宫地主一 (豭),宫地主一 ,赛于行一白犬、酉飤,占之曰:吉, ,赛于行一白犬、酉飤,占之曰:吉,  (刑夷)且见王。 207—208 (刑夷)且见王。 207—208
即是一个完整的卜筮辞例。前辞中有具体时间,并点明是苛光为邵 贞,命辞说明贞问原因是腹疾。由于占辞中的结果不是非常理想,所以又以豭、白犬、酒食向野地主、宫地主和行等神灵献祭,之后第二次占卜,结果为吉。 贞,命辞说明贞问原因是腹疾。由于占辞中的结果不是非常理想,所以又以豭、白犬、酒食向野地主、宫地主和行等神灵献祭,之后第二次占卜,结果为吉。
卜筮祷祠简,不仅提供了卜筮的完整体例,还有关于卜筮所用材料、贞人地位、贞问时限、卜筮作用的内容,史料价值巨大。
2.择日
在科学知识、认识水平有限的古代,人们行事中禁忌颇多,这样就促成了择日之术的出现与发展。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上活跃着一种名为“日者”以“占候时日”为业的群体,流传着一种将各种举事宜忌按历日排列、令人开卷即得、吉凶立见、即使没受过训练的人也可轻松掌握的《日书》。20世纪以来,战国秦汉《日书》简牍大量出土,加强了我们对择日这种古代数术的认识。
《史记·日者列传》载褚先生曰:
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可见择日的具体方法有很多,至少包括五行、堪舆、建除、丛辰等七种。睡虎地和放马滩秦简《日书》中的《除》、《秦除》和《稷(丛)辰》等篇,分别属于建除家和丛辰家的择日理论。
出土的较完整《日书》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时日为纲,选择之事为目;另一部分则以选择之事为纲,吉凶之日为目。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为例,其《除》、《建除》、《稷辰》等篇属于前者,而《衣》、《行》、《归行》、《到室》等篇则属于后者。
择日主要是确定某日宜于做某事,或不宜于做某事。其所涉及的日常生活范围很广,除了前面介绍过的婚姻、生子、出行、祭祀、请谒、建房择日外,农事、制衣、迁徙、求人、入官府、捕盗、杀牲、登记户籍、讨债、看望病人、加冠、逃亡、贸易、伐木等活动也都需要择日而行。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载,
四月中不可伐木。 100二
□未、癸亥、酉、申、寅,五月中不可之山谷采以材木及伐空桑。305
即是关于伐木的择日情况。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载,
毋以辛酉入寄者,入寄者必代居其室。己巳入寄者,不出岁亦寄焉。
57正三、58正三
如果辛酉日接纳来家里寄居的人,寄住的人肯定会霸占主人的家产;如果己巳日接纳来家里寄居的人,不出一年自己也会变成寄居者。辛酉和己巳日显然是接纳寄居者的忌日。
除了具体针对做某事的吉日、忌日外,还存在一些适合做很多事的良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秦除》篇载,
建日,良日也。可以为啬夫,可以祠。利枣(早)不利莫(暮)。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车。有为也,吉。 25正一
其中每月的“建日”就是良日,做很多事都吉利,适合当啬夫、祭祀、买入奴隶、加冠、乘车出行。
关于吉日或忌日的确定,除了由五行、建除、丛辰等具体方法推导外,有时还受所谓历史经验或天神信仰的影响。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载,
癸丑、戊午、己未,禹以取梌(涂)山之女日也,不弃,必以子死。 2背一
壬申、癸酉,天以震高山,以取妻,不居,不吉。 7背一
由于禹与涂山氏的爱情悲剧,所以禹娶涂山氏的日子被认为是娶妻忌日,如果这日娶妇,女方即使不被抛弃,所生孩子也会死去。同样,天神用雷电震坏高山的日子,也不适合婚配。此外,据睡虎地秦简《日书》,在帝盖房的日子,人们不能盖房;在赤帝降临人间的日子,百事不利;在神修缮房室的日子,不可筑墙;在田亳主、杜主、雨师、田大人等田神死去的日子,不能第一次耕田和破土动工。
《日书》包含的社会内容非常丰富,除了择日外,还可以根据某些事发生的时间判断其结果,类似于一种占卜方法。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盗者》篇载,
巳,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黄色,疵在足,臧(藏)于瓦器下。·名西茝亥旦。
即是根据被盗日的地支推测盗者的相貌、藏身之所,甚至姓名。如果在巳日失窃,盗贼就应该是个子高、脸色黑、眼睛黄色像蛇眼、腿脚有毛病的人,他藏在瓦器的下面,名字里含“西”、“茝”、“亥”、“旦”等字。
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择日术经过文化传播,后来可能流传到了西域地区,在楼兰遗址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中就有类似于睡虎地秦简《日书》的择日禁忌内容,如编号为565号的文书就写到:
星宿之首谓之鼠日,这天可以做任何事,万事如意。
星宿日牛日,宜沐浴。吃喝之后,可演奏音乐取乐。
……[44]
李零、林梅村等学者对这种文化交流现象有所关注,甚至认为其可能是某种中原地区《日书》的犍陀罗语译本。
主要作为择日术的《日书》中有很多关于民间信仰的信息,对我们理解古人的宗教观念、祭祀活动、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有重要价值,值得珍视。
3.占梦
古人认为做梦是灵魂暂时脱离躯体的旅行。而恶梦更被认为是由鬼所致,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就曾多次提到驱鬼以禳除恶梦之法。由于梦的神秘性,古人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有预言的作用,这样就产生了占梦的数术。
占梦属于杂占的一种,《汉书·艺文志》称:“众占非一,而梦为大。”其在先秦秦汉时期极为盛行,《左传》、《史记》等文献中多有关于占梦的记载,秦宫廷中甚至有“占梦博士”官的设置。当时民间的占梦也相当流行,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梦》篇就是关于占梦的著作,
(1)甲乙梦被黑裘衣寇<冠>,喜,人<入>水中及谷,得也。
(2)丙丁梦□,喜也,木金得也。
(3)戊己梦黑,吉,得喜也。
(4)庚辛梦青黑,喜也,木水得也。
(5)壬癸梦日,喜也;金,得也。
由于《日书》的择日性质,此处占梦与做梦的日期密切相关。其占梦文由梦日、梦象、占断构成。以第一条为例,“甲乙”是梦日,“被黑裘衣冠”是梦象,指梦见自己穿戴着黑色衣帽,余下的则是占断,由梦象得出有喜事、如果去水里及山谷中必有收获的结论。有的占文还附有对占梦结果的解释,如第四条“木水得也”即是释梦之辞,“青”五行属木,“黑”五行属水,水生木,五行相得,所以“喜也”。而第五条“金,得也”也是对梦的解释,“梦日”之“日”字为“白”字之误,“壬癸”五行属水,“白”五行属金,金生水,水日梦白,五行相得,故喜。[45]
2007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得秦简一批,其中有关于梦占的简牍40余枚,整理者称之为《梦书》。[46]其内容丰富,既包含占梦理论,
占梦之道,必顺四时而阳其类,毋失四时之所宜 1525、0102
也有类似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以日占梦的内容,
甲乙梦伐木吉。丙丁梦失火高阳,吉。戊己[梦]官事,吉。庚辛梦□山□,吉。壬癸梦行水为桥,吉。 1514、1526
当然更多的则是对所梦对象的占语式解读,
梦衣新衣乃伤于兵
梦见熊者见官长 1500
梦见项者,有亲道远所来者
梦身生草者,死沟渠中 1512
梦见羊者,伤欲食
梦见豕者,明欲食 1523
梦如井沟中及没渊,居室而毋户,
戍死,大吉。梦见虎豹,见贵人。 J51
梦以泣洒人,得其亡子
梦见李,为复故吏。 1508
这种占梦方法与《日书》中主要以日占梦的方式不同,但与后世流传的解梦书相似,充实了我们对古代占梦术与秦人思想、生活关系的认识,影响深远。
4.相术
相术是根据观察对象的外部特征,从而预测其能力、材质,甚至命运的数术。在秦汉时期其属于“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的形法之术。[47]《汉书·艺文志》中形法6家,分别是《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相人》、《相宝剑刀》、《相六畜》。《山海经》“大举九州之势”,《国朝》性质不明,后四者无疑属于相术,其内容分别是相宅、相人、相刀剑和相六畜。相人在传世文献中最受重视,但遗憾的是出土简牍中至今未见此种内容。[48]
九店楚简和睡虎地秦简《日书》中有关于相宅的内容,讲的主要是住宅方位对人产生的影响,相关内容已见前述,在此不赘。
居延新简有汉代相宝剑刀的简册,主要讲述了相善剑与弊剑的标准,包括善剑标准4条,弊剑标准6条。其称故剑好于新器,并认为剑的花纹、硬度、韧性都对剑的好坏有影响。简中明确指出,相刀与相剑同等,故整理者据《汉书·艺文志》将其定名为《相宝剑刀》册。
出土简牍中关于相六畜的记载稍多,敦煌汉简和悬泉汉简有相马的内容,银雀山汉简和阜阳双古堆汉简有相狗的内容。相马术在中国源远流长,到汉代仍很盛行。敦煌汉简载,
乡下说●肠小所胃肠小者腹下平脾小所胃脾小者听耳寓听耳欲卑目欲高间本四寸六百里
简文不好理解,罗振玉通过与传世相马书的对比,认为此简是相马法。[49]简文谈到了通过马的腹部、耳、目等体貌特征,认识马的内脏情况,进而判断是否为良马的方法。
秦汉时期狗作为主要家畜,是人们狩猎的重要帮手。善不善长跑动,无疑是相狗的重要内容。阜阳双古堆汉简《相狗》中涉及“善走”的简有12片之多,主要是通过狗的体态判断其是否善于奔跑。[50]银雀山汉简《相狗方》涉及到狗的头、目、颈、肩、膝、臀、脚、毛等部位,及起卧等姿势,可能是根据这些部位、姿势来判断其是否善跑。值得注意的是,简中多次出现“及大禽”、“及中禽”等语句,如
·相狗方肩晁间参(三)瓣者及大禽□者及中禽臀四寸及大禽三寸及中禽…… 0242
则预测了狗在追逐禽鸟时的潜力,反映了古人相狗的主要目的所在。
吕思勉先生认为:“骨相之说,本只谓观其形貌而可知其才性,因其才性而可知其穷通,……相法似他迷信,究较有凭,故信之者多也。”[51]相人且不论,从出土简牍中关于相物、相畜的记载来看,这种数术确实是从被相者的体貌、形态出发,更像一种凭借经验的技术,而与其它数术中过多的神秘主义倾向有别。
三、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时期。它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之初就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数术、方技有密切联系。东汉之后,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在社会上逐渐被纸张代替,但在道教的法术仪式活动中,木质简牍仍被广泛使用。
出土道教简牍从内容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请谒鬼神的刺谒类简牍和解除类简牍。[52]
道教刺谒类简牍与当时人际交往中常用的刺谒形式相似。《南齐书·祥瑞志》载,南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延陵县季子庙中掘井得长一尺、广二寸的木简一枚,文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谒诣起居。”“道人”称谓说明此简与道教有一定联系,而简中“张陵”是不是东汉五斗米道的领袖张陵则不得而知。据道教经典记载,道教有将谒版埋葬于土中或投于水中以向神祇表示顺从、臣服的习惯,希望由此能得到神灵的宽恕和庇佑,这枚井中所出之简应即用于这种目的。1955年武昌任家湾113号东吴墓出土类似木简3枚,其中一枚简文为:“道士郑丑再拜”,据同墓所出买地铅券可知,此墓是吴郡道士郑丑的自葬之墓,那么木简则是道士郑丑准备的死后拜问地下神灵的刺谒。[53]
“解除”是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种献祭除灾的数术。道教形成后,其又成为道教主要方术之一,由道士通过特定的神秘仪式为生人或死人解除灾疫、鬼邪及生前所犯之罪过。在道教范畴中,人世及阴间的诸多灾厄都被视为解除术禳除之对象。传世道教文献及史籍中有不少利用木简符箓或竹木偶人进行解除的记载,而部分出土简牍作为当时作法解除的实际道具,无疑更具有史料价值。
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曾出土朱书符咒木简一枚,该简上部偏右的位置画有朱色符箓,左下为朱书咒文三行,
乙巳日死者,鬼名天光,天帝神师已知汝名,疾去三千里。汝不即去,南山紟□令来食汝。急如律令。
“天帝神师”、“急如律令”是汉晋道教的习用语,此简作为道教解除简没有问题。简上符咒是用来对付鬼的,可见以知鬼名的方式阻止鬼害由来已久。此外,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也收录有相传为晋代的“仙师木简”一枚,此简正面墨书“仙师敕令:╱天贵龙星镇定空炁,安●”,其中“天”字变形。“师”是早期道教教团首领的常用名,“仙师”是继承这一习惯衍变而来的道教尊者名,“仙师敕令”就是以仙师名义发出的命令。由于此简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与后世道教文献《三元总录》中列举的迁葬神符极为相似,所以其与古代迁葬活动当有密切关系,应是迁葬后留于旧冢以保平安的法物。[54]
用于解除的道教简牍还有绘成或制成偶人形的木简。道教法术中盛行偶人,与东汉时期的民间信仰有关,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载:
今民间独祀司命耳,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檐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重之,汝南诸郡亦多有,皆祠以猪,率以春秋之月。
这里人像有祀“司命”的作用。长沙东牌楼汉简有人形木牍一枚,木牍先刻为人形,在正面上部描画鼻、眼、口、鼻、胡须及躯干,正面下部及背面写有文字,
喜平元年六月甲申朔廿二乙卯,谨遣小史覃超诣在所,到,敢问前后所犯为无状。家富 (正面)
有如肥阳(羊)、玉角。所将随从,饮食易得。人主伤心不易识。超到言如律令。故事,有陈者,教首。书者员圼(从心)、李阿。六月廿二日白 (背面)
此牍作于东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一个地方官吏身染重厄,遣小史覃超沟通上界,问自己究竟有何罪过而遭此劫,并奉上肥羊、玉角以求庇佑。由于书者“李阿”见于葛洪《神仙志》,是汉晋时期的神仙名,可推知覃超、员圼可能也不是人间的实有人物,而应是时人信仰中能沟通阴阳两界的神仙。简中“玉角”是道教常用之物,“如律令”除了秦汉公文常用外后来也成为道教符咒的常用语,“李阿”作为神仙见于道教徒葛洪的著作,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此木牍与后世道教的关系。此人形木牍反映了东汉后期传统的民间信仰逐渐融合于道教的情况,在道教考古上有重要意义。
更典型的道教解除用人形木牍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前凉建兴廿八年(公元340年)“松人解除木牍”。松人为凸刻后画,在木牍正面上部,揖手站立,木牍正面下部及背面是简文,简文中多见“天帝使者”、“拘校”、“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用语,其道教木牍的性质显见。关于此牍,学界关注较多。一般认为其内容是通过道术以松人、柏人代替死者及生人承担咎殃的。死者王群洛子的家人担心死者在阴间受到天地、日月的拘校责难,也担心死者会“注咎”家人,所以造松人、柏人来承担灾难。简文较长,部分摘引如下:
天地拘校、复重,松柏人当之。
日月时拘校、复重,柏人当之。
岁墓年命复重拘校,松人当之。
死者王群洛子所犯,柏人当之。
洛子死注咎,松人当之,不得复拘校复重父母兄弟妻子,欲复重,须松柏人能言语,急急如律令。
生人拘校复重,松人应之;死人罚谪作役,松人应之。无复兄弟,无复妻子。若松人前却,不时应对,鞭笞三百,如律令。
“拘校”指受到阴间官吏的盘问,“复重”指受到死者牵连而导致灾难或死亡等恶劣事件的再次发生,“注咎”指人死后疾病、灾厄向生人的转移,它们都是汉人在宗教场合的习用语。此牍显然是当时道士作法以松、柏人解除生人、死人灾厄的实物遗存,与《太平经》等早期道教经典中关于解除的记载可以参看。不仅汉晋时期有这种绘成或制成人形的木简,到唐宋以后甚至更晚,这种简牍在道教方术中仍继续存在。1973年南昌市北郊唐墓中曾出土完全制成人状的墨书柏人木简,[55]1999年武昌湖北剧场1号墓出土五代时期墨书柏人木牍,[56]1972年彭泽县湖西宋代石椁墓出土墨书柏人木觚,[57]根据简文可知这三件柏人简牍性质与前凉“松人解除木牍”基本一致,都是以柏人作为道术中解除灾厄的工具,其中湖北剧场五代木牍、彭泽宋代木牍与前凉木牍一样,都有“天帝使者”的称谓,更反映了解除这种道教方术的传承性。
除了上述简牍,天津蓟县等地也曾出土过道教简牍,有的且有明确纪年,是我们今天从事道教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出土汉文简牍中的宗教史材料大都与道教有关,而新疆地区出土的佉卢文、吐蕃文等简牍中则有部分与佛教、苯教等宗教相关的内容,虽然不多,但仍有一定价值,可供参考。
思考题:
1. 什么叫遣策,战国秦汉时期主要有哪些遣策类简牍出土,它们对战国秦汉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2. 根据出土简牍,谈谈你对汉代“养老”政策的认识。
延伸阅读:
1.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
3. 张延昌主编:《武威汉代医简注解》,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5. 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
6. 晏昌贵:《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 王育成:《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
[①]《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0页。
[②]关于“遣策”的命名及定义,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本文采取的是通行说法。出土战国秦汉简牍几乎没有自称“遣策”者,在简中一般被称为物疏、从器志等。
[③]《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工作简报》第3期,第7页。
[④]据居延E.P.F22:47A号汉简所载。
[⑤]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⑥]管振邦译注《颜注急就篇诠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⑦]《日书》是中国古代用以选择时日、趋吉避凶的数术书籍,包含有较多社会生活史资料。
[⑧]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310页。
[⑨]张春龙、龙京沙《里耶秦简三枚地名里程木牍略析》,《简帛》(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271页。
[⑩]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物处《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王子今《秦汉时期湘江洞庭水路邮驿的初步考察》,《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其实通过对里耶秦简1714号地名里程木牍的研究,可以发现当时不仅对长江水道广为利用,就是黄河水道可能也已成为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张春龙、龙京沙《里耶秦简三枚地名里程木牍略析》)。
[11]张德芳、郝树生《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2]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页。
[13]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14]何双全《<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页。
[15]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556页。
[16]汪桂海《谈碑刻、简牍中的赙賵名籍》,《秦汉简牍探研》,文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17]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页。
[18]李均明《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416页—425页。
[19]这三处墓葬出土名刺,称呼多“弟子”、“童子”。研究道教考古者认为“弟子”、“童子”是道教称呼,这些名刺应属于道教刺谒类简牍,但多数学者仍倾向于其是一般名刺,今从后者。
[20]扬之水《从名刺到拜帖》,《收藏家》2006年第5期。关于名刺和谒的区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有认为东汉称刺,西汉称谒的,也有学者认为:“谒和刺实为两种不同的文书形式,因使用时间、场合和身份的不同而有区别。一般来说,谒通行于官场;刺的使用范围更宽,为后世名帖的滥觞。”(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第744页)
[21]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9页。
[22]马怡《居延简<宣与幼孙少妇书>——汉代边地官吏的私人书信》,[韩国]中国古中世史学会主编《中国古中世史研究》(第二十辑),冠岳社2008年版。
[23]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7—78页。
[24]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25]参《史记·孟尝君列传》。
[26]王充《论衡·四讳》。
[27]应劭《风俗通义》。
[28]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擅杀子,黥为城旦舂。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今生子,子身全殹(也),毋怪物,直以多子故,不欲其生,即弗举而杀之,可(何)论?为杀子。”简文明确规定除先天畸形外,父母没有擅杀子女的权力,如擅杀就要“黥为城旦舂”。
[29]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1页。
[30]《汉书·贾谊传》。
[31]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72—773页。
[32]关于汉代老年人所受的“王杖”,有学者认为当称“玉杖”,但也有很多学者坚持应为“王杖”。其实,“玉”、“王”二字在汉隶中的写法几乎完全一样,而今天考古发现之“杖”大多为木质,在此问题未彻底弄清之前,我们仍沿用“王杖”的称呼。
[33]李宝通《汉代的<养老令>与“王杖简”》,《丝绸之路》2001年第7期。
[34]汪桂海《汉代高年受王杖的资格》,《秦汉简牍探研》,文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223页。
[35]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编《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25页。
[36]高大伦《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和疾病文书考述》,《简牍学研究》(第二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页。
[37]出土于江苏的有邗江胡场5号汉墓那份解狱告地策。出土于湖南的有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家丞奋移主藏郎中”的那份文书,但目前学界对“主藏郎中”是不是地下官吏的问题仍有争议,所以此文书究竟是不是“告地策”尚不能断定。
[38]陈伟《新出楚简研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124页。
[39]一般认为史先即造字的仓颉。
[40]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4页。
[41]李零《中国方术正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43页。
[42]《后汉书·方术列传上》。
[43]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44]林梅村《寻找楼兰王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111页。
[45]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46]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47]《汉书·艺文志》。
[48]出土文献中,马王堆帛书《木人占》里有涉及相人的内容,但由于不是简牍材料,不论。
[49]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5页。
[50]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7页。
[51]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31页。
[52]王育成《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
[53]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2期。
[54]王育成《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
[55]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5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湖北剧场扩建工程中的墓葬和遗迹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
[57]胡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