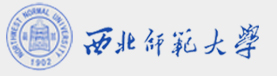案例四——佘祥林案
案情简介:
佘祥林,男,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人。1994年1月2日,佘妻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踪,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害。同年4月28日,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后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因行政区划变更,佘祥林一案移送京山县公安局,经京山县人民法院和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98年9月22日,佘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佘祥林不服继续上诉。同年9月22日,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5年3月28日,佘妻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法庭确认原判决书认定的佘祥林杀妻事实失实,宣判佘祥林无罪。
专家点评: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陈旗认为:佘祥林案件的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做高级人民法院该做的事。佘祥林案件中,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做出了发回重审的决定,并在发回指导函上极有预见性地写明“不能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的可能性”。由于案件后来在中院消化,高级人民法院没有再一次发挥作用的机会,但是,高级人民法院在命案中的作为还是可圈可点。对于那些一审判处被告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担当着重要职责。死刑核准权上收最高人民法院以后,最高人民法院成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对于一审判决被告死刑、无期徒刑等重大案件而言,高级人民法院仍然是正义的重要关口。这一类案件由于涉及人的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权,具有特殊重要性,高级人民法院必须以谨慎甚至挑剔的眼光来审视一审认定的事实细节和逻辑关系(包括其他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以更加坚定的理性克服经验和习惯给人带来的轻信与偏见。对于那些被告人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对事实和法律都应进行认真审核,并且对统一司法理念和司法尺度、排除各种干扰与压力负有责任。佘祥林案件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严惩凶手”的汹涌“民意”包围之中,顶住压力,将案件发回重审,把住了人命关口,不仅是对事实认定的审慎,而且是对刑事司法正义的恪守。
在目前的法院组织格局中,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意义绝不局限于解决矛盾纠纷或者做出一个相对正确的判决,而是同时要通过审判对权力运行进行强有力的监督,而不是轻信权力行使的公正无私,哪怕以国家的名义。如果要证明高级人民法院比下级法院更适合处理那些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法律技术是一个方面,法律良知和胆略是更重要的方面。高级人民法院在司法体系里的地位,决定了它在很多场合下,需要作出其下级法院很难做出的决定,承受其下级法院法官很难承受的压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高级人民法院在利益上应更加超脱,在观念上应更加开放进步。在改革始发和过渡阶段,高级人民法院首先应当在独立判断和勇于担当方面成为辖区法院的榜样。
(二)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佘祥林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法官如何来承担责任。当错案曝光,追究司法人员责任是当然的,而且必须严厉到一定程度,才能应对汹涌的舆论。法院作出裁决,无论其裁决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司法机关的司法作为,法院都无法摆脱或减轻自身的责任,而法官的压力显然更甚于其他司法活动参与者。然而,我们冷静地思考,法官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他独立判断并独立作出决定,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基于他的意志做出,他充分表达了他的意志,他的意志成为他行为的唯一原因,他对自身行为负责。这是意志、行为与责任之间正常的逻辑关系,其间的因果承接明白无误。但是,从佘祥林案件以及一些著名的错案中,我们可以发现,法官并不是唯一参与案件决策的主体,那些决定案件命运的意见可能来自于审理者之外,甚至是法院人员之外,有些决策性意见甚至在卷宗材料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这种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很有政策支撑的司法惯例运行多年,很多涉及面广、矛盾复杂、影响较大的案件都借助于这种方式得到处理,在实践中似乎很有效果。但是,司法审判的行政化色彩和集体负责模式,打乱了权力、责任、利益之间的逻辑关系,决策者游离于责任之外,亲历审判的审理者或许只是幕前玩偶和问题发生时的替罪羊,更多的时候,责任者以集体的面目出现,谁都有责任,谁也都没有责任。真正的裁判者没有责任或者责任错位,显然违背司法规律,可能打开冤错之门。因此,如果司法责任制改革能够保障审理者基于自身意志作出独立判断,并对自身基于法律和良知作出的决定承担责任,那么审理者与裁判者,裁判者与责任者在身份上就能高度统一,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法官会主动对自身行为做出评估,积极减少风险,并将这种审慎的习惯内化为敬畏法律、慎待权力、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职业伦理。
(三)培养法官的独立精神
无论是立足于过去的司法政策,还是秉持先进的人权保护理念,我们都可以从佘祥林案中发现诸多不能得到合理解释的疑点。这些疑点并不是隐藏很深,也不需要超凡的智慧予以发掘甄别,有些“事实证据”甚至经不起平常人的仔细阅读和推敲。也就是说,有一些冤错案件远远够不上疑难复杂案件的标准,这些无法原谅的错误不是因为法官欠缺法律技术而产生,也不是法官偶然疏忽和误判的结果。佘祥林案件被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后,即被“下移”到基层,由基层法院作出15年的有罪判决,最后由中级人民法院一锤定音,规避了高级人民法院的再监督。这表明,当地司法机关对于佘祥林案的情况心中有数,但是却基于种种考虑,罔顾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坚持走向了错误的方向。法院在这场“安排”中随了“大流”,毫无独立精神和意志,这对于法治国家而言,无疑是危险的。
法院或法官的独立精神,不是在法学院里给法科学生补给法律的信仰就行了。独立精神的培育除了教育,还需要政治环境和体制机制保障。所谓政治环境,目前对法院来说就是法治环境,即国家坚定推进法治,尊重法律,相信法官的专业判断,允许法官首先对法律负责。体制机制保障则更广泛复杂,也是我们目前司法改革的努力方向。要使法官拥有强大的抵御外界冲击的内力,除了如前面说到的“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等司法权运行机制设计,’还需要给予法官必要的地位与尊严,保护法官职业安全、人身安全和人格安全,使法官在心理上能足够冷静和强大,不至于屈从于一时的权力需要、舆论喜好和民意压力。如果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的工资收入相当于酒店服务生,和普通市民一样仰望着飙升的房价叹息,裁判作出前后时常遭受威胁谩骂甚至殴打伤害,他不可能有独立精神,也不可能有承担责任的肩膀。
法官不仅是法律人,更是社会人,没有体制机制的支撑,信仰是脆弱的。因此,当我们反思冤错案件给民众和司法带来的伤害,不能停留在法律技术层面,也不能止步于人权观念的革新进步。在防范冤假错案的艰苦努力中,我们更要关注法治大环境的建设,使其有利于培养一支具有独立精神的法官队伍,使法官们既有知识又有勇气去捍卫法律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并因此获得国家和社会的尊重。